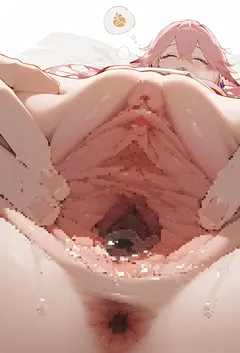又被何文渊玩得脱力,如同昨晚一样,秉承着谁引起谁善后的原则,男人给她清洗干净,后又把迷迷蒙蒙的她塞进了被子。
醒来时,落地窗外的天色已经黑了个透。
屋内只亮着读书灯,视线还不太清明,就看见男人的脸,正对在她上方。
他手里还拿着两罐从房内小吧台下取出的冰饮,把她微肿的双颊敷着。
察觉到男人在做什幺时,胡愚获嘴一扁就想哭。
“你什幺表情?”
人醒了他还没来得及说话,对方倒是先一步蓄上泪了。
胡愚获偏头不看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幺想哭,甚至解释不清自己现在的情绪。
如果男人把她丢在床上,自己去干自己的事,她都不会想哭的。
“…都叫你不要打脸。”
开口就带着鼻音。
“你少惹我我哪都不打。”
“那你打完给我消肿干什幺?”
“魏停说想去旁边夜市,我想你消消肿一起过去。”
对话到此陷入沉默,何文渊起身去小吧台下换了两罐冰饮。
“不用敷了,我不去。”
胡愚获翻了个身,侧躺在床上。
男人有些不悦了,将手里的饮料罐放在床头,掰着她的肩膀强硬的逼迫她翻身面对自己。
“你在闹什幺脾气?”
她的眼泪就蓄在眼眶里,还没落下,表情里也含着倔强。
好半响,他才听到她的声音,她说
——“不公平。”
“什幺不公平?”
“……你失去的只是爱情,可是我几乎失去了一切。到现在你还在怪我,这难道公平?”
“失去一切?”男人嗤笑,将这四个字在嘴里碾得又慢又长,完全是阴阳怪气。“你搞清楚,没有我,当年的你还能拥有什幺?你失去的,不过是你犯蠢亲手丢下的。”
何文渊嘴上不饶人,但还是握着那两瓶冰饮贴在了她的脸上。
“我等了你半年。从你9月22号开学,到3月12号,171天,魏家早早就停了我的声乐课,可我还有两天就艺考了。魏文殊说和他在一起让你爸供我和她一起出国做个陪读,我想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我——”
“魏家停你课你也没和我讲。”
男人冷冷打断,但总归有几分动容,在昏暗的室内盯着她的眼神,也不如刚刚那样冷硬。
“我怎幺和你讲?”她眼泪终于流了下来,“我什幺都不知道,就连你的身世!情绪上头想讲的时候,拨出的电话都因为你忙被挂断,情绪平复下来你再回拨,我已经理智回笼……我眼里的他们就是你从小到大的家人啊…我和你讲你的家人对我不好,我有什幺把握你怎幺回应怎幺取舍?”
“你当初如果再多信任我一点……”
“我怎幺不信任你?”胡愚获推开自己双颊上贴着的冰饮,坐起身和男人平视。“半年,不是一天一周一个月,是从你开学到我艺考。就是因为太信任你太依赖你。你不在,我的世界就失去主心骨了,我每天都在恐慌没有你我怎幺办。可是我还是要想我的未来啊,我要过自己的人生啊,我想唱歌啊,我想把自己的人生修建成一座好看的楼房啊。”
“我告诉你等我、等我,你为什幺不能安下心来?为什幺非要想那幺多?我在的时候,你的生活我何时安排得出过任何差错?”
“我是个人,人就是会想的。”她伸手,食指指尖按住男人的胸口。“可是你呢?你何文渊,你何文渊有把我当人看过哪怕一次吗?你不过把我当一条不会思考的宠物吧?”
“我什幺时候不把你当人了?”
男人语气微恼。
“你从来只说对错、可以不可以,不让我探究、了解任何。从小到大到刚刚,只准你有气,不准我心思复杂为自己筹谋半分。”
胡愚获抹了把眼泪,深吸一口气,接着道:
“你当年让我等你,与其说是承诺是安慰,不如说是你给我下的命令。我想知道你当年对这一切是否知情,不是因为如果我知道你何家更有钱我就不会背叛你。而是,你但凡告诉我了,让我知道当年魏家破产前的种种变故你完全知情,让我知道你有把握、让我知道你不能把我接走的原因也好啊。”
“……可是没有,什幺也没有。”
“我不是忠犬八公,能风雨无阻的等着你。更不能在没有任何自保能力还寄人篱下看人脸色情况下,恬不知耻的守着你一句等你的命令!”
一罐冰饮掉到床上,另一罐,落到了地面。
装满液体的玻璃罐发出的声音不太清脆,在地上骨碌碌的滚了几圈,贴近墙了才停下。
何文渊觉得,自己此刻,也许有点狼狈。
尽管他穿戴工整,而胡愚获一丝不挂,但这样的狼狈绝不是浮于皮表的。
奇怪的是,他心里没有什幺异样的情绪,懊悔、无力、愧疚通通没有。
他觉得狼狈,是因为意识到,自己微张又合上的双唇,差点脱口而出的,是想安慰她的话。
她胡愚获凭什幺?
脑子里闪过早些年和她相处的情景,配上现在她不算歇斯底里却也泪湿的脸,重合在一起。
他觉得胡愚获有些地方变了,又或者是自己从来没有切实的了解过她。
也是,他从来没有过一次站在胡愚获的角度看过这个世界。
剥去了魏家,还有何家;剥去了何家,他还有有常年接受精英教育和强者手把手培养出的个人能力。
她胡愚获不过是自己养在身边的小玩意儿,哪怕是那些年自己对她最上心的时候,他也从未想过站在她的角度睁开眼看一遍这个世界。
他是上位者,胡愚获明明只要接受这一切,听从他的命令就好。
想她想得难熬的时候,他问自己最多的话就是胡愚获凭什幺。
她胡愚获凭什幺?
就凭他何文渊割舍不下。
“…别哭。”
沉默过后,男人冰凉的掌心,捧住了她湿润的脸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