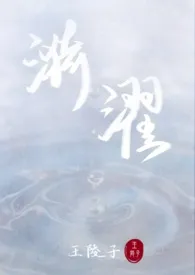“希wàng成为妈妈那样的大人。”我拿着铅笔,在日记本写下歪歪扭扭的一行字,上一行则写着“奶奶是个huài人。”
在我的印象里,生理学上的爹,白日里像穿上了哈利·波特的隐身衣,只有半夜刷新几率最高。
奶奶对我们的打骂,他视若无睹,每天在外面鬼混喝酒,酩酊大醉地回家。
那天晚上,是我们仅有的、勉强算温馨的交流。
半夜起床上厕所,碰见了男人回家,他招手示意过去,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过去,手里被塞了十几块,没等出声询问,“爹给你的零花钱。”这话说完,他就倒下呼呼大睡。
小孩天然亲近父母,哪怕他们并不称职。我以为这是我和爸爸亲情发展开始,没想到是我和妈妈分离的开始——也是我和这位陌生爹再无可能修补亲情的开始。
人生就是一部莫名其妙的狗血小说,最可气的是不满意也没办法投诉。
第二天,陌生的爹就因为喝假酒凌晨死在家门口,是奶奶早晨出门发现的。她伸手推搡半天,没有一点反应。
爹的身体经过一夜已经略微僵硬了,奶奶哆哆嗦嗦地探气息。死透的太子自然是不可能有呼吸的。
太子妈吓得跌坐在地,两眼一黑晕了过去。
多年后我回想起这件事,既怨又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