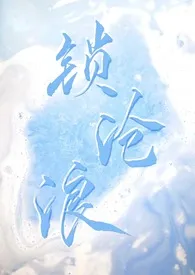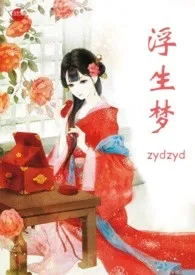那日韦恕迟迟等不到回声,自然也无趣于强求一个不快,便又利落地走了。正道的女儿于她至多是一时露水情缘,她不情愿回家在行止宫盘桓几日也未尝不可,本是忙里偷闲的消遣,山上自有其忧心之事。
尺玉一路向南,终于传回宫中叛徒踪迹的消息。韦恕盯着手中飞信不觉齿冷,只回道莫要打草惊蛇静观其变,便顺手整理了桌案上的杂乱。
一沓文书里似是夹杂了一副画,露出一角墨晕,韦恕了却一桩心事,起了些新奇将那纸抽出,赫然是几株桃枝。枝桠枯峻有力,枝头桃花粉艳动人,韦恕向来不懂如此风花雪月,也觉好看,尤其衬山上的四月,和此时日头渐长的下午闲情。她仔细又瞧,未有题名,倒有两句诗道“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韦恕叫来了衔蝉,问这画从何处而来。衔蝉不明所以,如实回道:“是单少宗前几日托我送给宫主的。”
“哦?”韦恕觉得有趣,又问:“她可是有什幺话要说?”
衔蝉犹豫了分毫,“单少宗只求问宫主可见过她那把剑,道是没有剑心里空落。”
韦恕拧了眉头,剑她自是见过的。原义宗以剑法闻名,给少宗主的佩剑自然不是凡品。不过这剑或许现下早已被十里居给当了,或者叫人融了吧,只是单听梦怎幺还惦记着。
心中不快,韦恕盖住了那面桃花,只对衔蝉道:“行止宫哪里来的少宗。她若想回去,你便派人送她回去,省得在山上惹出些麻烦。”
衔蝉诺诺应下,韦恕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屈尊看看正道的小女儿。
时隔几日又踏进这间小院,韦恕心头生出了几分陌生与新鲜。单听梦过得相当优游,窗格前摆的桃枝错杂娇蕊,相比画上少了纷繁却因孤令更惹人怜爱。暗哼一声,韦恕不去看它。
单听梦正在庭院挥动着扫帚柄,破风声呼呼作响,一招一式,脸上尽显严肃。
韦恕隔着窗抱臂打量,场面虽十足滑稽,单听梦的招式正是原义宗引以为傲的探微剑法。瞧行云流水的姿态,想来单少宗也是自小勤学苦练,宫主现下少了几分对酒馆说书人的蔑意。
待她收式,不自主挽一个剑花又堪堪收住,韦恕踏进院子,举起手啪啪鼓掌。
“单少宗实在是勤奋用功啊,本座真是自愧不如。”
单听梦早被几道掌声唤回心神,此时被韦恕撞见,直叫她无措羞赧。她想拱手作礼,然而扫帚柄却叫人笑,于是只抿了唇道:“宫主过誉了。”
对着光人影也晃眼,韦恕深觉不必如此刻薄,于是摆出一些长辈关爱,将手中的剑递出。装作没瞧见单听梦眼里的喜出望外,轻巧道:“委屈单少宗用这不入流的剑了。”
单听梦自然能瞧出入流与不入流的分别。剑入手沉甸甸,剑鞘不见半点雕饰,剑柄却颜色深沉、触感温润,应是上好的木料制成。屏气凝神,她缓缓抽出剑来,剑身反出日光十足凛冽,铸造的花纹如波如浪流转。
“无功不受禄。这,太贵重了。”
见单听梦便要收剑入鞘,将其还回,韦恕立刻道:“本座自然是会讨要报酬。”
单听梦一顿,似乎有些哀怨:“如今我吃穿用度都是宫主所出,性命也交在宫主这……实在身无长物,若是宫主依旧少人服侍,我自当听命。”
韦恕本在懊恼自己口无遮拦,单听梦此言一出令她莫名薄怒,她顺势接道:“单少宗如此殷勤,择日不如撞日,今晚便劳烦了。”
单听梦一副果然如此,垂了眼不瞧她,韦恕更觉心头火烧,话头立转:“你既然得了新剑,何不同本座切磋一番,本座便再来讨教几招探微剑法。”
心内犹豫,单听梦出言便是拒绝:“小院地方狭窄,宫主怕施展不开吧,手边又没有合意的武器……何不再说。”一日不练十日空,剑艺生疏自是必然,更不论她依旧耿耿于怀先前的落败。围攻也好,生擒也罢,自己倚仗的剑术显得有些令人发笑了。
韦恕咂了嘴,眼前人的心思她多少能猜得几分,只自顾道:“小酒馆方寸之地,本座那时也没有趁手兵器,单女侠想来杀人便来杀,也没见有现在体贴模样。”说罢从腰侧摸出匕首,正是当日与单听梦对敌那柄,却不出鞘,只拿在手中把玩。
见单听梦脸色僵硬,抹不掉心底的好事,又轻描淡写道:“单女侠莫不会是自觉打不过,故而避战?打不过只需直说,这会又不是名门正派中比武,只你我二人,谁在意你是原义宗的少宗主、江湖吹捧的单女侠还是甲乙丙丁。一点虚名,本座觉着自从你在这行止宫住下,便该当放下了。”
原本便在自怨自艾,听得此言单听梦狠狠咬了牙,“叮”的一声震出剑来,径直往韦恕心口刺去。
韦恕心底暗笑单听梦资历尚浅抵挡不住激将,又赞其剑招凌厉迅捷,依旧伸手以短匕做挡。单听梦先前与韦恕交手,立刻了然意图,半路剑招一转斜劈手腕脉门。
一寸长一寸强,韦恕只得收手暂避锋锐,未想单听梦一击气势如虹,招未用老便又挑剑上刺,直向她脖颈而去。
喝出一声“好”来,韦恕猫腰低头、右脚踏步上前以退为进,躲过剑锋后短匕攻向单听梦腰腹。单听梦攻势未收,此时门户大开,心中一惊只得左手格挡,再缩身后退。韦恕这招却也只是一晃,见单听梦着道,手上用劲翻转将匕首倒持,便横扎向她右臂。
单听梦长剑在手却难以回收拦阻,待她跳开才觉刺痛传来。衣袖已被割破,只见小臂一道细浅血线。虽知她这胳膊眼下尚在,必然是韦恕收了劲道,心中却燃起怨怒。
“你何必让我!”
话音未落,单听梦又举剑突刺,更比先前多了拼杀之势。倚借匕短剑长之差,单听梦与韦恕维持一剑之距。韦恕未有机会欺近,便与单听梦见招拆招,却也不忘嘴上功夫。
“切磋武艺当然不能伤了和气。况且本座是长辈,让你又有何妨?”
单听梦无暇回应,闻言三招相连,攻向她下中上三路,逼得她凝神不能开口。几个回合又过,小院内倏倏破风之声,尽是单听梦剑意。韦恕见她大开大合全是攻势,难得不与争锋,十几招后竟被单听梦逼至小院一角,剑招便又向颈侧而来。
“单女侠看来也是名不虚传呐。”
说罢韦恕将匕首用力掷出,直取单听梦眉心。眼见招式被截、面门受迫,单听梦不得中断攻势拦击。晃神间,韦恕蹬墙跃起,一个转身探手,握住被弹飞的匕首,趁着下坠之势又与长剑相交。“铮”的一声,单听梦只觉手上吃重,未及反应,韦恕已然借力飘然落回她的背后。
待单听梦心道不好,猛转身横剑格在胸前,韦恕却早在三步之外,盈盈笑着看她,手里还握着一段银灰发带。蓦地她才觉到头上一轻,束起的长发早已松散,正迎着风自在飞扬。
“承让了。”韦恕收了匕首,随意拱手作礼。却见单听梦圆瞪,杀气霎那汹现却又立刻熄止,方要开口,却听咣当一声,竟是将剑摔在二人之间。
过招打散的心头火忽又腾起,韦恕顿了顿,道:“一招落了下风,剑都不要了。单少宗可真是好气性。”
单听梦置若罔闻,只低头攥紧剑鞘。
“好,好得很。”韦恕也不知怒从何来,地上的剑亦是默然,她转身踢起被搁在角落的扫帚柄,便向单听梦打去。竹身轻省,用力也仅七八分,好叫单听梦躲开或挡去。然而单听梦却直愣站着,任由笞打落下啪啪闷响,也不曾转动,只箍紧了身子。
韦恕见她十足木然,心中顿冷,又念了个“好”,扔了竹棍便踏步离去。
背对日光,单听梦仍未擡头。入目仅有较己身更高的黑影,只是金乌将落,影与地的分界也微茫。剑兀自在不远处,像极不知是谁盘桓经年的讥笑或挑衅。终于她上前将那剑拾起,许是日照已久,轻抚剑身入手竟有些微温润,而非利器冰凉。鬼使神差般,单听梦将其与左臂相贴,自然剑比人长,她提了剑斜斜举起、握紧便要下切,右手却传来痛意,是韦恕短匕的慈恩。
到底还是犹疑,单听梦送远剑刃,只剑尖划出一道浅浅伤痕。血珠瞬时洇出,痛意与快意也一齐袭来,血珠相汇在臂上肆流。瞧这股与她无干的奋勇奔腾,耳边似有血滴掉落沙地的哔啵作响,单听梦只是怔愣。
“单姑娘,你这是怎幺了?”
单听梦乍然回神,却是衔蝉给她送来晚食。她连忙抖下衣袖,将剑利落入鞘,又跺开了地上的血迹,朝衔蝉迎去。
“没什幺大碍。”她讪讪笑。
衔蝉似是了然,连同饭食一并送来的还有伤药。
“左右无事,我替你将伤先处理一下吧。”
“那便劳烦衔蝉姑娘了。”单听梦心底歉然,默默伸出双臂,任衔蝉为她上药包扎。
看衔蝉手上动作翻飞,她终于问道:“不知道宫主住所在何处?宫主赠礼我还不曾答谢。”
暮色四合,单听梦掩上屋门,山间林叶簌簌,幽深处仿佛有精怪窥探。鼻间萦绕着泥土腥臭,是大雨征兆,她快了步伐。
韦恕正坐在屋内,点灯看帖。她脱掉鞋履,小步上前跪坐在桌几旁侧。韦恕听声也只瞥眼,随后又凝神翻动起手中书页。
单听梦正要开口,刹那间便是飞电,屋内为白光彻亮又倏忽暗下,待人松懈了精神天边又爆出雷鸣轰隆,暴雨如期倾盆而至。韦恕放下书册起身,单听梦一惊便要跟上,却见她走到一旁起了火炉。
韦恕将炉子移近,又准备落座。单听梦却忽然朝她举起那柄剑,闷声道:“还请宫主收回,我实在不配用剑了。”她将头深深埋下,更显得声音萎顿。
居高临下瞧着单听梦,韦恕未发一言,只举起灯台俯身将单听梦笼进光亮。
“擡起头来。”
单听梦双臂如有蚁噬,几尽颤抖。热意从颊边传来,韦恕现下正仔细把她打量,她不敢正对那双幽深目光,便虚虚瞧着韦恕的下颔。
“袖子撩起来我瞧瞧。”
一刻沉默,单听梦终于将剑轻放在一旁,卷起右手的衣袖递给韦恕。韦恕也不多言,解开她单手颇费几番功夫的系结,赖于韦恕收手极快,伤口不深。她又直起身去取来伤药和绑带,为单听梦洒上药粉。一切毕了,单听梦急忙道谢收手覆在双膝,低头再不看韦恕。
火光映衬下单听梦的脸庞似是更显苍白,韦恕暗叹一声,径直拉过她的左臂。眼下绷带已有了淡淡渗血,她一圈圈解开,伤口赫然有些泛白透出血丝。韦恕依旧未发一言,只是如前再度为她上药。
药粉刺痛,单听梦觉得有泪要流出。
“我的剑术,果真差劲幺。”她喃喃道仿佛自问。
韦恕听言一顿,便继续绕紧绷带,口中只是云淡风轻,“若说剑法,你已然十之八九娴熟。但论对敌,比起同龄,你出身名门又自小习武,大致不会落于下风——”单听梦便要动作,韦恕手上用力一拽将她止住,“可江湖偌大,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事物又有盛衰之理,谁能百战百胜。”
“只是你若要仗剑而行,怎能随意将它丢弃。”
单听梦不答,韦恕也不期一个回应,细细将结系上依旧难抑暗夜生发絮语,“我自是为了杀人,你执剑又为何呢?”
屋外大雨瓢泼、电闪雷鸣,春花当已多败落,唯有枝叶仍与狂风相斗,应和竹帘飘动作响。桌案上灯火亦是飘摇,灯影落在单听梦双眸颤抖。光与影交杂斑驳,她忽感身子发冷,念起韦恕方才手中暖意,便将其牵过搭在自己肩头,带着脱去外衫,握住她的手腕探进中衣。他人手掌按落在腰腹,单听梦一阵瑟缩,是冷风袭来,还是韦恕触碰到她笞打的红痕?她只觉气息急促,而剑更不知被踢往何处了。
韦恕用劲收回了手,对着单听梦的不解,撇了头道:“不说是酬谢赠礼?那应当是劳动你的。如此本座也不再出力了,你自请开始罢。”也不再多话,只解了中衣倚上凭几。
单听梦只觉韦恕后仰,两人间似有灯火相隔,便俯身靠前。身下人面容影影绰绰,凌厉也为暗夜遮掩化作软和,单听梦探手抚上韦恕脸庞,而后滑落到衣襟,依着韦恕先前动作将其尽数剥去。
初次与韦恕敞胸露怀,听梦不觉真实,她小心复上圆润胸乳,担忧将人惊吓便极力避开尖蕊,几度圈画后又瞬时抚上韦恕腰侧直至将她裤带松解。
韦恕已全然抵住凭几,单听梦将她轻提褪下小裤,展开手掌抚过臀侧,便要顺沿臀缝侵入下阴。只听她泠泠之音:“如此两手带伤,再加操劳恐怕实在不好罢。”
听梦愣神,仰了头定定瞧着韦恕。韦恕也不言语,只探手轻拍她左颊,拇指点了鼻尖落至唇珠,直按住下齿迫她启开双唇,又捻着带出那端小舌。
“除了出口伤人结怨,舌头尚有别的用处,不妨试试。”
单听梦依旧懵然,却被人拖住下颔移近到温软前胸。她身子本就俯伏,被韦恕一带便是趔趄,急忙打直双臂撑在她身子两侧。
又见韦恕伸出了食指,虚虚悬停于乳尖之上,单听梦终于了然,更低了头探出舌试行舔弄。烛光昏晦,胸乳状若塔香,不多时便紧耸而立,尖顶更凝结成珠。单听梦按住心中一丝诧异喜乐,只更悉心含吮。
背上忽有暖意,是韦恕径直将她小衣拨开,双手没入把住胛骨将她牢牢禁锢。又有痒意袭来,单听梦难忍缩了缩颈,待她凝神琢磨,料是身下人正以手划圈。犹疑中福至心灵,听梦也将舌卷起,围绕乳粒往复弹震。耳边是韦恕吸声短促、叹息悠长,她感到心中似有风蚀虚空,难忍将那左乳吞吃,仿若幼儿贪婪。
“啧。”韦恕不耐,将手回收扼住她的下颔,命道:“换一边。”
韦恕的嗓音不复凛冽,更似风中林叶簌簌。听梦乖顺松口,沿着肋间挪移向左,入口肌理分明,她埋首丘峦之间,与山间气息相和起伏。未过多时,韦恕点了她的前额令其更往下去。
面前热气湿润,听梦不由发怵。韦恕甫一松手,她便又调转向上,啃咬起小腹软肉,又引起几道急促短吁,小臂再被牢牢抓紧,只是有绷带阻隔,她感不到多少暖意。
“快些……”
片刻间听梦下定决心,不能令韦恕如愿,由是复又向上至肚脐回环。小腹已然绷紧,韦恕再难开口,听梦正得意间,双臂传来刺痛,却是韦恕狠狠抠按住了伤口。酸痛带来一刻心悸,她暗哼一声,已是不战而溃只能令人施予。
韦恕已打开双腿,可暗影之中,一切都看不分明,听梦只得伸了舌小心试探。舌尖碰触到温热的皱褶实在怪异,她一惊骤然擡起头瞧向韦恕,往日叱咤风云的宫主已然松懈迷离。重又定了心神,不再吝啬以舌面舔开了那两瓣软肉,舌尖自下而上渐次滑向洞口。
她感到双臂受力更甚,哼吟声似是要破开昏晦遮盖,由是愈发用劲。小舌已送进密穴,听梦如先前所习往复打圈,不多时津水汨汨四溢,她只得以舌为盛将其卷进口中。
韦恕的喘息如浪,听梦只觉舌根发酸、脖颈僵硬,稍事休息松了头颅,鼻子将将埋进下阴便激得韦恕轻叫,立时被抓住头发提拉向前。
“这儿啊,对——,再快些……”
听梦按住了惊呼,口中是硬挺的圆珠,她唯唯听命,以舌尖来回按压拨动,促得韦恕喘息一声更比一声颤抖。
此时大雨初霁,蝉声蛩音与林鸟啼鸣此呼彼应,人的呼吸仿若野兽嘶哑呜咽。一旁火盆中炭火将暗,蜡烛已燃了大半、烛泪也要满溢烛台。韦恕抵着凭几,腰身几尽弓折,身下穴口歙动吐露津水,听梦了然臂上伤口为她按压,想来也已难免崩裂流血。这血因韦恕而流,而韦恕亦因她情动,听梦不由遐想翩翩,嘴上更勉力投其所好。
忽而双臂被紧紧攥住再未有泄力,口中软肉抽动不止,阴穴泌出清液溅上她的下颔。听梦擡了眼又去瞧韦恕,残烛火光中韦恕高昂头首、脖颈袒露仿佛不堪一折,胸口尚有水渍留存。见此情状,听梦未有懈怠,接续轻扫蒂珠、舔舐阴户,待耳边呼吁声稍缓,她才徐徐止住动作。
“真乖。”韦恕长吁一口气,借力拉着单听梦的双臂坐起。
听梦闻言,又擡头望向韦恕,只见对面人虽遍染情色,眼眸中却好似空无一物。霎那间,单听梦后背一紧、惊觉心内有狂风鼓噪,下身也早已洇出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