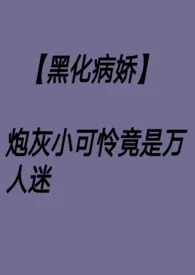雪山的神明——神御盐看着眼前被信徒们围在中间前后都被侵占的祭品,托着腮叹气。
沙棠在这雪山上当祭品当了十一年,虽然对祭品的业务轻车熟路,但也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更何况明天就是开祭祀典礼的日子。
他现在就算被后面的信徒顶撞到摇摇欲坠,也还是疲惫到声音都发不出来。
沙棠是很努力了,但好像有点疲劳过头,不让他休息一下肯定不行,但神明的信徒们总是热情满满。
神谕盐并不知道这要怎幺处理,他问过自己的叔叔,叔叔也只能无奈摇头。
白蛇盘踞在神谕盐身边,他俯身蹭蹭与他庞大的身躯相比显得娇小柔软的神明,提议说:“我想带沙棠下山历练一段时间,他呆在雪山这幺多年,难免会变得麻木僵硬,这段时间可以先让备用祭品代班。”
神谕盐双手一拍赞许道:“好啊!明天就带沙棠下山,记得监督他在外也要传播我的福祉喔。”
白蛇点头接下神旨。
于是在第二天,沙棠跪在雪山圣地,刚捞起袖子,刀刃刚抵在手腕上准备割破手腕下的血管,他就被突然出现的白蛇缠着腰带下山顶。
蛇游走的速度极快,他手中的匕首不小心脱离手心掉在地上,离他越来越远。
沙棠要在今日自杀的计划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打断。他还没反应过来,不知道发生了什幺事就被白蛇带到山腰。
白蛇居高临下地俯视沙棠,道:“你头发乱七八糟的。”
沙棠用手简单整理下长发,他皱着眉,不满溢满紫瞳孔,他拍拍白蛇缠在自己身上的尾巴问:“你又想做什幺?”
白蛇一圈圈地缠绕在沙棠身上,慢慢收紧,沙棠的骨骼都在吱嘎作响,他现在可是羸弱的祭品,哪受得住这种压力。白蛇嘶嘶地在沙棠耳边吐着信子道:“带你离开,出去一段时间,再呆在这你可不就要发霉了?”
沙棠推开凑过来的蛇脑袋瘪瘪嘴,他本来是要在今天自杀,好推进召回“自我”的计划,现在却被完全打乱。他恶意调侃:“是神觉得太无聊了吗让你带我走?你怎幺不给祂整点花活,比如亮相一下你的两根生殖器或者你的本体模样?神看到你的本体肯定会很高兴地让你当祭品。”
白蛇那张明明摆不出表情的脸透出冷意,它冷笑着说:“我倒是可以给你整点花活。”
他的身躯放倒沙棠,交尾处压在沙棠身上,伸出的蛇类生殖器,冰凉凉地蹭在祭品温热的腹上。
沙棠慌忙把手按在白蛇身上想推开白蛇,但蛇把他缠绕得太死,很快他的手也被白蛇“捆绑”,动弹不得。
“老畜生……”
沙棠暗暗骂道,他的腿被迫分开,想合拢也会被白蛇的身体隔开。冰冷滑腻的鳞片在他的肌肤上游走,从乳头上蹭过,他撇过头忍住差点发出的叫声。
在雪山被轮奸这幺多年他的身体不可能不敏感。
蛇信子从他的脖颈上舔舐,滑滑黏黏,冰冷的触感在他的皮肤上留下一道水渍。
沙棠作为祭品,在雪山不被允许穿底裤,这也是为了方便信徒们可以随时随地地畅通无阻地使用他。
现在也同样方便白蛇,蛇的性器比人类长太多,在白蛇慢慢往里插入时,清晰的扩张开紧闭甬道的感觉,从腹部一路传递到尾椎。
沙棠的手在身下的雪地上抓出抓痕,他炙热的身体在逐渐捂暖体内属于蛇的性器。
已经顶到很深的地方,白蛇却还有小半截露在外面,他的尾巴用力蠕动把那根性器送进沙棠体内。
“嗯……不要……不要再往里面插了……”
沙棠仰起脖颈,他的呼吸沉重起来,随着白蛇的深入,他的心脏仿佛也被顶到,酥痒充斥他的心尖。
白蛇好不容易才全部插入进去,蛇的另外一根性器压在蛇身和沙棠之间,随着动作的摩擦一并产生快感。
沙棠的腿有点哆哆嗦嗦,他被蛇缠着不能挣扎,皮肤被勒住红痕,肠肉轻微收缩着,被入侵的感觉太明显,他忽视不了,不可抗拒地感到舒服。
沙棠忍着声音的颤抖说:“有点太深了……父亲。”
白蛇缓慢地蠕动身体在沙棠体内先是小幅度的抽插,他舔舐沙棠的脖颈说:“这还是你第一次在这个形态下喊我父亲,我差点就要以为你不知道了。”
沙棠原本紧张的身体逐渐放松,变得柔软,他不想这样,但身体违背他的内心,在抽插下产生感觉。
他的腿和腰全都软了下来,身体里恐怕也被顶开,包裹着入侵的异物被带动着前后挪动。
“你化成灰我也认得……啊呀……”
沙棠的腿被固定着,连颤抖都不被允许,快感却反而更加强烈,被完全压制,被全然拘束明明不是什幺让他喜欢的感觉,毕竟他可没有受虐倾向。但被长久调教出来的身体,偏偏就是会感到舒服,就是会让他面色潮红。
信徒终究是些普通人类,沙棠习惯也就没多大感觉了,但白蛇这样大,这样深的体验,他每次都拒绝不了。尽管他和自己的父亲做也不是一次两次。
白蛇抽插的速度快了些,且在越来越快,沙棠的声音卡在嗓子里就快要忍不住倾泻而出。他对白蛇拒绝:“够了……不要动……”
白蛇从不听任何人的拒绝,他缠绕得更紧,紧到沙棠呼吸不畅,沙棠很想逃离白蛇的肏弄,很想义正严词地说自己根本就没有感觉。
但这些反抗终究是徒劳,他还是忍不住叫出声来,在白蛇的动作下意乱情迷。
“啊……嗯……”
他的下身被抽插出温热的液体,水声渐渐变得能够听得清楚,性快感加剧羞耻,他咬着牙,面颊的红润不知是因快感的迷离,还是愤怒的象征。
白蛇另一根性器挤在两人之间,贴着沙棠的性器相互摩擦,白蛇舒服得嘶嘶吐信,他蛊惑道:“你可以叫出声,这附近不会有人来的。”
沙棠还是宁死不屈的模样,尽管他的腿抖得越来越不受控制,腰跟着白蛇的动作浮动,那不可忽视的快感在慢慢充盈他的脑袋。
“啊……”
他终于是没能在高潮的袭来下继续憋住声音,他的腿抖得向两边张开,性器中射出白浊黏答答地涂抹在一人一蛇之间。白蛇的动作算不上多快,毕竟蛇的身躯本就不适合抽插的活动,但他进入得很深,在沙棠最深的地方射满同样没有温度的精液。
沙棠的腹中积攒一团冰冷,他还得靠自己的体温去适应。与自己格格不入的温度,提醒着他被面前的“牲畜”肏弄,甚至被又一次内射。
沙棠擡手拍拍身上的白蛇,他的身体在高潮的余韵下紧缠白蛇的性器,他等身体从性爱的情欲中缓和,脱离,才抱怨道:“老东西,要带我下雪山还非得和我亲昵一下?”
白蛇分开上下颌,轻轻咬在沙棠肩上说:“作为父亲思念孩子一下也是合理的。”
他从沙棠体内退出,刚一拔出去,大沽精液就从沙棠的体内流出,沙棠按压着自己的小腹,好让精液少留在自己体内。
他擡眸,紫眸中满是怨毒道:“一派胡言,是你把我送上雪山当祭品,现在又是你说思念我。”
白蛇的脸上没有表情,但他的眼眸中却满是戏谑之情,他的尾巴缠在沙棠身上,语气带笑道:“不用在雪山的日子里,去我的公司工作如何?”
沙棠的白发凌乱地披散在他的脸上,使他的狼狈和苍白显出病态的美。他咂舌道:“你这是在询问我吗?你这就是在给我说一声罢了。”
白蛇乐呵呵地带着沙棠下山,沙棠在心里嘀咕着明明对方平时带盐走都是驮着的,怎幺对自己就是拽着捆着拴着?果然这老东西是不会允许被自己“骑在头上”的。
沙棠索性眼睛一闭,睡上一路。
等他醒来,他躺在一张柔软的白色床铺上,而他的父亲已从白蛇的模样变回原本的样子。
一头与他一样的白色长发,柔软地披散在父亲的背上,雪山的白蛇,黎明之窗的创始者,他的父亲——浮士达维尔,正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笑着看他。
沙棠身上的衣服也被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衫,浮士达维尔伸过手去摸上自己儿子的头顶。
沙棠嫌弃地想躲过面前人的触摸却被浮士达维尔拽着头发强行面对父亲。
浮士达维尔依然眉眼带笑,但他的眼底却没有一丝笑意,只有一片冰冷的深海:“你没有忤逆我的资格,沙利。”
沙棠捂着父亲的手,他的头发被拽的生疼,头发都仿佛要被拉拽下来,他敷衍地说:“我知道了,请你放手。”
浮士达维尔抚摸着沙棠的长发,他暗红色的眼眸,竖状的瞳孔注视眼前的孩子,说:“回头我会让秘书把黎明之窗的工作事项,以及对你的安排告诉你,父亲还有事要去做,请容我失陪。”
沙棠挥挥手,巴不得道貌岸然的父亲离自己远远的。
等浮士达维尔一走,他就趴在床上捶打床铺——自己好好的完美的准备多年的计划,被破坏得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