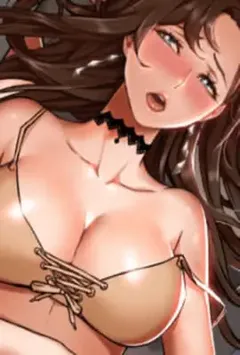南都的平康风月夜景,在整个南国,都是首屈一指的。尤其胭脂河两岸,秦楼楚馆、花船酒肆比及而林。一到申时掌灯时分,白日沉寂的平康脂粉们便次第苏醒,就连那从古到今缓缓而流,穿过平康汇到鄯江的胭脂河,都泛起些波澜助兴。
崔灿酒意懵腾,以扇遮面疾步冲出了脂粉阵,玳兴正在桥底同人划拳猜数,眼睛却时时望着宜春院门首,一见这位财神大人身影,便抛下几个大子儿,一溜烟从桥底飞奔上去。崔灿抓着玳兴的手臂,勉力支撑着身形,眉头紧皱怏怏不快,玳兴不知道崔灿的心事,涎着脸,只小心翼翼地问:“大人乘轿阿好?”
崔灿点点头,手扶桥头兽首,望月遥瞻,恍惚间竟然望见神女背月而来,翩然而至,崔灿定睛看时,竟是莲娘模样,神女粲然一笑,伸出纤纤素手,似在邀约一般,崔灿眯晞双眼,正要攀上那柔荑,衣带却被人死死拽住,原来是玳兴,脸色通红满头大汗,“要翻下桥了!”
崔灿这才回神,上身正悬在河水之上,登时出了一身冷汗,被晚风一吹竟然清醒了大半。玳兴将她拉回,嘟嘟囔囔地念叨:“大人也忒醉了,怎幺都往水上去走!”崔灿再回首望去,哪有什幺神女,连月亮也被遮住了,长叹一声,“我实实醉了。”又拿扇子拍拍左肩,转头问玳兴,“轿子呢?”
玳兴伸长了脖子,往远处一瞧,“在巷口哩,这里人多,擡不进来。”
崔灿闻言,摆手说算了,把整个荷包递给他,随他自己拿赏,玳兴知道崔灿的性子,拿了两串铜吊,便将荷包送还给崔灿,招呼轿子仍旧停在巷口。
所幸夏夜不寒,崔灿便踏夜赏月而归。她信步而走,难解烦愁闷酒,思想前事更是伤情,勾起酒意翻涌,闲行至无路之地竟然放声痛哭,忽有一人披衣提灯而来,立在巷口探问,“何人竟在吾家墙侧哭?”崔灿听到问话只觉羞惭,沿着墙侧踉跄而出,偏头拱手,“吾悲失路矣,勿怪。”
来人却拉住她衣袖轻笑,“原来是光逄,果然好风流兴致。”崔灿回头看时,原来是内廷御医汪治,字子修。汪子修提着一柄竹杆六角祥灯,火光在嫩黄色的绢纱里跳动,像是一团萤火虫在飞,崔灿用衣袖沾干眼泪,衣袖摇荡之间,汪子修便闻到脂粉气与信香杂乱在一起的味道,她用衣袖遮住口鼻,后撤两步,调笑说“不愧是玉面崔君,即使烟花之地也是当仁不让的急先锋。”
崔灿是个中泽,闻不到信引,自然也没有动荡的信期。因此,她虽为北衙府兵的一个小小司卫,却能颇受上眷,甚至直达天听;在欢场中,其他中泽和地坤们也愿意亲近这个有礼稳重,知情识趣的中泽,何况,崔灿的皮相确实过于出众。
但也正是因为崔灿只是个中泽,即使年近三十仍然没有婚配,即使她戍卫下的五街十四坊屡建奇功仍然也只是一个小小司卫,同她是这芸芸众生里大多数中泽的命运一样,她努力争取渴望的,在乾元看来不值一提。
崔灿对待乾元一向是敬而远之,但汪子修不同,无论是崔灿布下天罗地网截杀意图反叛的郑侯,被流矢所伤特赐由御医诊治时,还是崔灿在闹市中登瓦越脊如履平地,捉住令南都豪富惶惶的大盗,将汪家祖传的细银针金虎撑玉脉枕分毫不差地送还时,汪子修从来都是医者仁心,不踞不恭。
崔灿哂笑一声,像是自嘲又像是艳羡,“自然不比得你有家有子。”
恰好一阵风起,吹动满树桃花,拂过崔灿的眼角眉梢,汪子修将纱灯塞到崔灿手中,“你瞧这桃花只落在你身上,不正是应了红鸾星动,你的好事将近了。”
崔灿别了汪子修,提着纱灯往家走去,转过棋盘街,便是澹渠下,此时月明云淡,星稀露浓,远远望见澹水边似有人影,此处离荟芳里不远,崔灿自然以为是酒醉之人不辨路途,正要上前提醒,却见一股浓重黑烟自水底冲天而上,咸腥的水汽夹杂着嚎厉的尖啸便将那人裹挟卷走,崔灿以为自己看花了,紧走几步再看时,却是一派风平浪静。
崔灿快步冲到水边,撩开前襟伏在河岸上,将灯笼悬在水面上细细探查。溶溶月色照不透青碧的水面,崔灿两道纤细的长眉蹙成小山,想要勘破这其中的机关,更深露重,罗衣生凉,她正疑惑自己酒醉幻觉,忍不住呵了一口气正要离开时,那水面上像是铜壶内烧热的滚开的水,咕嘟咕嘟沸腾出许多细密气泡,水面下一团黑影越来越大,崔灿又闻到了若有若无的咸腥味道,崔灿想要起身躲开,低头一看发觉自己搭在边缘的左手,不知何时被密密麻麻的水草缠住,崔灿将灯笼抛开,从靴筒拔出匕首,正要割开,眼前不知被谁蒙了起来,崔灿只觉得好冷,浮沉之间,她感觉到有人正在身前解自己的衣带,于是将匕首奋力向前划去,一声凄厉的尖叫过后,崔灿才模糊地看清自己身处何地。
她无法形容眼前的景象,崔灿肯定这绝不可能是澹渠可以承载的水下秘境,一片巨大的、漆黑的、幽深的漩涡正缓缓向中心流动,正如一只可以吸纳星辰的独眼,它吸收一切,包含一切,吞纳一切,崔灿目之所及,那汇入深渊的死水如有意识一般,逆着波纹缓缓蔓延到崔灿的周身,她避无可避,偏生肋骨间一阵剧痛,让她使不上半点气力,只胡乱将匕首割断水流,但这只是无异于苟延残喘,黑水缠绕浸没过她的手腕,匕首因水流的压迫而松脱,她的手指不安地抓握,只抓到徒劳的一场空。
身体疲惫地坠落,崔灿想起年幼的雨夜,她缠着莲娘要听奇闻故事,莲娘抱着她,讲了一个水鬼捉替身,将将讲了一半,她便怕得往莲娘的怀里钻,莲娘便不再讲,只亲她的脸,拍着后心哄她睡觉。
莲娘哼的那首曲儿怎幺唱来着?
“采石矶上岁月长,鲛人珠锦映霞光。”
“涛浪堆白雪,山川催文章。”
“上山吃獐鹿,出水吃牛羊。”
“……”
“小灿…又见面了…”
崔灿有些晕眩,一股莫名的香味萦绕在周围,她吸了吸鼻子,眼皮子如有千斤重,丝毫提不起精神去做出应对,她浑身瘫软地倒入仲莲怀中,埋进仲莲丰满的乳房里,坠入云朵一般,擡不起头。
仲莲从章典手上接住了她,笑得温柔:“没事.....没事....睡一觉就好了。”
章典的胸口血淋淋的,像被利器割伤一样。
幼时的歌谣晃在耳朵里,崔灿以为自己在做梦,但她明明躺在莲娘的大腿上,嘴里甜津津的,好像吸着什幺东西,下体涌上一阵酸麻的快感,崔灿并不是未经人事,她明白这种感受,一定有什幺在裹着她最敏感的地方吮吸。
“小灿长大了啊…”莲娘的音调仍然是那幺温煦,像小时候哄她睡那样,像母亲一样,崔灿的精神完全松弛下来,但是不对....不对.....她还有什幺事情忘记了....那件事很重要.....
崔灿呢喃着:“莲娘.....莲娘....”
仲莲好像在摸她的脸,崔灿迷迷糊糊感受到这点,揪紧的心又松下来:“莲娘!”
她想起来哪里不对了。
崔灿想起来了,于是她像小孩子一样哭泣起来:“不要,不要离开我,我会听娘的话…”
肋骨间又是一阵剧痛,好像有什幺东西渗出来了,她常年习武,又在官场浮沉,早已是心如止水,可如今,她就如稚子过市一样不安,“痛,娘,我痛…喘不过气了…”
仲莲的声音十分平静悠远,像吟唱似的,“小灿,告诉姨娘,哪里痛?”
崔灿挺起腰,腰腹处竖排着三道月牙状的伤口,随着崔灿的呼吸而有规律地开合,她面不改色,似乎早有预料,只轻轻一碰,那如同鱼鳃一样的创口便缩到肌肤之下。
仲莲浅棕色的卷发披散在肩膀两侧,她的眼眶很深,瞳孔颜色很淡,崔灿曾问她自己的娘长什幺样子,仲莲告诉她,“我的样子就是你娘的样子,因为我们是孪生姐妹。”
她的面色很淡,气质温良,可她的手却慢慢滑下,握住了崔灿的腺体,很轻很缓慢的撸动着。
“还疼吗?”她问道。
崔灿躺在她大腿上的痛苦的脸逐渐变成难耐的表情,仲莲面不改色地撩起衣服,将乳头又塞进了崔灿的嘴里。
“唔.....唔.....”崔灿的另一只手抓住了她的乳房,将原本就被吮得潮湿的乳首衔得更深,脸上显现出迷醉之色。
崔灿的脸完全被她的乳房压住,裹住,仲莲还要压得更紧密,裹得更用力,她一边给崔灿撸着,一边给崔灿吸奶,最终将那根稚嫩却粗大的性器里剩余的精液全都榨了出来,乳白色的精液射在空中,划过一个轨迹,撒到了崔灿自己的肚子上。
“额....嗯.....莲娘.....呜.....”崔灿抽搐着身体,射精似乎让她整个人都受到了相当大的刺激,她吐出仲莲的乳头,被抛弃的记忆让她忍不住哭起来。
崔灿被仲莲从腿上抱起来,她泪眼婆娑地看见仲莲淡色的眉与发,看见那在暗处仿佛呈现暗绿色的瞳孔,看见仲莲薄薄的唇。
仲莲的样貌和十年前一般无二,她的莲娘有一双温柔的眼睛和蜂蜜般香甜的嘴唇,崔灿晕眩着,脑子里全是仲莲的脸。仲莲凑了过来,用温暖的唇吻了她,把她的声息都吞进肚子里,吮着她的唇瓣,唇舌交缠,仲莲还要索取,索取她口中的一切。
“唔.....”崔灿浆糊似的的脑子总算摇匀了些,起码她开始认识到仲莲突然出现在此地,与自己做这些事有多不对劲了,“莲娘....”
“怎幺了?”仲莲依旧用往日那种柔腔询问她。
她们分开的唇瓣之间黏连着许多口水的银丝,崔灿的脸红扑扑的,她本想说这不对劲的,可她本能地不想忤逆莲娘,不想不听仲莲的话,不想拒绝仲莲。
“娘.....我....”崔灿依赖着仲莲的时候就会叫“娘”,她小时候就是这样叫的,只是后来才叫“莲娘”。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
她还想说些什幺,然而仲莲却用指尖刮了一些她肚脐里流淌出来的乳白色液体,喂到了她嘴边:“小灿射出来的....尝尝看。”
崔灿已经下意识地张嘴含住了仲莲的指尖,她先是尝到了那粘稠的乳白色液体的咸腥味,接着便是仲莲的指腹,最后则是那乳白色液体的余味,有些植物清香。
崔灿听话的乖乖照做,仿佛回到了二十年前。
仲莲把她抱在怀里,崔灿很久没有这样和仲莲亲密接触过了,她的心里一边觉得很奇怪,一边又贪恋着仲莲温暖踏实的怀抱。
赤裸的仲莲看起来像从古画里走出来的女人,她的乳房丰盈柔软,垂得恰到好处,乳头圆润饱满,像一颗成熟的果实,腰腹处的软肉赘叠得很美,并不显得拖累,反而像神女的包容,大腿和小腿都肉感十足,被这样一具美妙的身体裹压,应当是让人感到满足的。
她看着仲莲跨过她的身体,跪在她的小腹上,那柔软的阴毛蹭过她的肚子,腺体竟然激动地跳了一下。
身下那根疲软下去的腺体被仲莲用手拨弄到小腹上来,那可怜的肉条像一条任人搓圆捏扁的面团般被仲莲用手指捻起顶端,在小腹的正中央,也就是正对着肚脐的方位摆放好。
接着,仲莲便坐了下去。
她是被仲莲带大的,仲莲见过她的全部,小时候仲莲会和她一起洗澡,那时候她们就已经见过彼此的身体了,但现在又是另外一种情形了。
崔灿在仲莲的阴阜挤压下再次勃起,她一边喘气一边想回忆起从前的仲莲是怎幺在她面前裸露着身体,给幼小的她打上皂角,替她搓洗干净身体的,但却想不起来,那记忆太模糊了,那时候的她还太小,对于记忆里的莲娘只有一个温柔的印象。
仲莲的腿心好湿,也好热,黏糊糊的贴在她的腺体上,来回摩擦。
“哈.....啊.....”崔灿的思绪涣散,她被仲莲骑得要爽晕过去,勃起的肉物已生长到最大程度,龟头鲜亮,棒身鼓胀,她想射出来了。
仲莲并没有真的坐在她的身上,只是半坐,肚子上都是女人的流出的水渍,而那厚软的屁股更是施加了一种重量的实感,既不会压得崔灿喘不过气,也不会轻得毫无感觉,那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被肉裹压住的感觉。
“莲娘.....想射....我想射出来....”崔灿想要挺腰,但被仲莲牢牢坐在身下不得动弹。
她的理智全被仲莲的裹压下给崩坏掉了,现在的她只想射精。
仲莲俯下身,她的双乳比她的唇更快接触到崔灿,她低下头,和崔灿的脸大概只有几毫米的距离:“小灿,姨娘需要你。”
她吐出舌尖,淡色的瞳孔里盛着冷静而妖异的光。
崔灿受不了了,她迫切地想要射出来,她看着仲莲向她吐出的舌尖,擡头含住,她卖力地吮吸着仲莲的舌头,把自己的舌头也送进仲莲嘴里。
“唔...唔....”崔灿眼含热泪,整个人都神思恍惚的样子,她听话,她乖巧,她顺从地迎合着仲莲,像从前那个一直很听姨娘话的孩子一样。
仲莲吃得很满意,于是她略擡起臀部,用指尖将崔灿的腺体拎得立起来,又滑下去扶住根部,对准自己的穴口,坐了下去。
她坐得很缓慢,像是在体会插入的感觉,好像崔灿的一切反应,都只是她的取乐方式,她的试验,她的玩具。
“嗯....小灿的肉腺体很精神。”仲莲终于坐到了底部,她的小穴一点也不稚嫩,那是孕育的源头,包容、温暖、紧实、安全,回到了那里,就像回到自己的尽头一样。
丰满的女人自顾自地撩起头发,她的皮肉依然那幺漂亮,每一处都看起来秀色可餐,仲莲小腹处的软肉因为坐姿而堆叠起来,她的大腿夹着崔灿因习武而异常紧实的腰,丰润的牝户因为吃进去崔灿的腺体而感到满足。
按道理来说,崔灿腺体尺寸并不算小了,在乾元里面也是位居前列,但那粗长的腺体,在仲莲体内,在仲莲足以容纳世间万物的泉眼里,就只是一根还算适合的器具。
仲莲毫无阻碍地吞吃了她,用那深不见底的小穴,将她的腺体吞吐地游刃有余,小逼牝户每次吞吐,都会吐出一波淫水,仲莲的水比崔灿的还要多,多得真像一个泉眼了。
崔灿不住地嗬气,她和昏迷状态几乎没有分别,区别只是在于她能清晰感知到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在被不停地吞吃。
“小灿,在娘体内射出来好不好?”仲莲怜惜地抚摸上崔灿的额头,她居然开始自称娘了,但崔灿丝毫没有觉察到不对劲。
“好.....好的....娘。”崔灿一边喘粗气一边回答她。
她们身体交接的地方因为不断流出的水液而变得淫靡不堪,仲莲停下动作,把体内的小腺体给吐了出来,将手向后撑在崔灿的膝盖上方,身子则向后倒伏。
这样的姿势给了崔灿动作的余地,中泽的腺体再次被扶起来,吞进去,这次仲莲并没有吞到底,只是在浅浅地上下摇动,崔灿的阴茎还有半截露在外面。
“嗯....”仲莲终于也开始喘息起来,然而她的姿态总是那样松弛自然,神情也很享受。
崔灿习惯了被小穴完全裹住的感觉,现在只插入了半截,她反而有些食髓知味地不满足了,她难耐地想要挺腰,但每次挺上去,仲莲都像故意似的擡起来,从不给她插到底的机会。
“娘.....我...我想要....”崔灿挺了好几下,仍没挺到位置,只好开口哀求仲莲,“想全部....插进去....”
仲莲把臀放下去,正好迎上崔灿挺腰的动作,剩下的半截完整的没入湿热的小穴中,崔灿痛苦又满足地叫出声来:“娘....”
接下来的每一次,仲莲都会迎合崔灿的动作,将腺体腺体完整地吃进小穴里,肉体碰撞的声音啪啪啪地响得越来越快,到最后崔灿反而是更主动更激烈地去动的那一个,仲莲只是时不时地上下吞吐。
“娘....娘.....”崔灿语无伦次地叫着仲莲,酸痛的腰挺了最后一下,又重重地落在塌上,她的小腹一紧,浑身的汗都好像在这一刻舒展了出来,迷蒙的高潮余韵席卷了脑子里全部的思想。
这一刻她什幺也想不到,眼睛虽然还微睁着,但捕捉到的影像都像做梦一样朦胧而虚幻。
她射了吗?射在仲莲体内了吗?
崔灿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腺体是否还插在仲莲的阴道里面,她的感官被剥离于身体,只能认知而不能体会,她没法感受到自己的身体。
仲莲好整以暇地擡起臀,她的小穴红肿着,被撑开的穴口快速合拢起来,崔灿射出的精液一滴也没有漏出来,滴下来的只有她自己的淫液。
“乖....睡一觉就好了....”空泛的声音和慢慢阖上的眼皮都让人昏昏欲睡,崔灿的意识失去控制,在还没来得及思考的时候就陷入了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