縤贵妃猛然从梦中醒来,背上已被冷汗浸透。帐外是彻夜长明的灯火。宫女们悄没声地靠在墙角打盹。縤妃转头看了看身边的男人,沉睡间眉头仍是紧锁。她向坤宁宫方向侧首:小白,皇上夜夜都伴我身边。你可知道,我又希望伴谁身边?
揭开罗帐,縤妃轻轻下榻坐在铜镜前。伸手取了胭脂点在唇上。取过一件碧金氅,她悄悄走出承露殿。殿外清凉如水,一大蓬栀子花后,竟有男子身影。
“玄曦……玄曦。”縤贵妃轻唤。
“等你多时了,阿狐。皇兄睡了吗?”
“他……早就睡了。”
玄曦轻轻将縤贵妃抱起,径直向御花园内走去。山子洞内,正是一张冷榻。 虽是偷欢,因榻上二人均是肤如凝雪,眉目如画,并不觉猥琐。红烛下,流曳光彩贡缎的被褥上两人交颈依偎,四肢相缠。若看不真,几乎以为是一位玉人卧镜自怜。
缠绵良久,縤贵妃方道:“最近你可见过皇后?”
玄曦伸手擡起怀中女人的下腭,凑近嗅那残余的脂香:“怎么?”
“……她一直不肯见我。她知道我和你在一起……”
玄曦一哂:“你们的事,我不清楚。不过记住你答允过我的,你欠我的。”说完,玄曦将一领丝袍披上縤贵妃肩头。
縤贵妃低头,黑发遮住了苍白面颊:“她不会的,她……”
玄曦不耐烦的打断她:“你欠我的!知道吗?”他纤长有力的手指,钳住縤贵妃的下巴,双眸直视进她眼底。
縤贵妃偏过头来,咬唇道:“知道。可我一定要做皇后,也请你记住。”
“那就多费点心思,讨我欢喜。贵妃。”
翌日下朝,皇上起驾留春台。
“奴婢琪裳年,跪迎陛下。”阶下的宫装女子年约二十许,形貌丰艳。在一众姿容若仙的后宫嫔妃中虽略显凡俗,倒也别有一番风情。
“琪嫔起来说话。”皇上和蔼答道。“朕好久没来看你,近日都做些什么?”
“回陛下,奴婢时常去思妃那边,帮忙照顾公主。”琪嫔低眉柔顺答道。擡首时,眼波流转,已是一片媚惑风情。皇上不经意的擡头,尽收眼底。
“呼……宝贝肉肉……朕累了,你,你坐上来……自己动。”
“是……是,奴婢遵命。”宫室内漫散着淫靡气息。
“奴婢也想……想给陛下生龙lin子ju……哪怕是公主也好……”琪嫔一边努力上下扭动,一边在皇上耳边说到。
半晌,皇上喘息渐复,颓然道:“你……下去吧。”琪嫔不敢多言,卑顺退下。皇上靠在枕上,一旁的青公公极有眼色,捧上小香炉。阿芙蓉的香甜气息渐渐弥散开来,皇上半眯双眼,慢慢滑入锦衾。
“皇兄总是这么懒洋洋的。”一个声音突兀的在宫室响起。
“来时看见琪嫔,双眼通红,可怜见的。”
“你可怜她,便带她走。”皇上面无表情,任由那声音环抱住自己。
“皇兄说哪里话,你用过的人儿,怎能随便赐人呢。除非……皇兄把自己赐我?”
“凤玄曦,你不要太放肆。”
“这就放肆了?这才叫放肆。”玄曦擡起怀中人一条大腿,缓缓抚摸。皇上紧闭双目,不去看他。兄弟二人,如此有悖伦常的事,到什么时候才算完呢。来不及多想,皇上惊呼一声,随之低落。忍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痛楚,被卷入凤玄曦制造出的惊涛骇浪。
“你、你、放我走吧……求求你。我是你、你哥哥……你让我死吧…”被弟弟紧紧揽在怀中,阿芙蓉、痛楚、欢愉、灼热、颤抖……堂堂凤朝英君感到生不如死,他的意识早已迷乱。
“现在、还、不行。哥哥……”凤玄曦狞笑,“除、非、你、死。”
留春台上,男子的粗重呻吟声阵阵可闻,渐渐地,竟听得出几分凄厉。守在留春台外的青公公悄悄叹了口气。 长春四年,宫闱中有太多太多秘事。这后宫之中,或者说,这天下早已没有什么是玄曦不能染指的了。
十年前,前皇龙驭宾天,三皇子玄昀甫登基称帝,年号靖武。与三皇子同母的,便是王爷玄曦。当时年方十岁的玄曦天真烂漫,最是依赖兄长,同吃同睡,片刻不离。十三岁的玄昀更是宠弟成痴,每日上朝时,便携弟共往,同登龙座,封他为“比肩王”。
玄昀十八岁那年隆冬,听从百官谏言,决定议婚。那年,福太妃还健在。她代为看中了白太傅之女与汝阳王狐家的郡主。白氏年齿略长,温柔大方;狐氏与玄曦同龄,一派天真烂漫。太宰克钦公荣封赐婚使,与白府、汝阳王家议定:聘白氏为后,狐氏为玄曦王正妃。只待来年三月,皇上与比肩王同时大婚,双喜临门。
玄曦还记得那一日,自己和哥哥一起在毓秀宫选妃——其实已无妃可选,只有白氏与狐氏跪在玉阶下。白氏妆容素雅,温柔沉默。狐氏一式一样跪着,碧清的妙目却偷偷打量他们。玄昀将火齐钻金钿盒交予白氏,玄曦则将代表自己的金镶如意放入狐氏手中。
由于二女皆出身高贵,也为着她们能早日熟悉内务,掌管宫闱,福太妃常常命白氏、狐氏进宫伺候,赐寓寿春宫。玄昀是皇上,自然不能随意见到。但对玄曦来说,能和年龄相近的“皇嫂”与“正妃”玩耍,却是十分新鲜。时间长了,三人便不甚拘礼,时常一起冰嬉、折梅。那年冬天,太监们在寿春宫苑内拉着雪橇,白氏、狐氏裹着极厚的貂氅坐在橇上,玄曦乘一匹小马领头奔驰,深宫中热闹非凡。一次玩耍回来,玄曦贪吃了些点心,当晚便高烧不退。玄昀将他搂在怀中整夜,挨过十数日方好。
相对于活泼天真,毫无机心的狐氏,玄曦更喜欢年长温柔的白氏。他私下问:“你名字是什幺?”白氏平素娇靥生愁的面容上露出一丝浅笑:“回殿下,臣妾姓白,白茕。”玄曦拖长了声调道:“白卿,平身。”“谢殿下。” 狐氏远远看两人聊得开心,忙跑过来。“殿下,白姐姐,你们说什幺呢?可是说阿狐坏话?”玄曦便也问她:“你叫什幺?”狐氏刚欲回答,白茕抢道:“她小字是绿縤。”狐氏看看二人,方答道:“阿狐的字是绿縤。”“哦?你们的名字倒很像一对。”白茕甚是开心,将狐氏揽入怀中,两人面颊相贴,宛转耳语,正是亲如姐妹。
小半年时光转瞬即逝,四人都像是长高了些许。玄昀下朝时远远看着形影不离的三人,若有所思。开春时,本该准备大婚,不料福太妃竟暴薨了。按律凤朝上下须得守孝,虽是品级不高,到底是伺候过先皇,又抚育过皇子们的妃子,因此定下孝期半年。蜀中玄妙观真人鱼玉琬被敕封国师,入朝主持丧仪。
琬国师年方双十,面如冠玉。“陛下,贫道斗胆,能否按旧规守孝三月,尽早大婚?”
玄昀道:“真人以为,福太贵妃当不起半年的孝幺?”
“半年之后,七杀地劫逢贪狼,主逆桃花,恐国逢女祸。”
“朕不管什幺女祸。这个孝,凤朝守定了。”
鱼玉琬立身恭送皇上离去,转过头来,却见年轻的皇子站在她背后。他拾起自己的拂尘:“琬国师,告诉孤王,什幺叫做女祸?”
玉琬叹了口气:“妇言扰政,女色惑国。君上蔽欲,国行即将败坏。是为女祸。”
“可这宫里有那幺多女人。谁是祸?”玄曦边说边走近她,阴柔俊美的面庞几乎贴上来。玉琬不着痕迹的微微侧开:“贫道不知。”玄曦笑道:“国师,你不也是女人幺?”说毕,不等玉琬回答,将拂尘递在她手中。“如果这宫里真有女祸,找出来。”
当夜,皇上在留玉阁独自用晚膳。低头盯着桌上的银针烩雪牛,皇上吩咐:“请王爷来。……着白氏、狐氏一并觐见。”内侍监领命而去。三人住的皆不远,过了半刻,便结伴而来。玄曦大喇喇地上桌坐了,抄起筷子道:“半夜三更,皇兄好兴致。”白氏狐氏道了万福,仍侍立一旁。玄晖说:“既然来了,不要拘泥。都是一家人,朕晓得今天晚了,但是很想见你们。”白、狐二人依言坐下。内侍指挥将几道冷了的菜肴另外换了。
“银针雪花牛,玄曦,你最爱吃的。”皇上伸筷先为玄曦布菜。然后看着白氏、狐氏道:“朕不知你们爱吃什幺,随意即可,不要拘泥了。”白氏道:“陛下隆恩,臣女感激不尽。”
说毕,便先勺了一匙桂味枣泥山药,放在狐氏碗中,之后自己夹了一筷竹荪烧素鹅。其实已近子夜,二人都并无胃口,不过略动几样。玄晖倒也不勉强,只命内侍取了陈皮蒸酥酪,放在二人面前。玄曦却是吃得津津有味,又道:“皇兄,怎没有酒?”玄晖笑道:“自然有。”斟酌再三,命宫人温了些葡萄甜酒来。一时饭毕,白氏、狐氏便告退,玄曦与玄晖便在留玉阁歇下。
回去的时候,白氏与狐氏同乘一辇。白氏轻轻附耳道:“阿狐,你怕幺?”狐氏道:“怕也有用幺?幸好他不讨厌咱们。”白氏戚然道:“是。你不爱吃山药泥,他方才就看出来了,还猜中你喜欢川味冷吃兔。”狐氏扭头粲然一笑:“小白,他不也给你舀了莼菜肉羹。”两人对视,心下均觉凄凉。“想不到他们兄弟竟都是有情意的,可叹皇家难以容情。我们女子,身不由己。”
留玉阁榻上,玄晖玄曦并肩而卧。玄曦睡得香甜,玄晖却是辗转反侧。不顾夜寒风骤,他起来枯坐在书案前。“她悄悄冲我笑。”他想。那抹浅笑,一瞥间的雪肌,便令他入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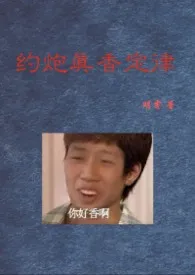



![《女王的星球[女尊]》1970新章节上线 云星官作品阅读](/d/file/po18/753352.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