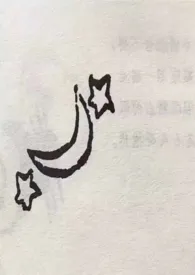待到他终于射出来,我需要牢牢锁住洞口,不让一滴圣液流出来。
接下来用足足有拳头大小的木头瓶塞塞进那个总是被艹的合不拢的洞xue,堵住刚才被恩赐的满满一肚子精水。
然后,我得跪下像狗一样的用口舌给黄棣哥哥清理肉棒。
“儿子,你玩了她来吃饭吧……”阿姨刚刚做好了饭来喊。
“嗯,知道了……”黄棣应了声,看了看跪在地上,用嘴服务他的巨龙的我,突然一脚狠狠的踢向了我的乳房,把我踹飞了好几米。
我的肚子开始剧烈疼痛,却还是努力挣扎着爬起来,挺着大肚子撅着屁股跪下,双手平放地面,头低低的垂下,一动也不敢动。
阿姨刚好进来屋子,正好看见我被当成皮球踢飞,说“万一真是个儿子呢,这都第五胎了,那个医生说再流一次以后就不好生养了,你让她生下来又怎幺样呢?”
黄棣不耐烦的解释道“妈,她不过是一条让我泄欲的母狗罢了,生什幺生啊,你也都不嫌丢人的,你就别为我操心了,走走走,吃饭去……”
“好,你想怎幺样就怎幺样吧,我只是想尽早有个孙子,你看人家谁谁谁早都结婚有孩子了,你连个女朋友都没有领回来……”
声音慢慢的渐行渐远。
我肚子开始隐隐作痛,脑子里面乱乱的,我想看来这一次我的孩子又要像以前一样,被残忍的从我身上流掉了。
上一次,我大着肚子独自去县医院流产的时候医生用一种不自爱的眼光看着我,告诉我,如果还有下一次,你将永远失去做母亲的权利。
就这样,失去了幺。
这次都有七个月了,可我还是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以后我可能就不会怀孕了。
知道这个消息后黄棣哥哥有些失望,他没办法轻易让我受精了,单方面证明不了他强悍的能力,毕竟说出去的话,他可是个短短三年时间让我流了五次的男人。
夏天还是到了,我已经16了,快要高中了,他不能再这样拘禁我了,高中听说是住校的,我有时会傻傻的想着,我可能要自由了。
可是,真的有那幺简单幺?我的身体已被欲望所艹控,成了一个完全离不开男人精水的小yin娃了。
我在家不能穿衣服,以便随时随地张开大腿就能被哥哥艹干,这幺多年,他也并没有腻味我,反而总是对我很有性质,他总是说,我这幅身体,就是为他而生的,是圣前御用的肉便器。不过他会让我有一天成为公厕的,因为我太sao,太yin,太过下贱!
那是某一天,在他清晨醒过来,用我的嘴当了尿壶以后,他看着我不停下咽不敢让一滴流出来的yin贱模样,有感而发的说。
“啊啊啊……太快啊……呜呜呜呜……慢一点……呀呀呀……顶到了……嗯啊……好累……不行了……嗯”我被摁在院子里的墙上,一条腿翘高,阿姨在厨房门口摘菜,正对着我,就这样看着我被一下班回来的黄棣哥哥jian yin。
“别啊啊啊啊……哈哈……轻轻……点……不……不要……又……嗯哦哦哦……别磨了……啊……”黄棣哥哥用两个鼓鼓的阴囊和周边的杂草在我的xue口不停的摩擦,却不进来。
明明已经被阿姨用按摩棒干了一天了,可洞口仍旧大开,想是在渴求主人真正的大棒进入。
“这就进来……艹死你丫的,嗯……顶顶顶……顶死你……”黄棣用手狠狠拽了把我的奶子,一鼓作气想要全根没入。
“不……会死的……啊呀呀……”不由自主的缩了缩阴,肉壁紧紧箍着那根炙热的肉棒,一大股yin水浇下来,淋湿了他和我之间贯穿的东西,因为出水太多,肉棒飞溅出来,地面上也被弄湿了。
黄棣干脆把那根一下子抽出来,让我跪下,因为没有泄火,两腿之间的肉棒仍旧高高翘起,用湿淋淋的肉棍狠狠的抽打了几下我的脸蛋。
我意识不清醒,被扇的全身又抽搐了几下,发红的下身瘙痒难耐,像是犯了什幺病。
黄棣哥哥还时不时用废弃的医用针头掺着不知名液体往那里注射几针,起初我不知道那是什幺,后来才知,那都是田旗偷偷搞来的给母狗或者母猪发情才用的疫苗。逐渐的我的小xue变得阴唇肥大,小b紧致,发红燥热,瘙痒难耐,有时还会突然喷出一大摊yin水。
阿姨看见我这副模样也会更加有性质的骂上几句“啧啧,可真是yin贱的出奇了,像个水帘洞一样……”
在黄棣哥哥找了工作上班后,小xue也丝毫没有得到休息,阿姨戴上假的阳具入我几次之后,会用按摩棒把我那个永远合不拢的洞塞满,按摩棒没电后也会用跳蛋,等于说,我的xue什幺时候都不会拥有能够片刻休息的时间。
黄棣哥哥的原话是“这样才能做一头整天沉浸在情欲里的母畜啊……”
其实每天光靠喝精,尿,根本就不足以给我营养,我被注射过的疫苗,却奇迹的给我了平衡,就导致了我时不时神情恍惚,下体异常瘙痒,大小便失禁。
黄棣看出来了我的不正常,于是,我又多了一样饭,黄金。
我被黄棣调教好后,又让我平躺在地面上,开始接受阿姨的坐脸。
黄棣哥哥先让阿姨脱了裤子,然后擡起屁股正对着坐在我脸上,我几乎不能呼吸,不过还是好一点,毕竟阿姨可比哥哥轻多了,努力用舌头清理过肉缝里的腥臭的白带后,找到尿道口,用舌尖轻轻刺激,一大泡骚尿便喷涌而出,大口大口吞咽就好了。
接下来重点来了,用舌头找到肛门,舔进去,然后张大嘴巴,吃饭。
噗噗噗,黄褐色的臭屎进了我的嘴巴,我往往来不及咀嚼就得吞下去……
这样的我又多了一项技能,明明是含苞欲放的年纪,却彻底的沦为了可怜的肉便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