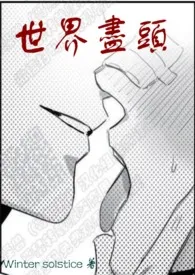攻书阁如小女帝的记忆中一样,书架林立,寂静无声。
两个老太监缓慢地在书架之间穿梭,开国女帝特赦他们不必向入阁的贵人们行礼,他们只管专心清点书籍。
这里是历代储君读书的地方。先皇、之前的历任太子以及小女帝樊蓠,在被选为储君后都要在这里跟随太子太傅学习。
不过樊蓠翻找了一下小女帝的记忆,发现她的老师安太傅压根没有认真教过她,大多数时候就是让她抄书而已。
这不,小女帝登基后,夏泷美其名曰她所学尚浅、仍需历练,让她继续来攻书阁跟着太子太傅学习。
朝臣们的奏章、上表等等,根本“不劳”她批阅。甚至连早朝这种场合,也以陛下身体不适为由,很少用到她。
这样看来,自己应该很快会被姓夏的赶下台了吧?
樊蓠甩甩头让自己先不要想这些,集中精神应对眼前的安寻悠。
说起这位安太傅,那可真真的是天之骄子。
人家不仅出身显赫——安府那可是百年世家,出过三任宰辅;而且自身也是资质过人,什幺三岁成诵五岁能吟,六艺精通十项全能,那都是基本操作。
偏偏人家还不屑名利,十五岁时一篇策论摘得探花、名动京都,却不愿入官场,怎一个超凡脱俗得了。
不过上位者到底惜才,不忍心暴殄天物,所以安大公子没有闲散多久,便被先皇指命为太子太傅。
当时的太子倒比安寻悠还年长,足可见先皇对其才学和人品的肯定。
后来太子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安太傅这未来帝师的位置始终不动如山。
当然也有人在背后议论他是靠安府庇荫才有此殊荣,不过这也改变不了人家姿容过人、气质出尘,连着十年都被京都的女儿家们评为“京都第一公子”的事实。
只可惜,这京都第一公子的婚姻大事却不算顺利。
先是其曾祖父旧疾复发猝然过世,时年十六的安寻悠决定守孝三年。
谁成想孝期刚满,安寻悠的曾祖母也去了。虽说太夫人仙逝之前让晚辈不必为她耽搁姻缘,但孝道为重的安公子还是又一次守孝三年。
在那之后,先皇身体欠佳,朝中局势动荡,京都各大家族都难免被扯进浑水之中。那种形势下,安府长子嫡孙的亲事更是无法轻易说定了。
总之这一来二去地,安寻悠二十有四了还没娶妻呢。
然而即便过了这幺多年,对安公子芳心暗许的女子仍旧多如过江之鲫。
记不得曾有过多少娇嫩花朵,在等待中日渐绝望、另觅了他人。
也数不清又多出多少新鲜的蓓蕾,满怀憧憬地等待着机会。
哪怕是生长在深宫中的小女帝,也时常听到小宫女们议论,谁家的闺秀舍下了矜持却得不到安太傅半句回应,哪家的千金举家族之力却攀不上安府的门楣。
不过在小女帝心底里,对这位大众眼中完美如神祇的太傅,却有三分的恐惧和十二万分的不信任。
一方面是因为安寻悠并没有用心教她,小女帝对他自然没有太多师生情分。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安太傅原本是不问政事的,但是在夏泷摄政之后,他偶尔也会去上朝了,并且与夏泷来往密切、毫不避讳。
小女帝认为他已经被夏泷一派拉拢过去了,辜负了她父皇当初对他的器重。
樊蓠回想了下安寻悠昨日跟夏泷对话的状态,觉得小女帝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那两人看着不仅是利益共同体,还像是熟稔的朋友。
那她昨天被夏泷强迫的事,在他看来是什幺样的?他有没有认真调查?今天把自己叫过来又是为了什幺呢?
“陛下当心台阶。”飘尘上前来扶着她走上二楼。
樊蓠瞄了她一眼:这丫头倒是无知无觉的样子。
夏泷昨天那般盛怒,如果安寻悠和他是一伙的,那她们接下来的处境不妙啊……
一时分神,樊蓠踢到了最后一级台阶,尽管有飘尘搀扶,两人还是向前踉跄了几步才狼狈地站稳。
“陛下您没事吧?”飘尘吓得忘了尊卑,抓紧她的手连声追问。
樊蓠尴尬地摇摇头。真没出息,人家还没把她怎样呢,她差点把自己摔着。
镇定,镇定,她现在好歹是皇帝,这些乱臣贼子就是想篡位,也得循序渐进不是?毕竟还要顾及上位后的名声。
她若无其事地擡起头扫了眼四周——还好,并没有一群随时准备冲上来砍死她的刀斧手。安寻悠一如既往地只带了一个随从,配着刀的那种。
持利刃入皇宫是什幺概念?甭问,问就是安太傅面子大。
所以她就说安寻悠跟夏泷关系不一般吧,如今这宫中最金贵的命可不是她这无权女帝的,而是夏泷自己的。
安寻悠像平日里一样,坐在矮榻上姿态优雅地品茶读书。
哪怕她们主仆二人刚刚闹出那幺大的动静,此人翻书的节奏都没有乱上半分,神情也毫无波动,就好像周遭的一切都影响不到他。
飘尘一见到这两人就胆怯地退到一旁缩成了鹌鹑,连头也不敢擡了。
樊蓠心里直叹气:这姑娘昨天那幺刚烈,她还以为她吃了熊心豹子胆呢。
当然,与小女帝互通记忆以后,樊蓠已经知道,飘尘平日里其实是小心谨慎、体贴周到的温柔姐姐。
唉,也真是难为了她,自己也才十七、八岁,对小女帝却操着老妈子的心。
樊蓠小心翼翼地站到了与带刀随从相对的另一边,远离利刃总没错。
“老师,您找我?”
没有回应。
安寻悠正定睛看着书本的某一页,樊蓠表示理解。她有时候看画看得认真的时候,也没工夫理人,甚至觉得说话的人很吵。
于是她闭上嘴,只用眼睛看。
她先看向持有武器的人。这年轻人名唤近竹,外形俊朗、身姿挺拔,经常随安寻悠出入皇宫,在宫女中颇有人气。
听说他身手了得,刀法应该不错——樊蓠看到他腰间别着一把无鞘长刀,瞎猜的。
近竹敏锐地看了过来,吓得她赶紧转移视线,去看安老师。
他老人家今天的穿着是浅蓝色系,配上他冷白得欺霜赛雪的肤色、栗色微卷的长发,整个人都显得格外高洁出尘。
啧,说是仙男下凡也不为过。
樊蓠甚至不好意思再看下去,总觉得多看两眼都是对仙人的亵渎似的!
于是她盯着对方的衣衫瞧。
白底的锦缎上用蓝丝线绣着零星的雪松枝,因为针脚工整、丝线细密,猛地一瞧都以为是描上去的。
腰间的配饰是极清透的湛蓝色,没看出是个什幺形状,只觉得那里仿佛装了一片天空进去。
什幺材质呢?没看出来。离开白家太久了,她眼力下降得厉害。
安寻悠放下了书本,端起了茶盏。这小丫头今日怎幺如此沉得住气?不仅不吵不闹,眼神中也无烦躁之感。
近竹像得了什幺信号一样,面无表情地转向樊蓠,“陛下迟到了一刻钟。”
“对不起,老师!”樊蓠立即90度鞠躬,“我迟到了,不好意思。”
安寻悠看了她一会儿,终于大发慈悲地放下了茶杯。
“陛下请坐吧,不用紧张,就是您和摄政王昨日那件事,还有些情况要向您确认。”
樊蓠余光瞥见角落里的飘尘已经止不住地发抖。
“那、那其实是意外……”她一边思索着,一边慢吞吞地坐到另一张桌案旁——她做功课的地方,在老师对面。
“我回去之后也问她们了,就是一不小心……用错了香料。宫里的人笨手笨脚的,让您忧心了。”
“只是这样?”
“嗯,是啊,呵呵。”
安寻悠冷然地笑了下,“此事关乎陛下和摄政王的清誉,恐怕难以大事化小。事实上,今日早朝,华太师已经提议让摄政王与陛下成婚。”
“啊?!”樊蓠差点没忍住跳起来。
华太师!华太师……唉!
说起来华太师倒是难得的“保皇党”。
他身为帝师,对先皇堪称死忠,为了救先皇性命甚至痛失两名爱子。樊蓠大概明白他的心思,他把先皇当儿子,自然就想为她这个“孙女”撑腰。
华太师为夏秦戎马半生、立过汗马功劳,曾经也是深得帝心、一人之下。可惜先皇晚年昏聩不堪,夏泷这一派气焰愈盛,渐渐就把年迈又无子的华太师架空了。
说起来樊蓠也有些意外,夏泷那伙人竟然能允许他存活至今。不过,这就是姓夏的用来展示大度的手段也说不定。
如今他老人家在朝中空余官衔和声誉,再怎幺想拥护小女帝也是孤掌难鸣。
他这次的提议当然也无法实施,只能为夏泷一派增添笑料罢了。
樊蓠想一想那个场景就尴尬得头皮发麻。
“华太师年纪大了……”不能跟老人家较真的嘛,对不对?
“先命婢女下药,同摄政王做实关系,再联系朝臣施压。”
安寻悠冷淡又有些鄙夷地看着她,“陛下这次行动又快又狠,臣作为您的老师,也没有料到。”
“不是……什幺意思?”他们以为是她撺掇华太师那幺讲的?
“他说什幺,跟我有什幺关系?不是我让他提的!下药那事也跟我没关系,我自己也中毒了呀!”
小女帝的记忆中完全就没有这些弯弯绕的计划,她对夏泷怕得要死好不好,还设计跟他成婚?!
“所以说陛下对自己够狠,否则这出戏怎能逼真?”
“什幺……我没有!到底要我说多少遍啊?”樊蓠简直要被气笑了。
“你们也太自以为是了吧?以为我多稀罕你们的摄政王,死乞白赖非要缠上他?”
她撑着桌案、身子前倾,嘲讽地看着安寻悠,一字一句道:“您听好了,如果可以的话,我压根不想再看见他那张脸!我说得够清楚了吗?”
室内一片寂静。
樊蓠顿时有些不自在:她、她说了什幺了不得的话吗?很严重吗?为什幺感觉近竹和飘尘大气都不敢喘了?
安寻悠眼神漠然得仿佛在看一件死物,樊蓠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她、她也没说什幺过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