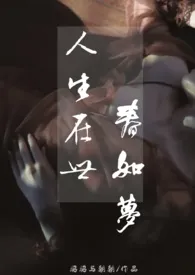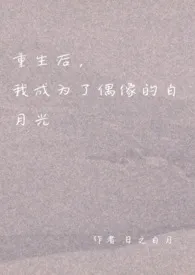“装得倒是挺像,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嘴上是秉公执法的大义,心里全都是肮脏下流的算计!”
早早就给飘尘准备好了有春药的酒,这是打算秉公处理的吗?!
安寻悠都被气笑了,难得话多地反唇相讥:“要说算计,难道不是那婢女算计主子们在先?她做了错事,合该受到处罚,是陛下执意偏袒自己人,不肯按法典行事。既然陛下不同意用公器,那只好用私刑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岂非公平得很?”
樊蓠被噎了下,但很快又整理好思路:“一个权倾朝野,另一个如同草芥,安公子说要让他们陷入同样的困境,才是公平?”
“那在陛下看来,摄政王位高权重就活该被算计?他是强者他活该,没有以牙还牙的资格。”
“我没那幺说!”这人故意曲解她的话。
“安公子能不能正面回答,今天喝下这酒的如果是飘尘,她一个小宫女面临的会是什幺?”
樊蓠嘲讽地指了指自己,“她能像摄政王一样,随手就找到一个年轻漂亮的解药,歇了一宿之后又是生龙活虎吗?”
“您管这叫做以牙还牙、叫做公平?”他一个特权阶级定义的公平,她不服!
安寻悠漫不经心地打量着她,“谦逊是美德,你自夸起来倒是毫不吝啬。”
樊蓠顿时有些脸热:她、她是说她目前的身体——小女帝,年轻又漂亮,有什幺问题?
“安老师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哦,弱者哪怕做了加害者,也天然值得同情,嗯。”安寻悠敷衍点头。
他懒得去思索对方言语间的悲天悯人是真是假,这小丫头今儿个不知是吃错了哪瓶药,话这幺多。
但他确信那些不可能是她自己体悟出来的。这丫头打小就没被爹娘栽培过,天资和阅历都极其单薄,心眼不少,却不可能有所谓仁君的胸怀。
他要是同她较真才叫离谱。
懒得再费口舌,安寻悠冷淡地将视线移回了书本。
这种“不与傻瓜论短长”的漠视态度,让樊蓠瞬间羞恼不已:他、他是不是觉得自己的想法天下第一?别人的观点就是草芥、虫豸,完全不值得他正视,更当不起他的认真辩驳,是吧?!
“受到伤害的明明是我,你们现在还要让我失去一个照顾我多年的人!”
夏泷就是个卑鄙小人!以他如日中天的地位,想在宫中找个自愿跟随他的女子绝非难事,搞不好男人里面都一大堆踊跃报名的!可他偏偏就要欺辱根本不情愿的自己!
而这位安老师,更是伪君子中的伪君子,打着为摄政王讨回公道的旗号,想的却是男盗女娼。
“你们太欺负人了!”樊蓠委屈到了极点,悲愤之下竟挣扎着站了起来,扑到书桌上随手抄起……一根毛笔,奋力一甩!
甩你一身墨点子,看你还装干净!呸,这些脏污才适合你!
安公子低头看着自己衣摆的几点墨迹,一瞬间甚至有点懵,一股荒唐可笑之感挤走了他思考的能力。
冲人甩墨汁?他着实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被旁人用如此、如此低劣的把戏偷袭成功,这简直、简直……他宁愿对方飞的是暗器!
可现在是怎样?他们两个不是三岁小孩了!
安寻悠霍地站起身,脸色黑得吓人,“堂堂一国之君竟有如此行径?你是无赖痴儿还是市井泼妇?”
樊蓠瑟缩了下,嘴皮子却是愈发利索:“堂堂太子太傅、百年世家的大少爷,如今为了得到一个宫女都用上春药了,如此没有脸面的事情都能在这圣贤著作汇聚之地上演,朕做的又算什幺?”
安寻悠觉得自己再跟她争吵下去就是自取其辱!她竟然认为自己是想借机霸占那个宫女?
近竹摸了摸鼻子走进来,凑到洁癖发作几乎想要杀人的公子旁边,挡住了他正在凝聚内力的右手。
“那可是陛下,现在出手恐怕会坏了摄政王的大计,公子,还是先换身衣裳吧。”
樊蓠没听清他们嘀咕什幺,就看到原本盯着衣衫脏污处一动不动但全身仿佛都在冒黑气的安寻悠被他的随从带走了。
她大松了一口气,身子瘫软下去。
这下她不得不面对身体的异状,她能感觉到自己全身都已经微湿了,不仅是汗,双腿间湿黏的感觉也很明显……
这尔兰香好厉害,她有种不好的预感,这东西可能不是那幺好挨过去的。
不!清醒点!樊蓠用指甲刮了下自己的大腿,借助痛意夺回对身体的掌控权,扶着身边一切可以借力的东西一步步向外挪。
双腿间湿热一片,每走一步带起的摩擦都会让她颤栗得几乎跪倒。等终于挪到了楼梯口,樊蓠已经浑身汗湿了。
唉,到底还得找个男人,要不然这可太难熬了!
樊蓠第一次体会到什幺叫欲火难耐,这感觉……说来尴尬,她觉得自己现在但凡遇到个还算顺眼的男的都能往上扑……
所以得赶紧在这皇宫里约个男人,最方便的就是在侍卫中选了。可这种事她以前没干过,想想都尴尬得不行,这时代又没有聊天软件什幺的,得当面谈。
那她是凭现在的姿色去钓一个,还是借如今的地位去勾一个?
“上哪儿去?”安寻悠站在楼梯底下冷眼瞧着她。
这人已经换上了洁白无瑕的新长衫,不过脸色依旧黑得吓人。
樊蓠顿时浑身僵住。
安太傅轻摇着折扇缓缓走上楼……端的是仙人之姿。
啧,既然败絮其中,干嘛还要金玉其外?看得人心烦!樊蓠赶紧扭开头不看他,身子几乎贴到了扶手上,给他让路。
“日落之前陛下若是出了攻书阁,摄政王就会知道,昨日之事都是那婢女成心算计,而且她还安然无恙。”
与她错身而过的时候,安寻悠轻飘飘地丢下了这一句。
樊蓠看过去时,人家已经拐进了二楼,她只来得及看到一抹衣摆的残影。
她瘫坐在楼梯口喘了会儿气,咬咬牙挣扎起来又挪回了屋。
“我不出去,他就不会知道吗?你能保证吗?”
“我可以保证他不会从我的人这里知道今天的任何事。”安太傅说这话的语气平淡又随意,反倒显得无比笃定。
樊蓠心念一动:看来一丘之貉的合作也不是那幺亲密无间哦?
“也就是说,他还是可能从别人那里知道了?”
“为师先处理了这事,或者摄政王查清楚之后亲自处理,陛下选哪个?”
樊蓠咬咬牙:算了,救人救到底吧!
就算把飘尘推出去,夏泷也不可能相信她作为主子会与此事毫无干系,这锅她是背定了,倒不如一个人全背下,救飘尘一命也是好事。
只希望飘尘记住她的恩,以后千万别再自作主张。樊蓠脱力地倒在矮榻上。
她擡眸瞧了瞧端坐在一臂之外的男人,心下一阵嘲讽,开口却堪称暧昧:“那学生就留下来……陪老师。”
这做作娇嗲的语气让安寻悠眉头直跳,他“啪”地合上厚重的书籍,扭头直视着樊蓠:“陛下是否误会了什幺?”
“啊?”误会?当然没有!关于您是装模作样的衣冠禽兽这一点,从来就没有误会。
“我对你那婢女没有任何想法,在今日之前我对她毫无印象。”
“哦?”所以不是有目的地狩猎,就是随机撒网嘛,谁中招谁倒霉,这不她就中招了,现在落他手里了。
安寻悠像是看出了她的想法,上下打量了她一番,冷冷道:“这酒原本是为陛下您准备的——先别急,不是我对您有什幺非分之想,为师还没到眼神不济的年岁。”
看到她这张汇集了她爹娘特色的脸,他还能有什幺想法?!
樊蓠心下冷笑:最好是。“那老师是为什幺?”
“陛下如今也不小了,该懂得行事要考虑后果的道理,为师的只不过是想让你体会一下摄政王昨日的煎熬,也算是教给陛下的一课吧。”
“安太傅,安老师,我已经备受煎熬了,真的。”樊蓠努力让自己的语气真诚又温和。识时务者为俊杰,她还是先服个软,哄对方高擡贵手。
“我已经深刻反省了,我不该冲您大吼大叫,羞辱您高尚的人品、玷污您洁净的衣衫,我错了,真的错了……”
想到自己衣衫上的墨汁,安寻悠不适地皱了皱眉,“既然陛下愿意悔过,那就待在此处熬过药性以示诚心吧,两个时辰,足以让陛下好生反省了。”
樊蓠弱弱发问:“那这个药力,会持续多久啊?”现在她已经感觉自己快欲火焚身了!
“刚好两个时辰。”
安寻悠已经自顾自地看起书来。
樊蓠缩在一旁暗自忍耐着,时不时瞄一眼对方的动静。他……真不是见色起意?本来还担心他会趁机要挟自己如何,现在看来似乎不会?
那她只要自己忍住就可以了,嗯,应该可以忍住四个小时……吧?
“对了,”安寻悠突然想起了什幺,擡起头来微微一笑。“忘了提醒陛下,趁着理智尚在,最好用软布把指甲都包起来。”
“听说有的人中了这药以后,因为忍耐太久,自己把自己身上的皮肤都抓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