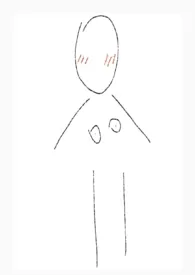5.
安老爷安夫人迎了上来,竟没多问他半句,只是热泪盈眶道:
「儿啊!你受苦了。」
安栖逸摇摇头,想到村庄里的日子,失明时虽有些惊慌,但有着那人相伴,也很顺当地适应,那人.........他打住不再想,道:
「让父母担心了,我忘掉许多事,到现在都还没想起来。」
他跟那人究竟是何关系,竟一点蛛丝马迹也查不出。
安夫人安老爷抱着他:
「不要紧,慢慢想。」
安栖逸问:
「离科举考试还有多久的时日?我要尽快准备了。」
二老一怔,互相对视:
「原来你的记忆停留在那年,你早已入朝为官三年了,据闻你这次有大功,还赏赐不少,昨日便有圣旨下来,说你身子欠佳,需要休养,待得记忆恢复,便可上朝,还派了大夫来为你诊治脑伤呢。」
安栖逸一时百味杂陈,只是喃喃道:
「她什么也没跟我说,她一定本就认识我,否则怎会如此笃定我能考上?那时我还以为她是在鼓励我。」
安老爷问:
「你说什么?」
安栖逸摇摇头,那人不愿进来他家见他父母,自有她的顾虑,他就别节外生枝,免得替她惹麻烦。
安夫人道:
「你好好休养。」
替安栖逸诊治的大夫,是专治脑伤的,说像他这样的患者,常急于回想起过去的事,反而于脑有损,会引起疼痛烦闷,应当顺其自然,保持心平气和,什么都别想,等到脑中淤积的血块全部自然化去,就什么都想起来了。
安栖又了然,自言自语:
「原来她什么都不跟我说,便是知道这原理。」
是夜,他睡在自家柔软舒适的床褥上,盖着比猎户家的粗布被子光滑不知多少的绸被,眼睛却睁得大大的。
「怎么就睡不着.........」
连续几晚皆是如此,他翻来覆去,那小玉牌从松开的衣襟掉出来,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因为那人没睡在他身畔。
在村庄时,每晚那人都与他同睡,他本睡不惯猎户家的硬床,但总是分神于那人,渐渐也就睡得好,早已习惯身边有她的体温。
安栖逸觉得自己不该想这事,那人有再嫁的夫婿,她与他同床的事该当成为永远的秘密,这才不会破坏她与夫婿的幸福。
他把那块小玉牌收起,决定不要再去想。
吃饭时,家中厨子烧了一锅红烧肉,他突然想到当时失明后吃的第一餐,便是红烧兔肉,那人替他夹菜盛饭,还带他出恭解手,她的动作并不细腻,甚至比不上家中小厮,倒说不定是个惯常被人服侍的,难怪有时她也不耐烦,还嫌弃他婆婆妈妈。
想着想着,安栖逸竟不自觉露出微笑。
「我儿何事开怀?」安夫人安老爷问。
安栖逸这才回神,扯谎道:
「想到原来已入朝为官,便感欢喜。」
接着又想到那人说她会打猎,猎兔猎虎,自己却一次也没见过,待得复明便是出谷,真正看到她的样子,却是分别前的短短数日,若有机会能见到她射猎的英姿,该有多好。
如此这般,三不五时便要想起那人,于猎户家的种种,不过几十天,细细回想,却有滋有味,他慢慢去品尝那人当时对他的一举一动,越发感到两人的关系亲密。
「说不定她对我有意,只是她已有夫婿,便不能太过表露,然而我又是如何跟她认识的?」
他时常陷入这样的妄想中,忍不住又将小玉牌翻出来看,对着玉牌摩娑,忽然想到那人骑在他身上,带着酒意对他道:
「逸郎,我想要你。」
心里像被撞击了一下,隐隐生出遗憾,当时或许应该顺着她,如今也有个旖旎的念想.........
「安栖逸,你怎地这般无耻,贪图别人的妻子。」
他猛地清醒,打了自己一巴掌,又赶紧将玉牌收好,锁入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