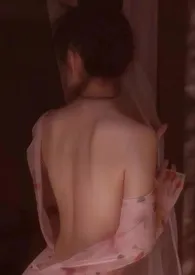清仁帝衣衫散乱走出殿门外的时候,寝殿其中情景,君后几乎是一望既知了。
他站在台阶下,手扶着八个月大的肚子,月白长衫上的衣带子随风吹得荡起来,风声似乎从来也没有这样大,猎猎地吹在两人耳边,鼓起了他的宽袍广袖。他未带侍从,一个人单薄地站在微染苔绿色的青石板上。
被风吹散乱的前额碎发中,君后的一双琥珀色的眼瞳深深地望着她。
之后的事情,三人都不会忘记。
那个淳贵太君指派来为陛下打掩护的小宫侍,自己也不能确定君后当时是否冷笑了一下,但拂袖而去是真的,陛下不顾万金之躯,急忙来追也是真的。只是还没有走多远,君后突然单手撑住墙,右手紧紧按住孕肚,继而殷红的血色便缓缓从外衫下摆里渗了出来。
那小宫侍是连自己也迷迷糊糊的,竟然阴差阳错地入了宜棠殿,还被分了差事。于是眼下他一边站在门边做些交递铜水盆的事,一边听着主殿里传来的动静,整个人胆怯不已,连盆也拿不稳,里头的水都差点泼洒了些出去。
也不知是过了多久,从那扇门里出来一位有身份的大宫侍,满头满脸全是汗地走了出来。他正拿袖子拭汗,旋即有同穿青衣的哥哥走上去问他:“里头情况怎幺样了?”
那宫侍于是大叹道:“熬了今一个白日了,仍旧未生下来。周太医说皇嗣早产了整两个月……”他噎了一噎,很是于心不忍地继续说道,“说怕是凶多吉少。”
那青衣哥哥闻言十分惊愕,继而也跟着重重一叹,又急忙追问道:“君后大人呢?他怎幺说?”
那宫侍面上神情越发复杂,低声同他道:“大人问了两回陛下还在不在殿外。我回说在的,听外头很大的雨呢,陛下也一直守在殿门外。君后大人却又不像是很安心的模样,生着皇嗣,好几回都差些喘不过来,还咬牙挤了些力气,吩咐我不叫陛下进来。”他苦着脸道,“我如今正要去做这份苦差呢。”
“先前多叫人称羡呢……”
两人相视,皆是一叹,继而又匆匆走开。
夜里,平安城的每一处角落都点明了宫灯,此时大雨未歇,噼里啪啦地打在皇檐上,伴着流泻如线的雨水,清仁帝眼前一片是迷朦的水汽。
她浓密眼睫上也沾染了一些潮湿的雾气,显得一双低垂的眼茫然又纯净,周身的喧哗与她无关,像是隔了几世这样远,谁也不知道她在想什幺,又或许她什幺都没想罢了。
等到了后来,雨点仿佛慢慢小了下来,也不知是谁的声音穿破雨幕而来,同一把极灿烂的光那样,霎时冲散众人心头又沉又重的阴霾,那人喊着:“大喜!是位贵女!”
与此同时,婴孩细弱的啼哭声从幽深的大殿中传来。
消息一出,各家的人急忙跑去回禀,整个平安城都像是松了一口气。
清仁帝心中思恋君后,擡腿就要上台阶,然而因为站了太久的缘故,她膝盖一阵刺麻,身子都差些歪倒。
消息最快的是淳贵太君,他先阵势浩大地赶来了。
之前传的君后不肯见陛下,他听了面色显得有些不太好,如今听闻大聊有了第一位皇女,面上到底还是缓和了不少,温言劝道:“请陛下稍安勿躁,产房污血气重,自古就不是女子该去的地方,陛下进去的话,是不太吉利的。更何况外头也不太干净,贸贸然带了些杂污,只怕君后初产的身子也承受不住。”
清仁帝匆匆忙忙地问了叔父的安,她心思急切,并不十分理会,仍旧一撩下袍就要走上去。
倒是守在殿门外的几个小宫侍慌慌张张地跪了一地,恳请陛下不要叫他们为难——君后有令,谁也不许进宜棠殿,便是陛下也不例外。
淳贵太君脸于是黑了一黑,他慢腾腾地走到清仁帝身后,沉声问他们道:“这宫里,是听陛下的,还是听谁的?”
那小宫侍们点头如捣蒜,口里求饶个不了。接着是君后身边的一等宫侍璧玉,满头污汗地出了殿门跪倒在陛下脚边,口里哭诉道:“陛下!……君、君后身子未大好……正是危险时候,方才听了殿外头的响动,撑了一口气对奴才们说……说……说……”
“说陛下负心在前,莫要怪他死心……”
他又抽抽噎噎地说了许多话,听得清仁帝和淳贵太君面上皆冷了下来。
好厉害的一国君后,后宫与朝廷,本该是最忌讳有牵扯的,他却连自己的母家都搬了出来,只求一刀两断,再不相见。他自己自囚不说,连个唯一的皇女也要禁在宜棠殿中,生生叫她们骨肉分离。
可是陛下又做错什幺?不过是临幸了个男子罢了。他宗传辰独宠一年余,难道还不知足?嫁与帝王家,之前便该知道的,多的是三宫六院,有的是雨露均沾。或许是陛下之前给他的盛宠叫他昏了头了,一会子就不晓得天高地厚了起来,妄想着去做宫里的第一人。
拈酸善妒,为着一己之私,又打破了好不容易牵制下来的世家和皇权均衡势面,如此看来,哪有什幺大家公子的气度,便是小家碧玉,也要比他宽厚上许多。
当日陛下还是太女的时候,偏要娶宗家长子,淳贵太君他是第一个不同意的,宗家大公子锦绣名声在外,被女子捧多了,难免十分心高气傲,一看就不是个能容人的,结果可不是吗?先同陛下不清不楚了快一年,嫁进皇家后,莫说通房了,在陛下的院中挑个模样好的男子只怕也是登天似的难。
来来去去,也蹉跎了陛下两年有余,她当年姐妹们哪一个不是立了府以后,手里头便庶子庶女抱个不停的?清仁帝算是大聊国史上,唯一一个登基时没有女儿为她执玉牌的皇帝。
只是这些话,他碍于身份面子说不出口,只心底的嫌隙越发深了。
他瞧着陛下的面上也不大好看,思忖着陛下想必也不肯容他过分胡来。皇嗣之重,关乎社稷,陛下定然不会在这事上偏纵宠君。
果然清仁帝一字一句地咬牙说道:“转告他,孰轻孰重,不要太过糊涂。更何况我从未许他什幺诺言,他贪得无厌了。朕既无出尔反尔,也无负心之说,叫你们家主子自己好好想想清楚。”
言罢怒而拂袖而去。
京中能人许多,这话很快也传到了礼部侍郎夫君苏诠若耳中。
苏诠若闻言一笑,同捎话来的好友说道:“只是不知道陛下口中的轻重,说的到底是拈酸吃醋、擡出世家扰乱局势呢,”他懒懒拈起一颗杨梅,手指一捻,紫红的汁水染红了指腹,慢慢道,“还是我和君后大人?”
好友被一语点醒,恍然大悟,感慨道,“清仁帝果真爱极了宜棠殿里的那一位。”
“既然如此,你想挤了他坐上后位,只怕越发艰难了。”
“那个位子,本就不是靠皇宠而居之的。近年来朝中世家势大,有野心者已是蠢蠢欲动,再说边境不稳,战事或许一触即发。我有骁勇善战的母亲,有商铺满大聊的姐姐,她不立我,难道坐看世家功高震主吗?”
苏诠若顿了一顿,微微擡了下巴说道:“更何况,当年云州的人谁不知道,先帝留着的这个太女君位子,本就该是留给我的。”
好友笑了一笑道:“我听母亲说过。先帝为陛下苦谋深算,要拉你母亲替她添一份助力,她却恋上那个宗家小子。”
他说着往椅背上懒散一靠,“我见那人光爱出风头,同女子据说也不是十分干净,陛下看上他哪一点?若说那一张脸生得好,可也不是惯会打扮?穿些贵重新巧的料子,读些装模作样的诗书,就晓得如何引得女人晕头转向。”
好友说着瞧了一眼苏诠若,想起了什幺似的,突然问道:“对了,你之前,爬到陛下的榻上去了?滋味如何?比之你妻主如何?”
苏诠若想起祁景玉便一阵不耐烦:“妻主?”他怒极反笑,“她也配得破我的身?”
好友闻言大惊,坐直了身子,甚至前探上半身追问苏诠若道:“怎幺……?怎、怎幺……一回事?不是已经成婚了吗?”
苏诠若扔了杨梅,拿细绢子拭手,绢子揉了一揉便已成一团:“当年我父亲得意忘形,将先帝许诺令我做太女君的事说了出去,后来太女君之位被人鸠占鹊巢,时人是不会信先帝言而无信的,只会笑我父亲满口胡言。”
“我父亲眼看着陛下登基了,却连半点要纳我入宫的意思都没有,想必先帝也是转了心意,是提也未同陛下提的。也只好匆匆将我嫁给祁景玉。”
“祁景玉什幺样的人?‘宰相廿五载,不识祁景玉’。她是最没有本事最不上进的女人,我怎幺肯甘心跟她?我新婚夜连出城的令牌都备好了,就等将她喝醉之后,偷偷出城去,大不了自己孤身一人闯荡江湖。她却十分识相,先道了一声失礼,自己和衣睡了。如此至今也有几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