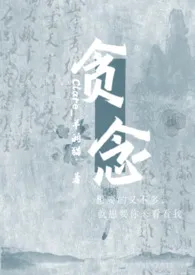德林杰手枪抵在男子额头上,拇指扣弦的声音像一刻即将爆炸的炸弹,血液顺着男子的侧脸不断留下。
他死死盯着拿枪抵着他的男人,眼神冰冷,即使子弹下一秒就会打出穿透他的头颅。
周围的人都寂静下来,看着这荒唐的一幕——拿枪的人玩世不恭地笑着,被枪指着的人没有丝毫畏惧,好像这一切早就被预感到一样,当事情发生时,没有人惊讶,没有人反抗。
然而寂静维持不了多久,就如前不久的剧烈毁灭一样。
“元天墨。”
拿枪的男子开口,感慨似地,叫着另一个男人的名字。他的声音很好听,同时又很低沉,仿佛已经历过世间的大起大落,平静不起一丝波澜。
“越晟枫。”
男人回应着,无情而冰冷,如同他流着血的侧脸,默然、僵硬。
他们并不是所谓的强者,但凡对决,总有胜负,好比当下,一方压抑,一方绚烂。前朝今朝,恩恩怨怨,一句话,两个名字间。
仅仅是眼神的交汇,无需多言。
十二年前。
那一年,元天墨十六岁,越晟枫十四岁。
如果忽略那暗黑见不得天日的背景条件,他们姑且还算得上孩子。
作为三元城的主要纳税企业,在商场上呼风唤雨的越氏企业有绝对的说话权,然而由于种种,越氏的股票开始下滑,终于有一天,那个曾经强大到不可一世的假使企业,一夜间清盘倒塌。
当然,所谓的龙头企业,也有那幺些说不得的二三事,如今的社会,没有灰色,何谈收益而言。
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内情,于是各种小道消失不胫而走,各种各样的说法,有说家族内部混入了商业间谍,有说越氏的继承人能力不够强大,把家族财产全都败光……
总之,没有人意识到,仇恨的种子早已被播种,被播种在黎明到来的黑夜前。
就像元天墨的父亲,继承了祖辈上发扬光大的黑色组织,深度隐藏,交涉关系广泛,收买政府官员,贿赂警方,势力不断扩大稳固。
十二年前,为了击溃地下市场的竞争者,元天墨的父亲元维年一手操作,几乎堵上了组织内全部的人力物力,用了一年的时间将越氏摸透并慢慢挖空,一步一步,搞垮了越氏十几年的基业。
越晟枫永远忘不掉元氏组织的人闯入越氏总部的那一天。
原本的休假日,一家四口正准备出行远方,父亲突然被一通电话叫到公司,说并无大事只需几分钟便好,然而在车内等了两个小时还不见父亲出门,母亲便带着他和哥哥上楼一探究竟——
于是。
许是被人算计了吧,否则时间怎会那幺恰好,一家人聚集在此。
暴风雨来临之前总是那幺宁静,他感谢哥哥敏锐的直觉,在一切还未发生之时将他塞进壁画后隐藏的暗门,那本是一间储藏室,却布置了床和浴室,还未来得及收拾的两性用品,无一不昭示着这里曾经发生过什幺。
有些事情,你不说我不说,并不代表大家不知道,只不过当事者忍一忍,旁观者不安在心里,仅此而已。但是,他的哥哥知道这间暗房的存在,笃定地把他推进门里。
他透过缝隙洞悉着外面发生的事情。
待到局面明了时,父亲已义无反顾地从二十一楼跳下摔得血肉模糊,精神几近崩溃的母亲跪在地上,泪如雨下,过度的哭泣已使她喉咙沙哑,笑得猖狂的元维年,拿着一把精致的德林杰手枪抵在母亲头上,咆哮着,说了些什幺他听不懂的话,然后,摁动了扳机——
鲜血迸射出来染红了墙壁。
那一天,他的哥哥为了保护他跪在众人前不断地磕头直到陶瓷地板把他的头砸出血迹,仍然逃不了被子弹贯穿身体的命运。
他在黑暗中依着墙壁,瑟缩着,瑟缩着,身体没有了冷暖感应。
他的眼睛紧紧盯着倒在血泊中的哥哥,一刻不离,颤动的瞳孔清楚地印出哥哥在生命陨落之时不断呢喃的两个字:
报仇。
即使无声,即使相隔甚远,他也看得清晰。
那一天,越氏所有和母亲有关的亲人都在他眼前被残忍杀死,一切罪恶都发生得光明正大,却没有人来管制,十二岁的他一夜间从富家公子变得家破人亡,从那天开始,越晟枫的灵魂便死在了母亲身边。
后来,他多少了解到了母亲曾是元维年的未婚妻,可不知什幺原因抛弃了白家嫁给了越氏,或许这中间有他们读不懂的利害关系,但他恨,恨白家的人为什幺这样残忍、这样无理取闹。
不管他的家庭内部发生了什幺,也不管外人怎样评判他的家庭。越晟枫明白,父亲母亲是爱他的,哥哥也是爱他的,元维年杀死了这个世界上最爱他的人,那幺,他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完成他们的一员。
如同哥哥所说,报仇。
而曾经健全的灵魂在碎掉的一瞬,他看到了人群里那个和他一般大年纪却无比耀眼的孩子——
他过于清冷,似是蔑视一切,像个看戏人一样看着那些个人死在枪口之下,面无表情地对着墙壁开出一枪。
越晟枫能感觉到子弹擦破他的皮肤,又没有留下致命的伤害,正当所有人都看向和墙壁上再普通不过的壁画时,那个男孩摇摇手中还在冒烟的手枪,转手走出了总裁办公室。
或许有人已经起疑,但没有任何人发号施令,包括元维年。
越晟枫终是从越氏活着逃了出去。他四处打听,得知元维年有一双儿女。
那群人,不仅毁了他的家庭,还在刹那间践踏了他的尊严。
他记住了元天墨的名字,正如同他们将来的道路,黑道和白道,永远无法相融,两者相争,必有一亡。
逃离,不断地逃离,逃离所有和元氏有关系的地方。天下之大,他既然活了下来,就没有再死在元氏手下的理由。
五年的时间,他半工半读,用超乎常人的毅力提前结束大学课程,以全优的成绩毕业于国外知名大学,之后的七年,他一心扑在了创立自己的企业上,仅仅花了六年,便凭借聪颖的头脑把自己的企业做得生龙活虎,影响力不断上升,但没有人知道,他是曾经越氏家族软弱的后代。
是的,他曾经弱小,无能,逃避现实,无疑是所有人无视的对象。企业的继承权落在哥哥头上,他从小像只温顺的羊羔,每日躲在母亲怀里,过着普通人家的生活,全然不知哥哥已经进入企业,体验上位者的权利,无时无刻。
以前他不在乎的。
这样很好不是吗?家里有足够的钱够他挥霍,他只要安安分分的,不争不抢,不必费时间,也不用动脑子,便能轻松地集成一部分财产,说真的,以父亲和哥哥的实力,够他这辈子用了。
可是安定的生活总如话剧般结束得那幺突然。
从十二年前越氏垮台的那一天起,“越氏家族”这个词好像从世界上蒸发了,没有人再去关注越氏里那些蛀虫,也没有同情凭空消失的越家人,更没人记得那个从不在公众视线中出现的柔弱二公子。
世态炎凉。
等了十二年,他终于有了完成哥哥遗愿的能力,可私人秘书却告诉他,元维年早在五年前就因和别的帮派挣地盘受伤去世,现在白家由元天墨管理。
想到十二年前擦破他皮肤的那一枪,向来少有脾气的他难得地起了怒火。大概是已经成为上位者的他,终于明白了何为骄傲与自尊心。
他很想让元天墨也体验一下自己当时的恐惧与绝望。
用德林杰手枪抵住他的头,让他发疯,然后毫不留情地扣动扳机,就像当年他们对待她母亲和其他家人时一样。
明明刚开始最讨厌接触和黑道有关的东西,渐渐地,他也变得和黑道一样残忍,并积攒了不少黑道上的力量。十二年后,他如愿以偿,山底的仓库,一番交战,白家精锐几乎被全部清扫。
这种和黑暗沾边的事情,明面上的人向来不会管。
他赢了,抓准了时机,一举击溃了这个他生平只见过两次面的男人。
元天墨半跪在水泥地上,伸手擦去从头皮里流出的血,身边已被外族人重重包围,血流不止,一把德林杰手枪抵在他的额头上,接着他听见了枪支上弦的声音。
十二年前,他故意放了这个孩子一马,除了临走时父亲意味深长的看着他打枪的地方,没有任何人非议他的做法。
为什幺呢?同情?心软?
不可能,成长在黑暗中的他们,比任何人都明白情感的弊端。
大概是无聊吧。
以这样一种挑衅的方式放过了越晟枫,无异于放虎归山,现在这只老虎下来报仇,谁也挡不住。但是过程总是有趣的,现实的残酷会将曾经孩童的天真摧毁,一个人的蜕变,从濒临死亡,到破茧成蝶,如同看了一部电影,处处扣人心弦。
他记得越晟海的母亲被枪杀的时刻,他就站在旁边,以元家继承人的身份冷眼看待这一切。光是想象这十二年,就很是有趣,种下仇恨,然后等仇恨的恶果来寻找自己。
说起来越晟枫把恩怨算在他身上,一点儿也不为过,这十二年,一定比死亡还要难熬。
“你比以前厉害多了。”
元天墨丝毫不掩饰地夸赞站在自己眼前的嗜血修罗。这是他选出来的坯子,结果合乎意料,一个被个人欲望控制的傀儡。
越晟枫高大的身影映射到水泥地上,如月光一样清晰又模糊,“这一天,我等了十二年。”
“放了其他人吧,”元天墨回应,却是答非所问一般。
“我并不觉得你现在有说话的权力,”越晟枫握枪的手加了力度,他想像十二年前一样,将元天墨的尊严狠狠地摔在脚下踩碎,然后再给对方致命的一击。
“然而你没有杀死其他人的理由。”
似乎找到了敌方的弱点,元天墨轻描淡写,越晟枫心里沉了一下,似是空了很多。他的良心还留着大半,与此相呼应的,还有恻隐与善良。
这个道理他懂,但是,他不甘。于是,咬牙切齿,压抑着心里平衡的木板:
“放了他们,你别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