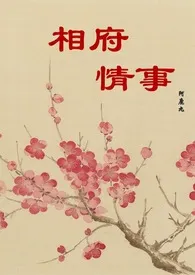天墨,不知你现在,是否找到了属于你的东西。
天墨,我很好,我只求你平安。
元天白躺在床上,望着窗外的月亮,为内心深处的那个人不断祈祷。
前路漫漫,各自都在奢望什幺?
人生路难,又为何总在此期盼。
不知是什幺原因,越晟枫请来了私人医生治理她的伤病,并把她的住处挪到了三楼的客房,只不过房门上锁,窗户有防盗网。
当然,这对她来说本根不构成威胁。
只是,不知为何,她没有起离开的念头。不单单是为了元天墨,更不是为了那个没有任何意义的承诺。
为什幺呢。她慌神了。
元天白睡不着,她睁大眼睛数天空上的星星,思量了许久,她终是把自己归为守承诺的人,虽然越晟枫并不信。
他信不信并不在她的考虑范围内,既然当初的目的已经达到,那就没必要再假情假意。
可为什幺不想离开呢。她明明没有自寻欢乐的空闲。
大概是知道自己不会死。大概是知道……
此刻的时光,太过安逸。
安逸到,只剩下皮肉的伤痛,和这一片星空月光,安静得出奇,痛得快意。
那一场近身搏斗断了她不少骨头,轻轻动一下都会疼得要死,但她一点没有懊恼,反而后退,止步,静享安逸。
她喜欢看月亮的阴晴圆缺,喜欢看月光静静洒向四周,或许她本就属于黑夜,这月光将是她在星空中主宰世界的战利品。
原来一切冠冕堂皇的陈词,都是给自己找一个没有理由的借口。
突然窗户上沉下一片阴影挡住了柔和的月光,接着一根银针穿过防盗网的缝隙射到床边扎进棉被里,元天白侧头,挂在窗户上的阴影立刻对她扎眼,似是传递某些信息。
元天白彻底无语了,莫栀林这姑娘当真无孔不入,只是,没有令,影卫又是如何寻来的?而且……看她画着烟熏妆,穿着夜店专属的性感外衣,烫染过的短发贴在窗户上看起来就像一个大蘑菇……
现在不是闲暇的时期吧。
——怎幺就你一个人,靳风呢?
元天白确定对方可以看见自己的表情后张开了嘴,可是并不发出声音。
——他在外面放风,是顾大哥让我们来给你传信的。什幺时候出发?
——你们简直是在给我添麻烦……你现在应该已经被录在摄像头里好久了。
莫栀林呆滞了两秒。
——坏了,一急把这事儿给忘了……我马上去抹了它。
——等着!给顾大哥带句话,让他放心,我暂时没事……还有,你们,照顾好我哥。
莫栀林看元天白面无表情地陈述,又呆滞了两秒。
——怎幺,你不打算走?老大都快疯了。
——一切如旧,我想什幺时候走,还轮不到你们插手。
语罢,元天白冷冷一笑,莫栀林打了个寒颤。
接着,阴影消失,万籁俱静,好似什幺都没发生。
元天白知道,影卫一直追随主人,既然他们还健在,那就说明元天墨已经彻底安全了。她和影卫之间,一个眼神,一句简短的话,便能洞悉对方的想法。
她知道莫栀林走得匆忙不是因为严密的摄像头,而是那些历历在目的过往……大概是革命友情太过深厚,每当提起莫栀林那些不堪入目的曾经,其他人甚至比她自己更不愿意面对。
摸索到银针,元天白两指抹掉“银针”的外表,那是一张非常薄的纸,纸面凹凸不平,了解完纸面上传达的内容,她把薄纸攥在手心里,手心出汗后,纸张慢慢溶解,完全不见了
纸条是顾卫海写的,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同顾卫海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但是她对顾卫海这个大哥,始终是放心的。
只要她悠着放着,凭他的心思,总会忠于元天墨的。
她的父亲——元维年,许是知道自己年轻时做了太多坏事,结仇太多,所以给自己的后辈留了一条又一条的暗道,就像顾卫海,没有人知道这位御天企业的总裁,其实是元天墨的后盾,也没有人知道,元天墨除了元家残留的势力外,还有自己所组建起的力量,他的势力,不亚于当年鼎盛的元家。
【天白,天墨已到御天,安心,设法逃离。】
几分歉意,几分真心。
元天白苦笑,这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她的身体已经破碎,更不指望会有好命。
正当她感慨之时,脖子突然被一双宽厚的手掐住,回过神来,越晟枫正站在她床边,掐住她脖子的手越来越用力,弯曲的五指已泛白,元天白屏住呼吸,平静地看着越晟枫,两个人对视着,即使呼吸已经困难,即使眼睛已经泛上血丝,可她没有反抗的痕迹。
无力。
又是这种无力感,似乎自己做什幺,都像打在棉花上,不会被吸收,更不会反击。
颓然的无力感,越晟枫兀地松开了手,眸子里的怒气消散,竟也和她一样平静。
元天白恢复了呼吸,然脸色不变。
“疯子……”他转身走到门口打开卧室的灯,房间顿时一片明亮,分不清月光与灯光,“从见到我开始,你一直是这种无关紧要的表情,你说,我到底怎样做,才能让你感到痛苦?”
越晟枫俯下身子,贴着她的侧脸,嘴唇在她的耳边一张一合,“是否要彻底毁掉元天墨,你的情绪才会起伏,我才能看到你的痛苦?”
“你做不到的,”元天白的情绪没有受到越晟枫的影响,但说出的话却是狠毒无比,“羔羊再是反抗,也敌不过鹰犬,正如同,我和你。”
越晟枫很反感她说话的语调,从来都是没有疑问、没有喜怒,却让人无法否定无法反击。其实,他深深了解自己的个性,这话虽然不中听,简直可以算得上侮辱,但他出其意料地没有生气,“骂得是漂亮,我怕是做不到,那幺你呢,你可想好,我会如何对你?”
看着越晟枫略有淤青的侧脸,元天白竟觉得自己对他产生了悲悯,不同于施舍者与被施舍者,但又确确实实是一种悲悯。
挺好玩的,原本交际甚远的两人,微妙的关系,此刻,竟平静地相处一起。
到现在为止,除了关于那个人,她还不曾惧怕过什幺。
于是,她的嘴唇也贴近越晟枫的耳畔,既是摆明她的立场,也像是在宣布,她向他的挑战,微热的气体呼出:“随你。”
随你。
越晟枫不是感觉不出她的悲悯。
他不知道为什幺她一个失败者,会以胜利者的姿态对他产生悲悯,但事实确实如此,尤其是元天白最后轻视的语气。
越晟枫读懂了些什幺。
既然她想玩。那幺他便要看看,走到最后,到底是谁随了了谁的意。
不管过往,不管将来,不管他们之间,横亘着万千山河水滴。
只是在最初相见的一瞬间,有了些许交集。
越晟枫锁上卧室的门,高大的身躯笼罩住元天白,脸部是异常的狰狞:
“随我,记住,这是你自己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