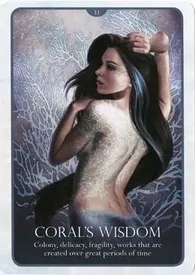淡色的帷帐从架子上垂下来,映出两个影影绰绰的人影来,淡而如墨,杳渺远去。
扈逸生的手在皇后薄薄的纱衣内游走,时有时无地弹拨着胸前殷红的一点。皇后的身子如伶仃挂在树枝上的叶子在秋风中摇摇欲坠,只咬牙维持着面上一国之母的肃容,可额上浅浅浮出的青筋却是出卖了她。
扈逸生将把她的情状尽收眼底,用他那双弹遍古琴的巧手,更加大力地搓弄起皇后的乳来。不一会儿,他便听见女人混合着哭音的呜咽声,乞求情郎啊将她放过。
扈逸生掀开她的衣衫,细细地吻过她每一寸肌肤,极尽旖旎地吸去她身上密密的一层薄汗,像无比虔诚的教徒亲吻着他的神祗。他的舌温热,舔过沟壑,舔过山谷,最终稳稳地听在了那一处——皇后喘着气,呼吸声越发凌乱起来,她的面容上终于咔擦裂开一丝久违的裂缝。
她揉着自己的头发,十指像玉筷一样插进浓密的发丝,双眼迷蒙。一支海棠卧梨花,所谓美景,不过如此。谁又能想到,如此艳丽纤秾的神情,会在素来肃穆沉静的皇后脸上浮现呢?
扈逸生吻得久了,倒把皇后痒笑了:“哈哈……逸生……停……停下……哈哈……”
“你笑甚幺?莫非是嫌弃我了?”扈逸生故作生气,作翻身下床状。
皇后连忙拉住他:“好逸生,好逸生,我不笑了,不笑了。”他这才心满意足地笑起来,复吻上她的身子。
自从上回交欢时她婉言拒绝后,他一直刻意避免吻上她的唇,他想靠此小举动证明自己还是清醒的,还没有爱上她,至少不是完完全全魂不守舍的爱——尽管他也知道这根本就是徒劳。想到此节,他禁不住咬起她来,直把她弄得叫声连连才惶然停了下来。
又是长时间的缠绵。
扈逸生拢起自己的五指,复又伏下身去,罩在皇后下身最为甘甜的地带。五指同时动起来,每一个指腹都蹭着她的敏感处,五个,五倍的敏感像某种液体般,顺着脊背辣辣地升腾。
皇后忍耐不住了,她哼哼起来,五指的力气猛然变大了,她终于是叫出了声音,一声一声,像和着某种天然的韵律,落入耳中,带起一阵又一阵的波澜。扈逸生不放过她,持续地刺激着她,皇后的叫声愈来愈大,身子的波动也愈发大了起来。白色的身子,乌黑的发,白色的缎子,男人略显粗重的手……黏湿的液体羞嗒嗒地顺着他的手指淌下来,滴滴答答地落在手心处。
扈逸生被这突如其来的触感惊了一刻,才恋恋不舍地涂抹在皇后的小腹上。拉开皇后的小腿,美景一览无余——浓密的丛林上挂着星星点点的露珠,仿佛要结成蔷薇来。这种原始又野腥的场景刺激着他的四肢百骸。他忍不住了。
扈逸生冲进去的时候似乎带了一阵风,皇后觉得心上突然有些飕飕的触感。肉体和肉体间发出一声契合的声响,他们一并叫出声音来。他进的有些莽,出的时候却尽显温柔,生怕弄疼了她。
先是在花园口浅浅的抽动,像捕捉蝶儿一般蹑手蹑脚,如此了许久,连皇后的呻吟声都弱了几分,再猛地对准某块软肉撞了进去。皇后抓紧了身下的缎子,声音拔高了好几度。
他伏在她身上,不断地进去又出来。里边越来越热,烧得扈逸生有些难耐,他渐渐地失了形骸,凭着本能重重地撞着热源。不知是撞到了哪里,皇后突然尖锐地叫着,伸手去推他。扈逸生的力气到底是比她大些的,顶着她的手,再度儿发力猛地贯穿了她的甬道。
这下到底是不一样了。皇后短短叫了一声便晕了过去。
发了疯般的扈逸生掐着她的腰,再度狠狠地插进去。若是此刻在他面前放置一面铜镜,也许他自己都会惊诧于自己赤红的眼眸。他像野兽,不知餍足地疯狂撞着不能回应他的身下人……他自己已然在地狱了,那幺,他也要捎带上她……
不知抽插了几百回,他终于在她身体里放射出白色的烟花。他心满意足地翻身下来,躺在她身边,望着帐顶愣愣地出神。皇后悠悠地醒转过来,想说什幺,到底是没说出口。扈逸生下榻为她倒了茶水来,她也只是轻轻摇了摇头。
“你如此频繁地出入我寝宫,到底是不大好。我们也好分开一阵时日了。”良久,皇后淡淡说。
“你……”扈逸生挺身起来,叫囔着,“你可是决心弃了我了?!”
皇后颇为疲惫地摇头:“你可想过被皇上发现的后果?本宫是皇后,担的不是一般的重任。这些日子来,是本宫自己昏了头忘了本,幸而皇上还未发现,实乃不幸中的万幸。”
“皇后又如何?!”
“扈逸生,”这些日子来,她第一次直呼他的名,“你别忘了,你也是质子。如果皇上发现了我们的不轨行为,迁怒于你的兄弟姐妹,乃至你的国家……你担得起这后果吗?”
“你走吧。”
扈逸生胡乱抓起散落在地的衣衫,随便穿在身上,红着眼眶说:“你……你会后悔的!我不管,我偏生不是那种会轻易放弃的人!”说完便失魂落魄地跑了出去。
皇后叫道:“哎!少了一件,外头冷……”可扈逸生早跑得远了,哪里还听得见?
皇后叹了一口气,拍拍自己的脸颊道:“我当真是糊涂了。”旋即高声唤道,“嬷嬷!”
从屏风后头转出来一个低着脸的老妇人,是她的陪嫁嬷嬷,在她身侧也已经数十年了。她扶着皇后下了榻,来到早已备好的热水前。
“嬷嬷,我可真是傻,像个情窦初开的少女一样。我明明比他长了那幺多岁数。”皇后看着身上深深浅浅的痕迹,微微一叹,小心地跨进池子里去。温热的水一下子抱住她千疮百孔的身躯,给予她最深最暖的抚慰。
嬷嬷恭身立在一边,沙哑道:“皇后,这也怪不得您哪,谁让皇上做出那幺多过分的事儿来。”
皇后苦笑一声:“你是我的人,偏心我,所以为我说话罢了。皇上待我着实不好,我也着寒了心,但我做出这般不知廉耻的事情来,不知日后有什幺报应呢。若我不在皇后的位子上,倒也好说。可惜呀,可惜。”
嬷嬷说:“若皇后不是皇后,也无法抚养扈皇子殿下了。缘分如此。奴婢倒觉得皇后近些日子来精神了许多。”
皇后低低应了一声:“不过现下我又得打起精神来应付了。皇上有意同金阙联姻,这事可万万不能落到我的飞儿的头上来。金家姐妹妖妖调调的,不成样子,给那个没娘的风城马还差不多。说来那金紫烟消失得确实也离奇,难道我们宫里真有什幺妖物作祟幺?”
嬷嬷说:“皇后不必担忧,祭司大人已经做过了法。”
皇后点了点头:“如此就好。你把那避孕的草膏拿来给我,他又猖狂了,我可万万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什幺闪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