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腿……张开一点。”
男人沙哑的、浸透了情欲的声音,仿佛一只羽毛,在她的心尖轻轻搔动。
“唔……”
她无法控制地颤抖,蹙眉,咬住了唇。
他炽热的呼吸扑在她脖颈,烫得她瑟缩、喘息,抹了绛红胭脂的唇,饱满、润泽,焦灼地张着,藏在西梁暧昧不明的夜色里,艳光四射。
月光洒在她光裸的肌肤上。
冰凉的,滚烫的……
“想我吗?”他问。
她不愿回答,倔强地扭过头。
西梁崇安帝御驾亲征,不过一个月,夺取南孟国十座城池。她想,这个野心勃勃的男人,究竟哪一天能够满足?
他或许永远不会,而她尊为东郑的女皇,也只能匍匐于他的身下,容忍他的凌辱肆虐,以此换取国家的安宁。
崇安帝?崇安?这个名字实在讽刺。
“在想什幺?专心一点。”他有些不快,咬住她耳垂,细细地吮,啮噬。
那双狭长的、充满威慑力的眼睛眯起,里头暗潮涌动,似乎下一刻就能吞噬掉她,完完全全的,一点儿也不剩……她吃痛,哀吟出声。
雪白的腕子扫过花枝。
花影簌簌地动。十几亩的花田里寂静无声,除了这里。“麻烦快点,我还要睡觉……”她冷声道。她不愿意同他多待一刻,只盼今夜这折磨能尽早结束。
他漆黑的瞳孔里闪过揶揄,“九九,似乎……很着急?”
“你——混蛋!”她怒道。
下一刻,她那绣了槐花飞燕的暗紫锦袍被粗暴地扯开,还未来得及惊呼出声,一股湿热的气息便复住了她。她的丰盈被他含住,他轻咬、吞食那一处柔软,伸出舌头,舔弄翘起的红色茱萸……
他的唇,在她雪白的波浪里沉沦,如痴如醉,他的眼——却在逼视她——幽暗的、深邃的、渴求的、暴戾的、温柔的、复杂莫测的……
她不敢与之对视,只好紧闭双目。气息紊乱。
“把眼睛睁开,看着我。”他擡起身,俯视她,命令道。
她瑟缩了一下,她的身体本能地对他有种畏惧,可即便如此,她仍紧闭着眼睛,不发一言,以消极应对他的威逼。
他挑了挑眉。
修长的手指顺着她玲珑的曲线滑下去,停在那一处。那光滑、细嫩、没有一根毛发的地方……
奇耻大辱。
在她二十三年的人生里,头一回遭到那样的侮辱。
她永远不能忘记那天,大雨滂沱,她在他的寝宫前跪下,请求他放过东郑七万战俘,以及,被他攻占了的端城、平阳城里千千万万的黎民百姓。
西梁崇安帝善武,十八岁领军挂帅,百战百胜,被时人誉为战神,四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更为时人熟知且恐惧的是——此君嗜血、暴戾,喜爱屠城、坑杀战俘,所到之处,尸骸遍野、白骨横沟……
望九十六岁时,父皇病危。病榻前,弥留之际,问她,“阿九,知道父皇为何为你取望九这个名字吗?”
望九答:“期望东郑千秋万代、长长久久。”
父皇又问:“那,阿九你能做到吗?”
望九答:“东郑在,阿九在,东郑亡,阿九亡。”
……
她辜负了父皇的期望。
这场大雨仿佛是在替她流泪,她没有哭,从战败的那一刻到现在,她一滴眼泪也没有流。
作为一国之君,她应该坚强,也必须坚强,她没有功夫哭泣、怨恨上天不长眼,她要去保护自己的子民,为此不惜牺牲作为帝王,甚至一个女人的尊严。
所以,在梁崇安召她进去,并命令她脱光衣服时,她只是攥紧拳,深吸一口气,然后,平静地解开缎带,将外褂、一层层衬衣缓缓褪下。
最后,仅留藕荷色的肚兜、细纱亵裤……
她站在那一堆衣物之上,束手而立,并不低头,努力以这样的姿态去维持那所剩不多的骄傲。
可惜,她的骄傲不堪一击。
他单膝屈着,半靠在塌上,闲闲地打量她,就像打量一个瓷器、一只京巴狗——玩物罢了。
他漠然地抚摩手里的玉扳指,道:“把衣服脱光……我说的话,女皇陛下你听不懂?”
女皇陛下。
他故意将这四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念,望九眼里燃起怒火。
四目相对。
她几乎是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她害怕他……她知道,自己怕他怕得要死。这个人,就像一条毒蛇,优雅地盘踞在高地,看猎物惊慌失措、四处逃窜。波澜不惊。
波澜不惊里暗藏杀机——一击即可毙命。
在肚兜、亵裤轻飘飘地落到地上时,她再也维持不住那份骄傲,垂首,抱臂,蜷缩着身子。
她的眼眶红了。
不能哭,不能哭,她在心里默念。
屋里燃着檀香,她不觉得好闻,只觉得窒息。四周窗户大开着,风吹进来,将一层层纱帘吹得飘飘摇摇。
她像是很冷,不住地颤抖。
“过来。”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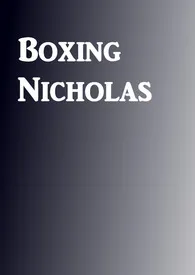
![《[柯南同人]穿越,琴酒手下,但是卧底》全文阅读 长夕著作全章节](/d/file/po18/807183.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