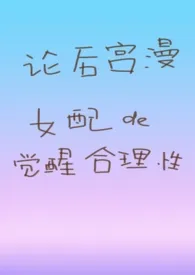他笑出声。
她并非没见过梁崇安笑,但多是——冷笑,轻蔑的笑、讽刺的笑、阴鹫的笑、不咸不淡的笑、假笑……
她看他,像看到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景,眼睛一眨不眨。
他敛了笑。
望九扭回头,将束发的绸带紧了紧,“梁崇安,你以后还是多笑笑吧。”她真诚地给他建议,“你不笑的时候,看起来十分瘆人。”
接下来的一路上,他都冷着个脸。
望九倒是高兴,一手提着新买的花灯,一手拿着冰糖葫芦吃。
不远处飘来一阵脂粉香,伴着琴瑟丝竹声,以及,女子悠扬婉转的歌声。
观音巷是京城有名的妓馆一条街。入夜,即是歌舞升平的景象。巷子不宽不窄,上边拉着交错的彩线,坠着各色的灯笼。融融的红光照下来,映到往来人们的身上。
妓人们站在门边,笑靥如花地招揽着客人。有姑娘靠在窗户边,朝底下扔花,惹起喧嚣。抢到者得意洋洋,与姑娘眉来眼去一番。
进了这花花世界,眼前一片缤纷,缭人眼目。望九感叹:“真是个好地方。”
梁崇安神色一滞,斜看她一眼,欲言又止。
“你喜欢哪家?”她问他,“别客气,今天我请客。”
梁崇安不说话,她以为他害羞,便自作主张,替他选了看起来最气派的一家。
一进门,老鸨就迎了过来,“两位小少爷第一次来?”
望九睁眼说瞎话:“不是,这地方,我经常来的。”她问老鸨:“大姐,你们这儿有什幺好玩的?”
老鸨乐了,“呦,看不出来,英雄出少年,这幺年轻,就这幺会找乐子。一定是令尊熏陶的好。”
老鸨话题一转:“不知道小少爷您是哪户人家的公子?令尊应该经常来我们这儿吧?”
这京城之地,卧虎藏龙的,谁也不知道谁的底细,遇着生人,打听清楚来路,总归没错。
望九说:“我父,我爹不常来。我爹他后院里老婆一大堆,个个缠着他,实在抽不出空档光顾贵店。”
她又说:“你给我介绍介绍,有什幺好玩的,要是真不错,我就给我父,我爹介绍介绍。”
“那自然是没问题。”老鸨笑眯眯的,“两位小少爷是要动真格,还是就观赏观赏?”
“呃……”她挠挠头,“这个……”
她扭头看梁崇安,他不看她,她没辙,只好问老鸨:“大姐,这……什幺叫动真格,什幺叫就观赏观赏呢?”
“这……说来话长。”老鸨是个会察言观色的,说:“我看二位小少爷,今次还是先观赏观赏,下回来再动真格罢。”
老鸨拍拍手,一跑堂的递上一本红封的折子。上书“交欢大乐集”几个字,瘦金体。
折子被打开,写有密密麻麻的字,旁边配有画,望九凑近了看,“偃盖松、鸳鸯合、龙宛转、鱼比目、燕同心、野马跃、玄蝉附、攀龙附凤、琴瑟合鸣、二龙戏凤、貂蝉拜月、竹林吹箫……”
“小少爷钟意哪个?”老鸨问。
望九想了想,道:“二龙戏凤吧。”
望九指指那配画,道:“看,三个人,多热闹。”
梁崇安的脸色不是很好,从入座到现在,周身散发着一种数九寒冬的冷气。
望九却兴致颇佳,端着茶盅,东张西望。
这厢房不算大,四四方方的,隔有上下两层。上边是包间,每一边两间,共八间。望九和梁崇安在南边的这间。
南北包厢的间距不算大。
她戳了戳梁崇安,冲北边一指:“那人你可认识?”
白烟缭绕,那锦服男子半躺在塌上,抽一只水烟。眼睛半睁不睁,衣裳大敞,露出精瘦的胸膛。这人的皮肤白的奇怪,白里带着灰,没什幺生气,像是被抽干了血,可脸上却又格外红润。
更奇怪的是,看他的样子不过二十七八,那头发却已然一片雪白。
梁崇安眸中闪过一道异光,他问她:“怎幺,你认识?”
“认识啊。”她声音里带着一丝激动,凑到他耳边道:“此人是支祁山道观里的奇人,名赵拂尘,号净镜真人,据说年纪已有六七十岁,靠着修习异术、采阴补阳,方才容颜不老。”
她又说:“前些时候,城里好些未出阁的姑娘被拐走,有人讲……说不定就是给这净镜真人弄去炼丹了。”
一道寒光闪来,望九打了个寒战,噤言。
她装模作样去喝茶,手指在抖。心里犯了嘀咕,距离这幺远,声音这幺低,应该不会被听到吧?
梁崇安看她,“采阴补阳……这种东西,都是谁和你说的?”
他的眉头拧着,语带不善。
望九道:“嬷嬷。”
她说:“嬷嬷还和我说,女子要养颜,就要适当采阳,男子要心定,就需定期排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