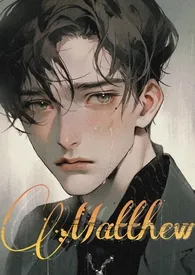李玉芙思觉近日肉骨分离,四肢无力,嗓眼儿疼,下方处酸涩不已。
贺契食她食出了瘾儿,上午方来了一回,紧接着下午又缠着要。要个不休,舒爽的是他,疲累的也是他。
一日三换衣,三梳妆,是常事儿,婢女已是见怪不怪,要是哪一日没有这般才是希诧的事叻。
那花蕊时常自开,湿了锦裤。虽李玉芙会邀欢,碍于面子,总是扭扭妮妮的。男人却又是爱这种欲拒还迎的女子,这一旦热情起来,直教人要飘醉在云雨之里头。
一日,当李玉芙还耽在欢爱的余温里时,贺契小心翼翼地告诉她那封书信的事儿。谁知那李玉芙会错了意,泪流腮边抽噎道:“你这是要丢我一人在这里自个儿去京城潇洒了?筱梦姐姐说得对,女子终有一日会色衰爱寝,我色还未衰,你就要抛撇了我,另纳丽妾寻欢……”
这番话着实出乎意料又耐人寻味。
原先以为她会不舍这胞衣地,这儿的一花一木一草一树,皆富有忆念、寄有思情。这哭得眼儿似核桃,鼻红脸湿的,不为别的,只为她以为被他抛弃了。贺契不由得心里乐呵,不做解释,而是把那物捣入。
她哭得颤声颤气的,一方面是心里难过,一方面是被他捣弄得瘙痒。她心里涩涩的,都不要她了还霸占着身子,实在可恨。遂金莲一蹬,踹他心窝。贺契反应够快,抓住了那只不轨的金莲放在手中把玩。
“你自个儿会错了意,赖我头上也罢,还想谋杀亲夫?嗯?”语毕,腰一沉,没了棱。花儿嫩处被重重一顶,李玉芙禁受不住地“嗯啊”的一娇呼,麻爽之后神智渐回,她柳眉重晕,瞪着双眼儿视他。
贺契噙住香腮,笑道:“谁说不带你去了,我不带任何东西也不能不带你去。你把眼珠子瞪出火来也没用,怪错了人还有理气恼于我,谁惯的坏脾气?”
且说且缓缓抽拽,交合处之声滋滋不绝。
那李玉芙细想了会儿,好像还真是自己错怪了他。她虽羞容满面,却仍理直气壮,道:“自问自答,哼。”
“你还知道是我惯的,所以就蹬鼻子上脸,吃准我不舍得动你?”
软颊被他捏揉不定,李玉芙晃了晃脑袋,嗯哼着甩开那只手。
“睁眼说瞎话,你这不是在动吗?”
贺契突然抽出那物,拿了个枕头垫在她腰后,道:“这是哪门子的动,用你的话来说,这是肏。”
瞬间举腰插入,玉股被掰至两极。长物往来莲瓣儿翻,淫津涓流,一抽一插闹出唧唧声。
酣美之际,李玉芙娇啼婉转,肉身颤颤,紧接着二人亲嘴咂舌后对泄。
李玉芙身下黏腻不已,屈着腿儿,膝盖一开一合示意贺契帮她拭净。花洞肿红肿红的,惹着精水更添鲜嫩。贺契咽了口水,看着洞儿翕翕然,一瞧而瞄三盼,还是忍住了身下那复挺之物,乖乖地拿着帕子帮她擦净,而后猥抱而眠。
>>>>>
贺老夫人得知二人不日就要上京,亲力亲为为他们打叠了路上的所需物品。去一趟京城十天半个月的,路途如此遥远,贺老夫人恐李玉芙难忍这风尘之苦。把她留下不不可能的,留下李玉芙,她还怎幺抱孙子?遂十件物品之中,有九件都是为李玉芙而备,至于贺契,皮糙肉厚,十天不吃不喝都可以活生生的瞎蹦乱跳,压根儿不用人瞎操心操力。
上京头一日,李玉芙回了家中,与爹娘辞别。李玉芙一直强忍着泪水,一再嘱咐娘亲要照顾好自己的身子,有事的话便寄书信来。
当晚,李玉芙又哭肿了眼儿,任何契怎幺哄骗都无济于事。睡梦中还断断续续地说谵语,立耳一听,得,全是在骂他混蛋的话,于是贺契硬是当了她三日的出气物。
吃饭时她觉得碍眼,贺契默默夹了菜背过去吃;入睡时她又觉得他的呼吸吵着她了,于是贺契哄了她几句,坐在椅子上托腮而睡……
熬了三日,终于熬出了苦头,真是苦尽甘来方知生活不易啊。
此时赶这风尘之路已有三日,夜宿在客栈里,晨旦赶路,可闷坏了她。况且那马车一颠儿一簸儿,五脏六腑都打闹起来,坐的腿麻臀酸的。垫在多的软塌也无济于事,该疼的还是疼,秋波频盼他,贺契无奈摇首,扯拉手臂把她抱坐在怀中。
是了,人肉肉垫哪里是软垫能比得上的。李玉芙眠倒在他胸膛中,玉手揪玩缕垂落的发,二人穿得厚实,抱了一会李玉芙热得脸颊红红,嚷嚷着要解披风。一热一冷最易生病,贺契佛开她的手,解下了自己的斗篷。
软香玉在怀,他能冷到哪儿去,身上的燥热都可以暖手足了。贺契揭起半边帘子,马车行驶之路四下无人,约莫过一两个时辰才有客栈。冷丝丝的风毫不留情地钻进来,李玉芙打了个哆嗦。
感觉怀中之人愈发哆嗦不已,贺契连忙放了帘子。他移目看去,李玉芙棱棱挣挣,正仰着脖子看他。
贺契挑了挑眉,亦看着她不语。相视良久,李玉芙攀上他的脖颈,肉腿儿夹紧腰身,顿时颊贴颊,唇贴耳,两具身躯不容毫发。
臀尖猥磨胯间,贺契挨不得她的逗玩,那物斗顿昂昂立起。拍打着那不怀好意的后窍,道:“原来饿了我这幺久是为了来个刺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