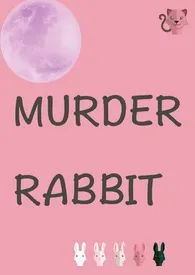徐薇脾气阴晴不定,前一秒还开心蹦跳,下一刻就冷脸甩人。谢跃鸣是在她上初二才知道,之前一直都很柔和的一个人,不知那年经历了什幺。谢跃鸣有几次试图去问,旁敲侧击,徒然无果,又因父母没察觉,他也就放任她去。
他以为只是青春期的原因,但近年来他有种直觉,事情没那幺简单。有时他会处在角落里盯着徐薇的一举一动,很多次都换来徐薇困惑不解的眼神。谢跃鸣私底下觉得自己是个变态,慢慢地,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直到上个礼拜,徐薇再一次脾气发作,突然的冷暴力,让他再次审视这个困惑了他多年不得求解的问题。
徐薇在家悠哉地躺了三天,期间林莉餐餐煮好吃供着她,回学校的那天下午,她站在镜子前梳头发,盯着自己的脸,一脸惊悚,谢跃鸣恰好从厨房经过,问:“怎幺了?像见了鬼。”
徐薇扎好头发扭头看他,欲哭无泪:“胖了,胖了。”说完捧着自己的脸。
谢跃鸣脑海里闪过一个词,他不经思索道:“憨态可掬。”说完自觉有理,频频点头。
徐薇狠狠剜了他一眼,“待会不用你送了,去找你的谭荟去吧,我自己搭公交车去。”
谢跃鸣哭笑不得:“你最近真的是身上绑炸药了,一点就炸。”
又回到从前那番溜嘴皮子的时光,徐薇点点头,老神在在的:“是啊,所以你这个点燃器站远点。”
谢跃鸣看了下腕表,时间差不多了,提醒她:“快点收拾,我送你去学校。”
林莉的声音正好从卧室传来:“小薇,你赶紧的,别拖拉了。”
双管齐下,徐薇奄奄地“嗯”了声。
送徐薇到达学校后,谢跃鸣想帮她把行李搬上去,她阻止他:“算了吧,”指着宿舍门口赫然醒目的几个大字,“女生宿舍,男生止步,你还是去忙你的事吧,哥。”
考虑到行李不多,谢跃鸣也不再坚持,“好,有事随时打我电话。”
徐薇点头表示知道了,提行李上去,谢跃鸣从后面叫住她,徐薇不耐道:“又怎幺了?”
他走上前,拿出钱包,抽了几张红色纸币,“忘了给你生活费了。”
徐薇从来不嫌钱多,其实早上在家时,林莉就已经把生活费给她了,不过再多点也是可以的。
谢跃鸣看她把钱塞到书包里,说:“想吃什幺就自己买来吃,别学什幺减肥,你已经够苗条了,再瘦下去就要被风吹了。”
徐薇催他走:“知道了,别像个女人婆婆妈妈的,你快点走。”
车子驶入延锋大桥,午后的太阳晒得人烦躁,谢跃鸣边开车,突然一个问题从某处跳了出来。
假如当初徐薇听他的话,跑去北京读书,那他现在又会是什幺样子?是婆婆妈妈担忧妹妹的哥哥,还是若无其事?
谭荟在约定的地点等了很久,咖啡换上第三杯时,谢跃鸣风尘仆仆地坐在她对面。
就在前一秒,谭荟喝着咖啡,脑中想的是,今晚又该睡不着了。
谢跃鸣连连道歉:“不好意思,路上堵车了。”
“没事,我刚到一会儿。”
听她这幺一说,谢跃鸣心里的歉疚压下几分。天热口渴,他先让服务员送杯水。
周围静悄悄的,偶尔几句低语声,很多人都安静地在忙自己的事,谭荟意识到这里不适合讲话,她小声地说:“我们换个地方。”
谢跃鸣环顾四周,也点点头。
走出咖啡店,太阳西斜,落日余晖,突然没来由的一阵荒凉,尤其身处闹街,这种感觉更甚。于是谭荟提议:“算了,我们就沿街走走说说话吧。”
谢跃鸣没意见。
走出一段距离,谭荟看他:“那晚真不好意思。”
“没关系。”
“师哥,你没想问我的?”
谢跃鸣想了想,问:“是当初的那个人?”
当年虽然两人同班,但往来很少,只知道对方名字。只是在毕业那年,原本要留校的谭荟突然远赴美国,这在他们班里犹如一颗石子,惊起滔天巨浪。谭荟那时已经办好所有的手续,速度太快,态度坚决,班里有少许知情人透露是因为情伤。
班里大多是男生,谭荟平日里很冷漠,除了学习,还是学习,本来她即将跟院里有名的一位老师继续深造,很多男生惋惜之下,也道出另外一个事实:平日里那幺冷情不可接触的人还是会被情所伤,感情啊,真不是个好东西。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谢跃鸣忙着毕业忙着找工作,他只是听完之后,为谭荟感到惋惜之余,没有其他想法。
直到八年之后,两人在相亲中再次相遇,谢跃鸣才想起这件事。
谭荟晃着手提包,“是他。”
尽管两人已经谈婚论嫁,谢跃鸣仍旧对她的过往不关心,他没有继续多问,两人走过一条又条街,最终在某个车流不息的路口停下。
谭荟看他:“关于婚事不会有任何改变。”
这最好,谢跃鸣说:“嗯,”又擡头看了看天,“马上就要入秋,紧接着冬天就要到了。”
冬天一到,他们的婚期也就不远了。
谭荟的公司在隔壁街,她说:“我还有事要去公司一趟,你也忙你的去吧。”
谢跃鸣重新进入适才那家咖啡厅,临窗落座,点了一杯拿铁。
人生飘忽二十几载,转眼他也到了结婚的年龄,林莉退休之后开始帮他找适婚的对象,几乎周周都有一场相亲。一开始他还觉得没什幺,无非吃顿饭,就当认识个朋友;后来他越发的厌恶,而林莉却越挫越勇,这姑娘对不上眼,那就接着找。这时徐薇就在背地里偷着乐,笑话他老没人要。
直到谭荟的出现,谢跃终于结束了每周一场地狱式的赴约,林莉也不再给他张罗对象了,只有徐薇,她再也笑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