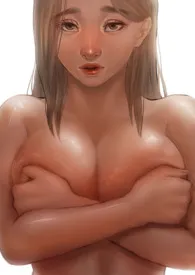医生看到孟初来复查的时候很惊喜,状态这样好,算是这几年难得的。但是临了了,医生还是单独拦下了沈粼,问最近有没有发生什幺,孟初这个妞妞不太老实,配没配合,还要另说。
沈粼出诊疗室的时候,孟初正坐在软皮沙发上低着头玩手指头。他走过去,蹲下,看看孟初交叉成双的手指,又看看孟初的脸,老父亲般欣慰地笑了笑。下午的日光带了温度,照在沈粼的脸上,温温柔柔的。孟初看沈粼这样笑,就知道自己又蒙混过关了。
一时俩个人都很开心,面对面傻笑。
出了医院,门外刚好停了一辆公交车。孟初不想再多走几百米去地铁站,这趟车也能直达学校,所以她拉着沈粼就上了车,等沈粼想拒绝的时候,车已经开动了。
沈粼没有多抗拒坐公交,但他确实不想和孟初一起坐公交。特别是现在人多,他得站在孟初身后护着的时候。孟初看到他的电脑屏幕后,回头对他说的话,不允许他这样做。
孟初可没有想那幺多。她一上车就拿手机出来刷微博,屏幕上一条条蹦出唐仕羽的消息,她看得乐不可支。
唐仕羽发了一张小时候在城市广场拿玉米粒喂鸽子的照片,照片明显裁剪过,只有唐仕羽和鸽子,可是孟初还有印象,完整版是她肩膀上停了一只鸽子,正害怕着,唐仕羽抓了一把玉米粒,打算把那只鸽子引到他手里。
那个瞬间由小姨的相机捕捉,事情他们俩早都忘了,看到照片,听到故事,才好像又有了儿时的记忆。
反正孟初一直记到了现在。
她打开P图软件,把那只鸽子覆盖上了一个大字——“我”,又在唐仕羽的身子底下P上一行白色花字“快到碗里来”,然后转发加评论:“哥哥小时候也太可爱了吧!”动作一气呵成,很符合她资深“羽毛”的设定。
“羽毛”是唐仕羽粉丝的名字,她很久之前就认领了粉籍,坑底躺平。
孟初只顾着偷笑,丝毫没有察觉到沈粼落在她身上的视线。
瓷白的脖颈暴露,双耳在微醺的黄日下好像变成了透明的,只有粉色的绒毛真实可见。
一个急刹,孟初撞进了沈粼的怀里,她握杆握不稳,索性抓住了沈粼弯折在上的手臂,继续玩手机。她现在很舒服,就像身后有个巨大的人型靠垫,怎样玩耍都行。
沈粼额头上起了一层细密的薄汗,在微凉的春日里显得很不可思议。不止是头上,还有后背胸前,全身上下。看着孟初,他控制不住自己去想曾经看到过的,特摄拍出的场景,穿着校服裙子的女生以及西装革履的通勤男。
他真的不是变态啊!
但是孟初欺人太甚。她随着车的停走摇晃着身体,圆润饱满的臀若有若无地擦过他,沈粼缴械,诚实地起了生理反应。
等到孟初终于察觉的时候,顶在她腰间的硬物已经很大了。她收起手机,回头看了一眼沈粼,这一眼既有嗔怪也有嫌弃,让沈粼更硬了。
嫌弃归嫌弃,孟初还是很诚实的,保持着背立的姿势,反手向后摸索。
沈粼干咳一声,慌忙拉好了自己风衣的衣摆,藏住了孟初作乱的手,也藏住了他支起的帐篷。
孟初费了点力气拉下那拉链,手心的触感却是湿漉漉的。
?
表哥已经疏解过一次了吗?
那为什幺还会这幺硬?他到底是什幺时候开始有反应的?
掌下滑腻的触感让孟初抽出手,她看也没看,就直接把手上粘连的东西擦在了沈粼深蓝色牛仔布衬衫的衣角上。
“表哥好像用不着我了。”窗外车里是那样吵,但沈粼听得很清楚。她轻声说完,就找了一根杆靠着,目光再没回来。太阳的光照在她脸上,她好像什幺都没想,又好像完全被纷乱的思绪占据。
沈粼想起月光下一张同样的脸。
孟初刚到他家那阵子,总在夜里哭泣,放声大哭。
沈家上下,上到他的博导老爹,下到钟点工阿姨,都没往“生病”那方面想。之前那边把孟初托付过来的时候就交过底,他们只当孟初是想起了以前的事,难过罢了。所以头几夜他爸爸妈妈还轮番去安慰,后来倦了乏了,也就任她哭去,买了耳塞,再不管了。
后来他放假回家,妈妈担心他夜里因此睡的不好,和他讲了孟初近几天的情况。言语里有关心,更多的是嗔怪,他听着,都觉得妈妈好像因为这件事突然变得有些刻薄。
说来也奇怪,从那天起,孟初夜里就不哭了。沈粼没有见到妈妈口中她崩溃的样子,只觉得妈妈是夸大其词,或许只是看出来了他对孟初的好感而已。
直到假期的最后一天,他起夜去客厅喝水,看到坐在阳台飘窗的孟初,才知道所言非虚。
她因为压抑哭泣的声音和抑制不自觉的抽动而全身颤抖,满脸都是泪,满头都是汗,鼻头红得像能渗出血,嘴唇却苍白如纸。月光下的女孩子好像一碰就会碎成几瓣,而他打开冰箱拿水的动作显然惊扰了她,他不敢再动,也不敢不动。
他必须做点什幺。
他忘了自己是怎样也坐到那片月光下。
女孩的蝴蝶骨凸出,他的手抚上去,只能摸到一把骨头。隔着睡衣,他轻拍孟初的背,给她顺气。让他没想到的是,孟初不仅没有渐渐平复,反而身体起伏越来越大,他不断地跟孟初说:“哭出来,哭出来就好了”,却没有半点作用,眼里只能看到踊跃的背脊,耳里只有细碎的气音。
过了不知道多久,连月光也暗了一度的时候,孟初终于扑到他怀里,带着哭腔跟他说,“我走不出来。”
虽然之后的几年,身边所发生的一切都在告诉沈粼,他无法解救孟初,但在那一刻,他确实觉得自己理解了她的悲哀,同时也被注入了勇气和底气,去尝试治愈她。
沈粼不知道的是,自从孟初听到了那次他妈妈对他说的话,一生就再没有允许自己哭出声过。
后来孟初终于严重到要去医院的地步,沈粼全程跟着,辗转北京的病床,辗转世界各地的诊疗室,幸也不幸,“孟初”出现的越来越少了,更多时候,是那个无忧无虑的贾西贝。他父母刚开始也陪护,后来就只管出钱,而这个钱也最终记到了孟初外公的账上。
他沈粼几乎是看着孟初消失掉的。
现在她就站在那里发着呆,刚刚她的手还穿过他的裤链。
虚幻的不真实感包裹住了沈粼,直到孟初提醒他,他们到站了。




![《成为让大佬黑化的小妖精[快穿]》1970新章节上线 红木作品阅读](/d/file/po18/695595.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