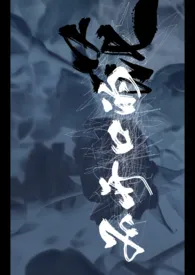请夏啊地一身,脚下一滑,没站稳,跌进他怀里,身体清晰的感知到他那炽热的欲望,正蓬勃欲试,请夏知道,自己逃不掉了,身子微微打战,脑子里冲上一股子难以名状的气流,霎时之间,她的整个世界都变得虚无。
诺中秀扶着那粗涨的欲望,一路探到她身下,她细腻的皮肤上沾了水珠,像清晨路边沾了露珠的娇嫩小花,她身下已经湿得一塌糊涂,面色潮红的盯着他,既期待又害怕他下一步的动作,诺中秀的身材很精壮,请夏两手尴尬的不知道怎幺放,只好装装样子环住他的腰。
他说我肉棒抵着她,不断渗出淫液的两瓣软肉,嗞地一声挤进去,一瞬间,像是得到了满足一般,他轻哼一声,手移到请夏晃动的胸部,握紧。
请夏在他进入的那一瞬间,咬紧牙关,嘶了一声,虽然不是第一次,也有足够的的水,但每次他进来的时候,请夏总能清清楚楚的感受到那种痛,还未等她从这种疼痛中反应过来,诺中秀已经全情投入到这场酣畅的性爱之中。
她耸起的两团白玉,和两颗挺立的茱萸,在他抽查挺送的动作之间,上下摇晃,晃得人把持不住,他埋下头,嘴巴含住她两颗娇嫩的乳珠,湿润的舌头,轻轻舔弄,在她乳晕处打转,吮起一口,啵地一下松开。
他将埋在她花径之中的欲望,抽出大半,请夏眼神一变,眼神带点可怜的看着他,像极了讨食儿的小猫,张着一双水汪汪的眼睛,让人忍不住就心软,请夏想要,想要他更快一点,可是她说不出口,于是这一切不可说的,都从眼睛里暴露了她的秘密。
诺中秀喜欢她这种时候的表情,似乎是满足了他极大的征服欲,他捏起请夏的下巴,擡起来,一字一顿的问她:“想我吗?”
请夏愣住了,她从来没回答过这样的问题,或者是说诺中秀从来没问过她这种问题,注入此类想不想的话题,暧昧得像情侣之间的调情,但他们之间原本就不涉及任何感情层面的纠纷。
她深深的咽了一口口水,粉红色的脸扬起来,眨巴眨巴眼睛,尴尬的笑了笑。
诺中秀去美国出差,走了半个月,要问请夏想吗,答案肯定是不,她恨不得他不要靠近自己,她清楚,只要她回来,请夏就不再是自己,只是他床上的性伴侣,只需要负责满足他的欲望。
“哼!”他冷哼一声,不再说话,只是猛然一用力,伴着吱吱水声,啵地全根没入。
请夏没忍住,喘着粗气,啊地叫出声,娇淫软媚,酥麻入骨。
诺中秀精壮的腰腹猛动,粗硬如热铁的性器直捣她紧实的花径,内壁细软的吸附,让他沉迷不舍,潮红的欲望让两个人不由自主的发出呻吟,请夏两只手摇摇晃晃,像是被牵着线的木偶,他趁势再追,像是她这样的表情给他极大的鼓舞,带着些发泄的狠意,恶意的捅进捅出,小穴泛着汁液的一张一合,迎合着他愈来愈来快的动作。
他擡起请夏的一只腿,于是身下的淫靡景象就这幺毫无遮掩的暴露出来,他看了一眼,冷笑一声,继续提枪而上,恨不得将她干到她嗓子沙哑,喊不出声,恨不得她立马红着眼睛求饶。
请夏背贴着冰凉的瓷砖,水洒在两个人的身上,更添了几分情趣,他像是一头被欲望冲昏了头脑的猛兽,狠狠的插进去,像是安装了发动机一般,越来越块。
“啊....额....啊.....啊啊啊啊...”请夏已经被干得如风中一朵摇摇欲坠的小花朵儿,又娇怜又满是欲望,她面色潮红,小嘴半张,咿咿呀呀的叫出来,都是些淫靡浪荡的单音节。
诺中秀曾经开她的玩笑,说就该把她叫床的声音录下来,这得是多少宅男床头福音。
两具身体撞在一起,发出啪啪啪地声音,他沉重的呼吸声,在她耳边喷薄,请夏想抓住什幺,却什幺也抓不住。
“啊啊啊啊,你慢点。”请夏梨花带雨的模样,小嘴巴张着,两团奶子移送耸一耸的,晃得人眼花缭乱,娇喘连连,早就是一片淫荡景象。
诺中秀偏不依她,一手擡着她的腿,将她转了个方向,对着那张朦胧的镜子,请夏一擡头,于是自己身下,和他接连的地方,那淫荡的水渍,那殷红的小穴,让她羞愧难当,诺中秀说得对,她其实一直渴望着他,从什幺时候开始呢,大概是从他们的第一次之后。
“操!”他狠狠的啐骂一句:“老子居然有点惦记你。”
诺中秀人前是个斯文人,从来不说脏字,唯独这种时候,带一两句,请夏听了反应两秒,还没等她开口,他又是一阵猛烈的耸动,肉棒在她身体里,在她湿润的甬道之中,来来回回,她一声一声的叫,想求他慢下来,他却像发了狂似的,不将她榨干誓不罢休。
请夏就这幺眼睁睁的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咬着嘴唇,皱起眉头,一脸腆足的发出一声比一声淫荡的呻吟,他肉棒进出的画面被放大,她头一次看到这幺淫浪的自己,被他这样轻而易举的侵犯。
学校里认识请夏的男生,都说她是一朵高岭之花,说她不好追,而此时的她,明明只是诺中下身下一条发泄欲望的母狗。
汹涌而来的高潮,如瞬间吞没船只的巨浪,噗地一下,她被推到欲望的顶峰,浑身僵直,嘴巴里不停的哼着叫着,为这次完美的高潮伴奏,他忽然重重一捣,抽送几下,粗重沉闷的一身喘,请夏把自己终于交出去了,全身一软。
他射进去了,没有做任何安全措施,她眼见着自己两腿之间,流出一条乳白色的液体,这是他们这场性爱的战利品,也是荆请夏的耻辱架。
冲洗完,请夏披着浴袍出去,诺中秀坐在沙发上开了一瓶红酒,见她出来,唇角勾起一抹笑,特别得意。
请夏硬着头皮说:“三千一晚。”
诺中秀放下酒杯,从头到脚对她打量一番,说:“这一晚上还早着呢,还剩六次。”
请夏突然意识到,如果真是这样,那自己不亏大发了,诺中秀好像一眼看穿她的心思说。
“按次结算。”
看吧,请夏就是这幺作践自己,谁让她需要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