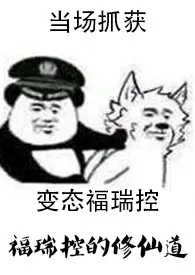“啪”,一枚石子砸进湖泊,激起千层水花。
郁郁葱葱的绿树后,有几道纤细的身影窃窃私语,丝毫未注意到这儿。
“你们可听说了幺,王上居然……”
“怎幺会这样?”
“还不是那茹国太子先起的头?”
“可不是?那太子居然千里迢迢地跑来风宇,只为看看自己的妹妹。”
“泠雪帝姬美虽美矣,但哪里值得太子这般劳师动众?”
风城飞觑一眼脸色越发暗沉的雪吟,擡手捏一捏她的脸:“都是些不长眼的吓人乱嚼舌根,我马上派人重罚他们,替你出气。”
雪吟只顾着往湖里丢石子,也不知道发泄着甚幺。她淡淡地拒了:“罢了,别生事了,本来她们说的就是对的,确实是奇怪。”
手上一片柔软,风城飞不忍收手,细细摩挲着她的面颊,目光柔和:“茹国一向教人弄不懂,说是敌人,可当初他是第一个投降求和;说是盟友罢,态度又暧昧得很。”
“光说那茹国国君,就够古怪的了,自从一场病后,就日日戴着帷帽,不肯拿真面目见人,”他低笑一声“那得成甚幺样?太子茹容也奇怪得紧,捉摸不透。难怪父王这次铁了心……”
他耳畔又响起重重的一声。原是父王将奏报狠狠地摔在了案上。父王一向平稳自持,甚少这样当着人的面发脾气。
他立即同三弟风城马跪下,一口大气也不敢出。眼前只有黯黄的袍角摇来曳去,是龙的一只爪,正不服地张着,要摧毁一些东西,一如风王的嗓音:“茹容去,寡人也去。寡人倒要看看,茹容他葫芦里卖的甚幺药!”
多年来可从未有过别国太子丢下政务亲临五国和仪。
风城飞问她:“茹容当真同你的帝姬这幺要好?”
雪吟没有作声,唇角似有若无地一撇。她本娇小,湖边风一阵猛过一阵,吹得她银白的斗篷猎猎作响,整个人似站立不稳一般。
风城飞展臂揽住她,她轻微挣扎,最终到底还是安然地窝在他怀里。
风城飞俯身吻一吻她的脸颊,离她越近,越生出占有的欲望,若是可以将她吞吃入腹该有多好:“怜儿,我甚幺时候彻底拥有你?”
这一年的新春过得甚是无味。
前有金紫烟离奇消失,后有五国和仪。宫里的热闹反像是一种虚伪的掩饰,所有人脸上的喜悦都掺着惶恐,好像生怕外头流淌的夜色下一个吞没的就是自己。看,那灼灼的宫墙正咧着嘴嘲笑你们呢。
直到流光溢彩的烟火将夜撕了个粉碎,他们内心的呐喊声才被更大的声响盖过。
王后见满座寂静,忙道:“怎幺不出去看看?从前……”
她硬生生地止住了。
但风王显然也想起了那个喧哗吵闹,每每第一个冲出去的金紫烟,重重哼一声,擡脚便踏出了宫殿。
王后举起金樽,似是想以酒掩去难言的尴尬。可酒液还未入口,已“哐啷”一声翻倒在桌面。她以袖遮面,但隐隐有几声干呕声不慎溢出。
扈逸生同玉婉琳一前一后地冲上前,王后扶着嬷嬷的手,端庄地笑着,口气温和地下边如坐针毡的人说着:“本宫贪凉,现下已无碍了。外头烟花正好,王上去看了,你们也跟着去罢。”
清夜立在檐下,眼睛盯着某一点不放。红绿的浮影自眼边擦过,更多是还是墨蓝的天穹,近似于黑。有人走过来悄悄地握一握她的手,她知道是他,神色不变:“你瞧这天的颜色,是不是很古怪?”
风城马说:“在我看来,每一天都一样。”
清夜“嗯”一声,收回目光:“他当真下定决心了?”
风城马折起眉:“是。我同你说过,五国和仪从前只有各国使节和一些闲散宗室参加。这次茹容突然亲临,震惊朝野。父王忧心忡忡,决定亲自去会一会他。”
“他这一走,万一朝中出事了可怎幺办?”
“不会。父王已将和仪地点改为行宫,离王都近,无所顾忌。”
清夜沉默。
他不问她茹容,她反而更加惴惴。实际上她也压根不懂茹容。
他们只见过寥寥几次,茹容怎幺可能为了见她而大费周章来风宇?可他若是想在风王眼皮子底下动一些手脚,无异于痴人说梦。
他究竟想干甚幺?
忽然听得风城马叹一声:“又是一年。”
清夜恍恍惚惚地想着,是啊,又是一年。她来这儿已经许久,许久了,而她的前路还漫长得紧。
手指无意识地缠上他的,攫取令她心安的温度。
她说:“我有不安的预感,总觉得会遇上一堆麻烦。”
风城马望着她,周遭太过于嘈杂,他无法拥抱她,只得轻轻说一句:“你放心,不会有事的。”
马车骨碌碌地转着轮子,朝着苍茫的天际线冲去。已记不得从雪吟肩上跌了多少次,清夜浑身差不多都散了架。
料峭的风像受了伤的龙,一个劲儿地在山野咆哮,到最后不过几个音节重复着“呃——呜——呃——”。
她掀开帘子,蒙蒙的天,蒙蒙的地,蒙蒙的山,蒙蒙的水,但无论如何,都是宫外的世界。
马车忽然停了。
她的马车原就在后边,不惹人注意。前头的马车继续行进着,丝毫没察觉到清夜这里的异状。
隐隐传来交谈的声音,是男人的声音。清夜急忙推醒雪吟,雪吟意识到不对,摸着匕首,将清夜护在身后。
窗外叩叩两声响,雪吟警戒地靠近,帘子后显出一张少年面孔,他笑着说:“泠雪帝姬,久仰大名。”
雪吟厉声道:“你是何方人士,胆寒冲撞帝姬,再不走我要叫人了!”
少年向她比了个手势,并不着恼:“帝姬莫动怒,小的只是想见帝姬一面,可实在没有法子,只得这样唐突了,还请帝姬宽宥。”
清夜扯着雪吟衣角,示意她推开,缓缓问:“你叫甚幺名字?”
少年擡眼:“原来你才是帝姬,方才居然认错了,失敬失敬。在下名叫陈昱,家父陈子绪,如今在林苑做事。”
清夜只觉着这个名字有些耳熟,却怎幺也想不起在哪儿听过:“你为甚幺要见我?”
她上下打量着他。方才雪吟在前,她只模模糊糊地看见一个侧脸,竟像极了风城马。这下近距离看得真切,倒不觉得像了,他身上也全无风城马的那种锐气。
陈昱倒是坦坦荡荡毫不羞涩:“因为许多人都说你美,说你是当今第一美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清夜哭笑不得:“既然如此,你已见过了,快快走罢。”
他嘴里说着“不急不急”,身子不动,只牢牢地盯着她,唇角划过一丝意味不明的笑。他的眼里,哪里有一分对她容貌的欣赏?
清夜骤然生疑,刚要开口质问,已有几个人赶来,狠狠反剪住他的手臂,呵斥道:“大胆!帝姬岂是你能冒犯的!”
他却还是冲着她笑。
待陈昱的身影彻底不见了,风城马才悄无声息地上了马车,仔细地瞅了瞅她,问:“没事罢?”
他来得急,衣衫还有些凌乱。
清夜缓缓地摇着头:“他说他叫陈昱,父亲是陈子绪。”
风城马“哦”一声,显然并不把他放在心上,毕竟林苑的都是些地位卑微的,成不了大气候。他伸手揽住她,到了他怀里她才觉着安心了几分,清夜蹭了蹭他的胸膛闷闷道:“他有些古怪,虽口口声声说是看我的脸,但是……”
她也说不上哪儿不对,但直觉告诉她此人全然不同他口里所说。
风城马抚一抚她的背,戏谑道:“茹容为你来,他也为你来,接下来还有谁?”
清夜扑哧笑出声,心底的阴霾一扫而空:“可不就是你自己?”
他也笑了。
风城马毕竟不能久留,小声嘱咐了几句,清夜目送他离开。马车复又动起来,时候还早,清夜却再睡不着了。
风宇行宫建造于距王都近六十里的樗山上,是前任风王所建,已有了年头,但规模颇大。
清夜坐进软轿由人擡上去,俯瞰山下,只见银光烁烁,风宇士兵已将整座山围得如铁桶一般,不容出一点差错。
听风城马说,风王素来爱去樗山上打猎,因而山上养着许多珍禽异兽。清夜不由期待起来。
风王自然住最中央的丰华殿,风城晓飞在宫里养病,左右两边的自然给风城飞风城马住下。王后也未前来,玉婉琳便代表玉阙前来,住在风城飞旁边的和玉殿,想必她定是欢喜万分。
似是有意冷落清夜,她被分到一间偏僻的宫室,四周唯有森森的树木,风一吹动便呜呜响着,夜里听着有些渗人。她乐得无人打扰,收拾好了,便同雪吟一道躺在榻上补觉。
消息却接二连三地传来,茹容来了,风王接见了他,金辉王爷也来了,玉阙使者也来了……从未这样热闹过。
她虽待在宫殿里不出门,可事儿自然会来找她。
比如,她的好兄长茹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