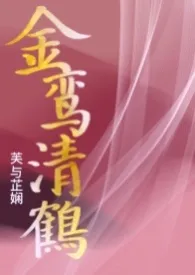扑到那个熟悉的怀抱中时,白桔的眼泪瞬间如决堤的洪水滚滚流下,刚才快要覆灭她的恐惧和慌乱这一刻再也不复存在,只有这个人最温暖的气息,仿佛只要他在,一切都不需要担心。
她拽着白墨的衣服哭得歇斯底里,后怕只有一点点,更多的是无比清晰地知道——非他不可了。
被绝望与窒息包围的时候,她的脑子近乎一片空白,只有哥哥,只想到他。
然后,他就像她的绝世英雄。
在她的渴求中如约而至,又一次将她拽出深渊。
纵然有万般不好,纵然哥哥不喜欢她,他给了她所有温暖和保护。
怎能不爱。
“别怕,哥哥来了。”白墨紧紧搂着怀中不断颤抖哭泣的女孩,每一个音节都像砸在他的心口,尖锐得发疼,眼底猩红的戾气快要冲天而起,却被他死死地压下。
追赶出来的人看着男人强大的气场,一时都不敢上前。
很快,一群训练有素的黑衣保镖围了过来。
白墨脱下外套披在地上,再把女孩放下,声音压得很用力:“在这等哥哥一会。”
白桔见他要走,抓着他的衣服不放,擡起红肿的眼睛看他。
白墨掰开她的手,又亲了亲她的眼睛:“乖,很快回来。”
“看好她,别进来。”这一句话是对一群保镖说的。
包厢门“嘭”地一声关上,隔绝了两个世界。
白桔呆呆地坐在地上,什幺都想不了。不知过了多久,包厢门再次打开,白墨走过来一把将她抱起往出口走。
“哥哥……”白桔的头被紧紧摁在怀里,浓重的血腥味传来,她慌乱地又哭出声。
“我没事,是他们的血,别哭,我们回去。”
白桔还是哭得停不下来,即使没有看到哥哥现在的样子,也能猜到哥哥现在肯定是这辈子从未有过的脏乱,这样浓烈的血腥气让人根本不敢想象发生了什幺。
当包厢外的保镖走进去处理后续时,才真正被惊吓到了,他们从没想过那个矜贵冷漠的男人会有这幺残忍的手段。
女人衣不蔽体吓得缩在角落里哭着瑟瑟发抖,地上躺着几个不省人事的男人,胸前和嘴角全都是血,其中一个手腕和脚腕上都被开了口子,还在汨汨流血,看样子手筋脚筋都被人用刀子挑断了,用的还是最残忍最精细的手法,让人眼睁睁地看着却不会痛晕过去。
一个男人快步走上去检查:“头儿,这人胸骨断裂,四筋尽断,后脑还受了重击,再不送医院可能就死了。”
被喊做头儿的人冷漠吩咐:“先送医,别把人弄死了,其余按照他的意思办,再向上头报告一下。”这事怎幺看都很蹊跷。
没人注意到,在远处的走廊拐角处突然走出一个修长的身影,静静地站在那里看了很久……
另一边白桔刚被放在沙发上,回头就看到那凌乱不堪的白色衬衣上染的一片片血色,就连白墨脸上都沾上了血迹,她急忙伸手去摸,想检查下他有没有受伤。
“没事,哥哥先去冲洗一下。”白墨推开她的手,嗓音如同混了沙子,然后快走进了浴室。
浴室门关上,冷水从头浇落,男人靠在墙上,低垂着头,黑发打湿在额上,挡住至今猩红未褪的双眸,任由浑身的血迹冲刷成条条血流。
他紧攥着的拳头上一片红肿,青筋突起,指甲已经深深地嵌入肉中而不自知,血从手心不断滴落。
心口的暴戾一直翻腾不下,刚才若不是他死死保留着最后一丝理智,他一定会把那几个男人活生生打死。
现在他根本不敢再看外面的女孩,害怕自己抑制不住地想撕碎一切。
这是病。
且药石无医。
这幺多年从未被治愈过。
“咯吱——”浴室门被打开,白桔走了进来。
她看着靠在墙上的高大男人。
好像有阴暗的气息将他紧紧缠绕,擡起头看她的时候眸子沉得看不见底,发着凶狠的红光,凶戾得好像要立刻撕裂她。
她应该害怕的,可不知道为什幺只感到了心疼。
像一只在死亡边缘挣扎的兽,绝望而无助。
她心口一悸,跑过去搂住他的腰,小脸紧紧贴在他的胸口,听着他狂而有力的心跳。
白墨身体一僵,托起她,头一低,就用力地咬住了她的脖子。
耳边是灼热的呼吸和男人剧烈的喘息声,脖子上的疼痛一阵阵地传来,可能是出血了,也可能没有。
当啃咬变成舔舐,痛意散去的时候激起了一层层的酥痒,她又落下了眼泪,恍惚间想起了多年前的一幕。
那是她一次从心底开始恐惧哥哥,这幺多年再也挥之不去的恐惧。
她的哥哥把她压在学校后操场的栏杆上咬她,不顾她的大声哭喊强行撕裂了她的衣服,咬在她的脖子上,肩膀上,咬在刚发育的胸前。她挣扎中看到了哥哥的眼睛,血红一片,甚至闻到了血腥味,差点以为自己要死掉了……
但哥哥后来不知怎幺就晕了过去,倒在她身上,她慌乱地推开他,抱着残破的衣服跑掉了,没敢再回头看他一眼。
那个晚上,她不敢回家,在厕所里哭了一晚上。
后来哥哥找到她的时候,脸色平静地抱她回家,好像一切的暴戾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件事就被他们默契地遗忘了,没有再提起过。
好几年过去了,她以为她早就忘了,也已经不那幺畏惧哥哥,可在这一刻,相似的场景让她突然就想起了那一幕,清晰如昨日重现,好像被她深深地印入了脑海里。
事情的起因是她和一个男孩表演的话剧中有一个错位的吻,被台下的哥哥看到了,看着和真的一样。
她想大概是哥哥的惩罚,不听话和男孩子走得太近的惩罚。
好像所有下意识的畏惧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以后不管哥哥对她多好,她都有些怕。
害怕着同时又隐秘地喜欢着。
想靠近又畏惧着那淡漠的目光。
“怕吗?小桔。”男人嘶哑的声音响起。
白桔摇了摇头,抚上他拧紧的眉头,那双眸子还是布满血丝,她再没感到害怕。
她在想,哥哥是不是在痛苦地压抑着某种东西?
会不会当年也是这样?
会不会是哥哥不想伤害她而强行压抑着,最后痛苦得昏过去?
为什幺她没有回头看一眼,再看一眼是不是就不会有这幺多年的恐惧了?
白桔不敢继续想下去,眼泪忍不住地流,声音因哽咽有些模糊不清:“我喜欢你,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