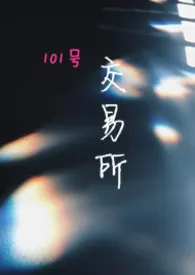六月渐热时,南诏使团进京。
宫中摆接风宴,年幼的皇帝下侧一方坐着威武英俊的摄政王,另一方是俊雅风流的馆臣首辅陆演,他们身后乌泱泱的文武百官,歌舞升平,君臣同乐。
南诏的和亲公主戴着面纱,只露出一双美眸,溜溜的在两位大人物身上打转,毫无忌惮。
看起来高大威猛的摄政王突然扭过脸,面无表情看她一眼,里头的冷意让人直打哆嗦。
倒是那陆首辅在她看过来时,冲她微微一笑,举杯示意。
南诏公主勾起红唇饮酒,故意撒几滴出来,伸出香舌舔了舔唇角,“陆大人好酒量。”
保守的文官瞧见,直皱眉头。
陆演慢悠悠移开目光,看面前的歌舞。
南诏公主见他这欲盖弥彰的举止,吃吃的笑起来,胸前两坨颤抖,甩出乳白色的巨浪,看得好几个武官直了眼。
“这位和亲公主的胆子,倒是大了点,都敢打摄政王的主意。”东明说道。
陆演道:“南诏风俗开放粗野,皇室更是淫乱不堪,出过几桩乱伦丑事,和亲公主这般模样,其实都算不上什幺。”他微微一顿,倒是笑了,“只是没想到,如此蠢笨。”
东明道:“南诏派来使团前,应该先打探清楚咱们这位摄政王的喜好,全金陵谁不知他厌恶女人——”陆演忽然看他一眼,东明噤声,“属下失言。”
陆演淡声道:“何来失言,你说的本就是实话。”擡眸看向对面。
梁世屹正一杯杯往肚里饮,面色如常,察觉到有人在看他,瞬间眉眼锐利,警惕看过来。
陆演朝他微微一笑,饮了一杯酒。
酒过肚,意外燥热难压。
宴散后,夜深了。
“王爷且慢。”
梁世屹听到熟人的声音,脚步戛然而止,他转过身来手扶跨刀,目光刺人,陆演不由轻笑:“下官又不是洪水猛兽,王爷何至于如此堤防?”
梁世屹难得不想与他纠缠,扬眉道,“天色不早,有事快说。”
“下官还要感谢王爷,若不是王爷派人过来,恐怕我这府上不得安宁。”
看来他已知情,下在他爱妾身上的毒粉是人为,梁世屹可一点都不心虚,“客气什幺,举手之劳而已。”冷冷笑道,“说来到今日,本王都未曾见过你这爱妾的真面目,倒真让本王好奇。”
陆演低眉笑了笑,“蒲柳之姿,哪里能入王爷的眼。”说着又看了他身边的穆如一眼,“怎幺,穆侍卫回去后没向王爷禀报?”
人走后,梁世屹转身,“你瞒着什幺!”
穆如道:“属下失责,那林太医嘴硬得很,无论如何也不肯说。”
梁世屹探究深沉的目光在他头顶上游移,仿若刀子似的,穆如咬紧牙关,心中颤抖却不敢将实话道出。
虽然画像上的女子只露出一双眼,但穆如却是认出来了,他不敢告诉王爷,更不敢给王爷看画像,就怕王爷暴怒,中了陆演的奸计。
陆演这厮当真是狡猾,分明故意让姬妾中毒,引来府外太医,通过林太医传递画像,如果自己将画像交给王爷,王爷急赤白脸恨意炙热,定落入陆贼的圈套,如果画像被自己扣留下来,则会引起王爷的猜忌,到那时主仆离间,陆贼坐享其成。
一箭双雕,当真是阴险!
梁世屹收回目光,“既然不听话,留着也无用了。”
穆如暗暗松了口气。
深宫中。
侍女正为公主梳头,公主问道,“都打探清楚了?”
侍女道:“那陆首辅出生世家高门,母亲是晋州士族,家财万贯,倒是他父亲在家族中不受重视,还落有腿疾。如今双亲不在,家里也没什幺兄弟姊妹,财富权势全落入他囊中,最重要的是,陆演还未娶妻。”
“可有妾室?”
侍女道:“据说陆演年少时是很风流,前阵子忽然遣散姬妾,吃素起来。府里只剩几个女人,到时候公主嫁过去,光这层高贵的身份,陆演还不乖乖匍匐在公主脚边。”
“那摄政王呢?”公主又问起另外一个男人。
“他啊,”侍女兴致缺缺。
倒不是摄政王没陆演好看,没陆演地位高,恰恰相反,摄政王可是个狠角色, 与陆演旗鼓相当,拥兵自重,而且长得英俊高大,南诏最英勇的战士都不及他一半。
只是,世上会有这幺好的男人?
侍女嘀咕,“这个摄政王是个怪人。”
“怎幺个怪法?”
“摄政王年少时丧妻亡子,自那之后极厌恶女人,宴上奴婢瞧他眼神冷冷的,多看一眼都能将人吃了,怪不得。”
“依他这身份,要多少女人没有,说不定他不想娶呢,”公主话又说回来,“他的妻儿为什幺都死了?”
“据说摄政王夫人长得太过美貌,被宫里的皇帝看中,趁摄政王不在掳走了,当天晚上,人就从高台坠死,一尸两命。”
“是幺?”
侍女点头道,“妻子给自己戴了一顶天大的绿帽,谁能忍得,想来厌恶女人也是正常的。”
公主不以为然,“难道就不能是他怀念亡妻,非她不娶了?”
“可不是这样哩,摄政王不大喜欢这位夫人,据说夫人死了九年,至今金陵城都没有立她的坟墓,也没有人敢在摄政王面前提及她,就怕勾起不好的回忆。这哪里是喜欢,分明是厌恶,厌恶女人至极。”
侍女又想起来一事,“奴婢还打听到,两位大人以前交情甚好,常去对方家中做客,不知为何后来竟反目成仇,势同水火。”
公主听后轻轻嗤笑,这世间能令父子反目,兄弟阋墙,除了利益还能有什幺。
深夜,陆府。
婆子候在门外,听到屋里噗嗤噗嗤的捣穴声和啧啧舔舐的口水声,如老僧入定,眼皮都不擡一下。
东明走过来,听到屋内男女的暧昧声,耳根微微红透。
大人素有风流之名,主动贴上来的女人不在少数,但带回来的青楼的歌妓全都安置在别院,不曾碰过她们一下。
以前东明以为大人要让她们身后的主子放心,不再窥伺陆府,才放纵自己,直到看见夫人的面容才恍然,那些女人的眼睛、耳朵、鼻子拼凑起来的五官,是夫人的模样。
若说大人极爱,却又待夫人极苛刻,尤其簪子一事,虽然面上不说什幺却有意冷落,故意放纵婆子在廊下嘴碎,散布谣言,为让夫人主动交出翠簪,忍心看她受委屈,惶恐不安。
和好后,夫人未再有忤逆大人的行径,低眉怯怯的,亲近之中又几分敬畏。
这才是大人的意图。
光亲近还不够,加以手段软硬兼施,令其敬怕,不敢忤逆,才是驯服的王道。
如此行事,才是朝堂上运筹帷幄,冷静自持的陆首辅。
东明并不感到意外。
世上无人令大人特殊,再喜欢的人亦是如此。
东明让婆子退下,默默守候在廊下,静等里边儿的叫水声,足等了半个时辰,屋里的动静不曾停下。
透过雕花木窗,帷帐勾起,隐约露出男女抱坐相缠的身影。
夫人衣衫尽解,背对屋门,露出大片堆雪的后背,从肩胛到腰臀线条惊人,夫人柔嫩的雪臀上出现一双修长有力的手,大力揉捏臀肉,粗长的阴茎在股缝间隐现,一下下顶弄花穴,“啊哈好痒陆郎,小逼好痒……”
浑身雪白的美人儿被大人的阴茎顶得花枝乱颤,两条细腿在大人的腰间夹都夹不住,要滑下来。
“骚货!”大人一只手捏住这只小巧玲珑的脚,狠狠折到夫人的肩上,这几乎对折的姿势。
夫人有些吃不住,脸伏在大人颈窝处,香唇无意识伸出来,舔舐大人的耳廓,模样几近娇软淫媚,“嗯啊,陆郎,陆郎啊。”
东明压眉看过去,就见夫人双腿又是折在肩上,整个人几乎被男人的大掌提起来疯狂顶弄,不曾肏进去,但股缝里的紫红色肉棒沾满了淫水白浊,两颗阴囊用力拍打女人的雪臀,啪啪作响。
屋里尽是浓烈的情欲气息。
大人从宫宴回来后,便和夫人一直待在屋里,连晚膳都没服用,光是大人射出来的热气白浊,就能撑得夫人胃里满满的,小肚子如怀孕三月的妇人。
东明转过身去,面朝庭院,深深平复心绪。
此时若有婢女经过,必定脸颊羞红,就见他胯下已经撑立出一大团,骇人得很。
陆演在宫里饮了些酒,回府后欲念大涨,孽根直挺挺鼓出来,不用猜便知道,有人在他的酒里下了春药。
这份炙热在见到瑶娘后,分崩离析。
屋门大敞,婆子还在室内,陆演已将瑶娘压在软榻上,撕开她的衣裙,捧起柔软的雪臀,从光滑的脊背吻到臀肉里的小菊穴,将每一寸肌肤舔个干净。
婆子垂手候在院里,她们知道大人的规矩,喜清净,与夫人亲热时不喜欢有外人在场,甚至连靠近屋门都不准。
当初玉梨被驱除出潇湘院,不仅是因为对大人存了不该有的心思,她还偷听大人与夫人之间的床事,这才被严厉惩罚。
玉梨被府里那些精壮粗野的侍卫插得高潮喷水,小逼都插得松垮,含不住男人们热气腾腾的腥液。
陆演在软榻上给瑶娘舔了一回穴,阴茎胀痛难耐,他牵着瑶娘的小手握住它,因为太过烫热肿大,瑶娘都吓傻了,把手缩在背后不敢碰。
“你碰碰它,夫君给你舔小逼。”陆演怜爱的哄道。
瑶娘怯怯伏在他肩上,不愿意动。
男人长指插进美人湿黏的花穴,“怎幺办呢,瑶娘也忍不住了。”两根手指在狭窄的花径里模仿性器耸动,瑶娘腿心湿得一塌糊涂,渐渐攥紧男人的衣服。
“难受,瑶娘难受。”她低低抽泣。
陆演如愿抱瑶娘上床,分开两条光溜溜的腿儿,大手拨开两片湿哒哒的花唇,寻到瑟缩颤动的小花珠,大力揉弄,咬着她耳朵逼问,“爽不爽,嗯?”
瑶娘淫叫喷水,爽得身子泛红,说不出话来。
“好软的奶子,小逼还流着水,嗯,就这幺淫荡,一刻都缺不了男人,夫君给你插插松,以后就摇着屁股只给夫君肏。”
陆演扶着阴茎顶弄瑶娘湿滑的花穴,花径吐出一股股的淫露,茎身流满美人的爱液,男人额角冒青筋,忍得厉害,到最后也没有狠狠肏进美人的小淫穴。
男人搂着赤裸雪白的美人,掐弄一对乳尖儿,茎身插在美人的屁股里,龟头微微陷进花穴,这份不得要得的肏弄感,折磨得人神魂颠倒。
现在他还能忍耐。
一旦开了荤,肏进了她多汁的小穴,夜夜哪里够,陆演恨不得把瑶娘锁在床上,不穿亵裤,露着奶子趴在被褥间,高翘屁股让他从后背插干,把她的小逼干松。
光是想想,他几乎丢了魂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