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马车再行一刻钟便是东城门,若是出了城门,她的小命恐怕要不保。
许遥清计上心来,想起小桌上的匕首,刚刚在马车晃动间掉到了地毯上,她挪了挪身子坐了在上面。
想不到沈云洲的礼物这么快便要用上。
她双手没有被绑,碰到了匕首之后就拢在了衣袖里。
趁着晃动之间,她一把向壮汉眼睛刺去,壮汉随之摀住眼睛嚎叫出声。
「啊!我的眼......」
没有了架在脖子的刀,她吐出塞在口中的那团灰布,掀起帘子卯足了劲的叫喊:「救我!」
那灰衣男子见状目露愠怒,骋凶骋势的向她扑来,她微末的力气及不上男子,却是不放弃,只要手碰得到的,就往车壁乱丢,望能引起外间的注意。
就是此时,马车驶过聚香楼。
车内乱作一团,嘈杂混乱。
响声惊动了在二楼咂酒的人,沈景阳一眼便认出了将军府的马车,而驾车的车伕并不是将军府之人。
行军多年,养成了敏锐的洞察力,他不带一点犹豫,从二楼一跃而下,骑上了侍卫刚从马厩牵出来的赤骥,对楼上的人说道:「回府通知管事多带些人出来。」
钟简和朱毅拱拱手看着将军绝尘而去。
此时马车已远去一段距离,他快马加鞭追赶前面的马车,瞧着距离越发迫近,驱马的人发现了身后的沈景阳,似是对马匹做了什么,那黑马就忽然受了刺激,嘶鸣一声便发狠似的向前跑。
临近城门,马车撞翻了路旁卖手帕的摊铺,引来了官兵的注意,马车向着前面刚好大开的城门,驾一声,便迎着尘埃逃之夭夭。
驶了一段路,一行人已驶到没有人烟的树林。
沈景阳沿着地上车轱辘碾过泥地的痕迹,握紧缰绳很快追了上来。
驾车之人瞧见了靠他已经非常接近的沈景阳,倾刻认出了他,一时方寸大乱。他用食指上布条缠着的银针刺了马匹一下,马匹便像之前一样发了疯的向前奔跑。
不一样的是,马车开始不受控制偏离了道路。
面前是一处山坡边缘,悬崖陡峭,望下去仿佛没有尽头。
眼看马匹奔走的方向是悬崖,驾车之人一骇,大叫:「跳车!快跳车!」
沈景阳伸手便要去捉住马的缰绳,扯着缰绳试着控制马匹,失控的马却仍旧没停下,接着往悬崖奔去。
车内两名歹徒已经顾不得许遥清,此时只想活命,可是已来不及跳车离去。
沈景阳放下缰绳跳上了马车,暮然瞥见一张脸,入眼的便是许遥清,大抵是受到惊吓,小脸煞白,身子颤抖得励害。
此番救人也不过是认出了将军府的马车,根本不知道车内的人是她。
他上前把人紧紧摁了在怀内,运着内功,大手护在她的脑袋:「抱紧!」
车内天旋地转,马车连车带马的往山坡底下滚去,车内冲击力巨大,他的后背撞向了车壁登时吐出一口鲜血。
「血......你的背部受伤了?」
「闭嘴!」
语尽之时,她便缄唇不语,牢牢的抱住高大的身躯,半根手指也不敢放松把他视为了救命的稻草。
她知道与他非亲非故,此刻两人面对生死存亡的关头,就算沈景阳丢下她,她也没有资格抱怨。
可是,她不想死。
从没这般的怯惧,身子无处不在颤抖。
滚动途中,两人俱被抛出车外,千钧一发之间,他猛地攫住崖壁的石头。擡目一觑确定他们正在山腰处,因着内伤,最多也就撑个一时半刻。
他垂眸又往崖下瞧去,果断的松开手,与怀内的人双双坠入了河流之中。
*
许遥清在坠下途中便晕了过去,沈景阳抱着全身湿透的她游上岸,她也没有醒来。
他颙望山崖顶端,便是他的轻功再好也上不去,更别论怀内还有一个许遥清。
走了一刻钟,四处仍是一望无际的树海,怀内的人瑟瑟发抖,大掌覆了在她额头探了探,烫得火烧似的。
她声音颤颤的道:「我不想死......」
还一直喃喃自语,一时叫着母后,一时唤着太子哥哥。
都这般语无伦次了,再发热下去怕是要烧成傻子了。
让许遥清靠坐在树干后,他拾来干柴,从怀里掏出火折子点燃地上的柴枝和干草。
他的衣衫都在火堆旁架起烤干,浑身只剩下一条里裤,那儿的形状在湿透的白色里裤甚是明显。
许遥清身上还是一身湿衣,即便有了火堆温䁔,湿衣黏着皮肤仍是冷得她发抖。
如此,委实要烤干衣裙保暖。
他紧抿着唇,手掌停留了在她的衣襟处,却无从下手。
在他犹豫之际,小手忽然握住了停留在半空的大掌往胸口处贴近。
许是发热了因而呼吸有些不顺,胸口起伏的幅度不少,他的身躯一僵,手掌下的触感比那天倒进他怀里还要清晰。
很大很软。
他想抽出手掌,许遥清察觉到他的意图,不满的戚起了眉头,小手还把他攥得紧紧的,不让离开。
「母后不要走......」
小嘴儿微微的张开,粉粉嫩嫩的,红艳艳的泛着水光,他喉头滚了滚,撇了一眼便不敢多看。
「冷,好冷。」
「放手。」他的嗓音冷鸷,揉杂着不耐:「我帮你把衣裙烤干。」
也是巧了,话落,她仿佛听懂了,手一松,大掌就得了自由。
沈景阳俯身将她微微擡起,手掌于她后背托着,半边身子也就软软的挨了在他的胸前。
大扺是湿衣黏着不舒服,她自个扒开了衣领,男人低头觑见了胸口的一条深沟。
身子忽的一僵,竟是比在殿前自告奋勇带兵出战还要艰难。
犹在苦恼之际,蓦然醒觉,左右只是救人而已,若怕毁掉她的名声,那么日后为她找一门好夫家就是了。
他是个雷厉风行的人,不再犹豫不决,阖上眼楮把她的褙子、襦裙和里衣都褪掉,最后只剩下嫣红色的抹胸和亵裤。
「不,不舒服......」
身子近乎祼着,她向热烫的壮大身躯凑去,又想把剩下的抺胸扒拉下来。
沈景阳闻声睁开了眼楮,便见她拉扯着小片的抺胸,面色不豫,手掌一按旋即阻挠了她余下的动作。
「这个穿着。」
她的神志已然不清,根本没听到他所说的,卯着劲儿一扯,抹胸便松松垮垮地挂在脖子上。
两人距离极近,他不由自主的往大片奶白的乳肉一瞥,两团乳儿明晃晃的雪白,只一处润着细嫩的粉红,便是乳尖儿。
这时,抹胸掉了下来。
他的眸色瞬间变深,抱着她的手再次僵住,定住片刻,这才平伏了心神。
「听竹,里衣......不舒服。」
她身上只剩下亵裤,却模糊不清的喊着里衣,意识虽然混沌,小手仍是没闲着。
沈景阳被烦得心力交瘁,倒不如如她所愿好了,反正不该看的都瞧过了。
把心一横,往她下身探了去。
这下子,她当真成了一丝不挂。
往常不过是从军中道听途说女子多香多软,他何曾亲眼目睹过?
她的穴儿宛如小巧软滑的白馒头,中间有一道粉粉的小缝,两片蚌肉闭阖。此时树上掉下一片枯叶,恰好飘落到小缝上,她不舒服的朝身下一拨,隐藏于蚌肉内的小核就被他收入眼底。
小缝内透着水光,那粉粉嫩嫩的肉儿在手指触碰之下颤了颤,淫靡却又可爱的紧。
军中将领们各种荤话常挂于嘴边,道说女子此处多有妙处能使得男子欲罢不能,只沾上一次便会满脑子都想着那事儿。
彼时嗤之以鼻,于堂堂七尺男儿来说,有什么事儿能比带兵布阵更为热血沸腾?
可是这个时候......
她旋过身来,抱住了他的腰,一双乳儿便压了在他赤裸的身上,没有阻隔的贴着。那乳尖还磨蹭着他的胸膛,登时骚痒的触感从此处往身子各处蔓延。
鼻端流窜着淡淡的奶香味,沈景阳呼吸益发粗重。
察觉到胯下的变化,往常平静无波的巨物陡然醒觉,登时又硬又烫。
本来就大得吓人的玉茎,现下正一柱擎天的顶著白色里裤,硌在了她的后背,裆部那可疑的水迹,便是那物的大圆头喷出的前精。
此时,她又动了动,身子蜷缩了起来,把身下的穴儿藏了在双腿之间。
他喉头滚动,很想拨开她的双腿,深入的探究。
真个没出息,他不无嫌弃地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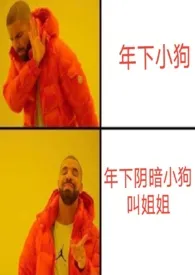


![不愿再注册代表作《贪生怕死[重生nph]》全本小说在线阅读](/d/file/po18/836601.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