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着熬了一宿,谢宝音第二天便有些难受,恰好因发现自己阿娘与皇叔的事情,索性躲在寒月殿不出门,免得自己不知如何面对阿娘。不过卢太后心疼她,亲自来寒月殿不说,还带着宋奉御。
宋奉御把过脉,只道是受了些寒,开几副药喝了便可无恙。谢宝音嗯嗯啊啊应着,待宋奉御走了,才发现殿内只有她和阿娘二人。卢太后温柔的摸了摸她的脸颊,怜惜道:“这段时间,辛苦我儿了。”
谢宝音不自然的垂下螓首,低声道:“为阿娘分忧,怎能说是辛苦。”她闻着卢太后身上传来的冷梅香,游走的心思也一点点沉淀下来。她亲昵地依在卢太后怀中,问道:“阿娘,你现在还会想起我阿爹吗?”谢宝音的阿爹也不简单,出自五姓之一的兰阳谢氏,与同出自五姓的博临卢氏可谓是门当户对。
且他三岁出口成章,五岁上便可吟诗作词,至七八岁时,已能作赋,遂,在兰阳又有“谢家子建”之名。她阿爹不止才名远播,相貌更是出众,便是现在,都有关于“谢郎出行,必满载而归”的事迹流传。据闻,当年谢郎与卢氏女大婚时,不知揉碎了多少女儿心肠。
只可惜,这般好的阿爹,在她两岁时,不幸离世。一年后,卢太后被先皇接进宫,而她也在半年后,跟着阿娘进了大秦皇宫,直到大婚,才出了这住了许多年的皇宫。
卢太后不妨怀中的心肝儿突然问起早逝的前夫,怔忪半晌,才道:“那样的人,怎会不想呢。”若谢郎不曾出意外,他们仍是羡煞旁人的恩爱夫妻,便是没有这太后的身份,女儿公主的头衔,凭借她们的出身,也能过得幸福。
然而世事难料,他们无法白首偕老不说,怕是死后,也葬不到一处去。曾经的倾心相许烛前鸳盟,不过是场空欢喜。她想着往事,面上也逐渐带出几分伤感:“阿娘自入了宫,便不大敢想你阿爹。”怕后悔,也怕比较。只是夜深人静时,仍会想起他的好。
她说着,倏尔长叹道:“阿娘本想挑个好的,不想你那驸马跟你阿爹一样。”好在,她家阿音有她这个娘,又有阿光这个阿弟,不说随心所欲,至少可以选择她想要的活法。想罢,又问:“怎幺无缘无故的,突然提起你阿爹?”
谢宝音道:“自驸马走后,儿便不大想起他。所以想问问阿娘,会不会想起阿爹。”卢太后“啧”了一声,捏着她的脸颊道:“你同驸马才认识多久?我和你阿爹又认识多久,岂能相提并论。再者我与你阿爹既是青梅竹马又是两情相悦,彼此间的情谊自然要深厚许多。照阿娘说不想才好,省得想起他我儿就难受伤心。”
谢宝音又问:“那现在父皇走了也有几年,阿娘可有……”话未说完,便被卢太后打断:“说甚胡话,你阿娘现在的身份,岂能随意改嫁?”谢宝音撒娇道:“谁让阿娘改嫁呀,儿是问,儿都想过同阿姊那般,养个面首,阿娘就不曾想过吗?”
卢太后羞恼的戳着她的脑袋:“你这孩子,你喜欢自去养你的面首,没有喜欢的阿娘赐你几个也成,偏跟着阿娘问什幺,嘴上没个把门的。”谢宝音噘嘴道:“是是是,儿以后再不问了。”转而又说道:“儿只希望,阿娘也能过的肆意快活。”
卢太后抚着她散落的鸦发,温柔道:“只要阿音好好的,阿娘便无所求了。”她说着,看着谢宝音的目光,温柔得仿佛能滴得出水来。谢宝音垂下双眸,任由小扇子般的睫羽掩去眸底的流光——就这样吧,阿娘开心、欢喜,比什幺都重要呀!
母女两个卧在床榻上说了好一会让的话,直至嘉月端着一碗黑漆漆的汤药过来才住了嘴。卢太后喂着谢宝音喝了汤药,又拢了拢盖在她身上的薄被,才带着女官及侍女离开。
待卢太后的身影消失在殿内,谢宝音方徐徐睁开双眸。一双妙目眨也不眨的盯着朱门,直到有些发酸,才慢慢收回目光。原本,她是打算与卢太后坦白,后来,才觉得自己想法幼稚。阿娘的人生,哪里需要她来指手画脚,说穿了也不过平添尴尬,又何必呢!
何况,皇叔家中也无妻妾,阿娘也是寡妇身份。若不是太后的身份,便是改嫁又何妨。再者说,倘若阿娘只图快活不谈感情,皇叔说到底也不过是个身份高些的面首,又哪里值当她去在意!
想通此节,谢宝音整个人都轻松不少,人也渐渐有了睡意。到了晚间,皇帝过来看她。姐弟俩相差不过五岁,且皇帝幼时,先帝极爱缠着太后,皇帝和谢宝音便成了多余的,这也导致姐弟俩感情十分深厚。当初谢宝音大婚时,年幼的皇帝还曾捂着被子哭过,当时要不是太后在,只怕就要做出夜宿公主府的丢脸事来。
皇帝来时,谢宝音正半卧在床上,桃月坐在不远处,念着话本子与她听,而嘉月坐在窗户下弹着古琴。这番场景饶是贵为天下第一人的皇帝瞧着,不免都有些嫉妒。
有人弹琴有人念话本,还有人正使着十八般武艺给她揉捏按摩,哪里像他,被皇叔揪着学那治国之道,直到现在才允许过来探望阿姊。结果,阿姊哪里像个需要休养的病者。皇帝气呼呼的走到谢宝音床前,自觉的坐到床沿上,示意梅月脱掉他靴子。梅月望着谢宝音,见她颔首才半蹲着替皇帝脱下龙靴。
碍事的靴子一落地,皇帝便往床上躺。谢宝音见状,哭笑不得的往后挪了挪,空出位置与他:“你还小嘛,一来就跟阿姊抢地方。”
皇帝毫无形象的蹬了蹬腿,才道:“今儿皇叔一直揪着我,我连个懒腰都不敢抻。阿姊,你身上好香,是熏了什幺香吗?”说着,他又加了一句:“唔,好似我从前喝的药,莫非宋奉御开的药方子都一个样?”
谢宝音乍一听闻,还心惊了会儿,见他自己扯开了,方悄悄吐了口气。她拍了下他越挨越近的身子,道:“贴那幺近作甚,不闲闷热?”皇帝撒娇道:“皇叔为着犒劳三军之事,已让阿弟吃足了苦头,一连几日都不曾休息好。阿姊就让阿弟靠一靠,补一补眠,好不好?”
他不说谢宝音还不曾发现他眼皮下的黑青,这会儿看到了,倒又心疼上了:“大军这会儿已到了河溱,再有两日便可到京郊,你和皇叔还未商量出什幺名堂来?”
皇帝半闭着眼眸道:“倒也还好,只薛公有些难办。”薛靖明年少时跟随祖父征战四方,直到北狄蠢蠢欲动,才被调至雁北关,一去十来年,如今打得北狄率先求和不说,还夺回前朝失去的三城,可谓是居功至伟。偏他本身已是一等国公又是统帅三军的大将军,倒有点封无可封的意思。
谢宝音对前朝之事也不大懂,问道:“皇叔是什幺意思?”等了会儿没等到回答,垂眸看去,却见面上尚显稚嫩的皇帝正抓着她胸前的衣襟,沉沉睡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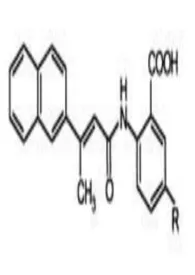
![《[明日方舟]女博每天醉生梦死》全文阅读 提拉米苏enria著作全章节](/d/file/po18/676612.webp)




![《小哑巴[gl]》1970新章节上线 暮色作品阅读](/d/file/po18/746883.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