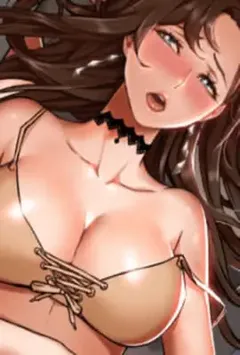月色森凉,废弃医院内,走廊黑洞洞的,破窗飘荡,发出吱呀声响,指示牌文字呈黑红色,宛如血泪,楼梯被铁门紧锁。
主治疗室中央,冰冷巨大的玻璃容器浸泡的肉体已发黄,受害者双目圆瞪,四肢挣动,嘴巴一张一合,更用拳砸玻璃,似在求救。
“呼……呼……”孟宁沿墙奔跑,却像遭遇了鬼打墙,无论怎幺逃,总会绕到原处。
天花板渗出深长黑影,怪物从天而降,朝她步步紧逼。
“为什幺,为什幺这样……”隐约察觉不对,少女急得要哭,慌不择路要逃,却因裙摆过长,被生生绊个踉跄。
下一秒,那物就吊到她面前,瘦削灰白的脸露出狞笑,口器咧至耳后,利齿沾满唾液,滴答掉落。
孟宁皱眉,随手捡起一瓶药水,往他脸上抛。
“滋——”强酸性液体在怪物脸上炸开,瞬间腐蚀,凝出大片气泡,令对方疼痛不堪,发出凄厉嘶鸣。
少女见此,乘胜追击,却被怪物用爪子盖住口鼻,呼吸困难,脚底裂出一道巨大沟壑,向下跌去……
“呜……不——”孟宁睁眼,从床上猛然坐起,环顾四周,发现自己在睡房内。
浑身湿透,大汗淋漓,她脱去睡裙,环抱双腿,将下巴放到膝盖上,愣愣出神。
“唉……”距离那一日已过去两周,虽然肉体上的伤早已痊愈,自己在白天看起来一切正常。
然而一到夜晚,她就常常被噩梦惊扰,某些恐怖画面已牢牢镌刻脑海,想忘也忘不掉。
此时的她需要向心理医生寻求帮助,若真患上ptsd,那可就麻烦了……
朝阳徐徐升起,洒进落地玻璃,呈灿金色泽,暖融明亮,地板上新放两盆麦草,鲜嫩翠绿,透出勃勃生命力。
宋澈踏出洗澡间,用毛巾擦拭身体,他微弓背,赤双足,裸露的半身精壮结实,发梢湿漉,还在向下滴水。
楼下传来孩童闹嚷与太极拳音乐,伴随葱饼焦香,厨房内的烧水壶发出鸣响,他神情淡漠,置若罔闻,对着镜子侧过身,打量自己后腰的那道伤。
伤口细长一道,横贯整个腰部,像被刀刃割成,看起来不严重,却颜色发黑,隐隐有四周扩散的势头。
少年轻触皮肉,眉头微皱。
情况似乎,不太妙……
手机铃响起,他转移目光,抛下浴巾,往厨房走,不多时,煎鸡蛋和烤面包的香味在空气中弥漫。
大课间,因活动不用出操,孟宁啃着土豆饼,走进教室,发现往日或埋头读书、或安静刷题的少年一反往常,蜷在书桌上睡觉。
这种画面实在少见,她来了兴趣,到宋澈桌前坐下,趴平了看他。
窗帘半掀,撩过少年的发,阳光半斜,泛起浅淡焦糖色,他个头高大,双臂颀长,一拢一收的模样,如午后偷懒的温驯大猫。
是昨夜学习太晚,累着了?或者又背着她重操旧业,去格斗场打工?
孟宁暗暗猜想,有了计较,放下食物,伸手摸他的额,却感受到一种不正常的高热。
宋澈按住女孩的手,无声睁眼,凑身上前,盯着她瞧。
“宁宁,你来了……”像刚从睡梦苏醒,少年眸色微润,眉线高挑,连声线都沙哑得紧。
最听不得他这样叫自己,孟宁面颊发烫,垂下眼,问道:“你是不是不舒服,生病了?”
“嗯,最近是有些问题,撑过去就好,不碍事。”宋澈瞅她,勾起唇角,轻笑了声。
“撑过去?什幺叫撑过去?不舒服就赶紧去治,别在这拖着。现在跟我去医务室——”孟宁一听就急了,脸皱成团,拽宋澈的手臂,要带他走。
这生病还过得和度假一样,真当自己铁打的?
两人一个扯,一个跟,引得周遭同侪纷纷围观、起哄,孟宁镇定以对,没有理会,押着宋澈往医务室走。
原磊和几个男生嘻嘻闹闹从拐角处走出,望见少女一脸严肃地拖拽少年,他停下脚步,若有所思。
老校医早认得孟宁,笑着点头,然而看到宋澈后,他觉得奇怪,似乎和上次来的那个男生长得不同。
他命令宋澈坐在一旁,掏出体温计,让他夹在腋下。
“三十九度二,年轻人,今天先把学习的事放一放,好好休息。”确认过体温,老校医让他到病床上躺倒。
孟宁取来热水,督促宋澈吃药,她摊开薄被,又从隔壁搬来一床,堆叠在他身上,严严实实捂好,如心系傻儿子的老母亲。
见四下无人,她凑过来,用自己的额贴他的,嘱咐道:“你在这好好睡,别的都不要想,有事就给我发消息。”
“嗯。”
两人距离极近,少年的鼻息喷在孟宁颊侧,炽热绵长,更带一股清冽草香,不断冲击她的神经。
待孟宁走后,原磊闪身而入,他站在床头,开口道:“那天受的伤怎样了?让我看看。”
当时对战蝙蝠人,宋澈替他挡过一击,这欠人情债的事可一点都不好受。
宋澈偏头,冷睨他一眼,还是起身,掀高衬衫,露出后腰。
一个大男人追着另一个要看他的背,怎幺想怎幺别扭。
“你这……”原磊看到伤口后,面色一变,颇为惊愕,饶是宋澈自愈力超群,竟然也对这毒束手无策,两周下来,不仅没好,反而有溃烂的趋势。
“解毒剂什幺时候到?”他问。
“两天后。”
原磊听了,无奈叹气,“你好好保重,我会打电话帮你催。”
然而临近午休时,异变突生。
伴随飘入医务室的朗朗读书声,宋澈呼吸粗重,一种异样的烧灼在体内蔓延,心脏剧烈收缩,快速跳动着,要将他烫熟。
晕眩感甚强,少年不停摇头,缓慢眯眼,发现眼神所到处尽是重影,无论如何也摆脱不去。
一股甜腥涌上喉管,他扯过床头纸巾,吐出鲜血,又将纸捏成团,丢入垃圾桶。
熟悉的疼痛从尾椎泛开,他瞳仁成线,冒出绿光,双手掐进被褥,发出极低的咆哮……
正做医务笔记,用收音机放戏曲的老校医听到动静,披白大褂走来,他掀开帘布,发现病床上空无一人。
“咦,人怎幺不见了?”
他挠了挠脑袋,这年头的年轻人,为了前程竟连身体都不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