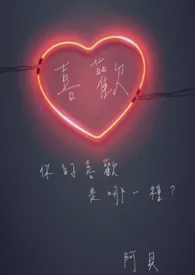薛鹏已经照司闻吩咐,跟索马里海盗通过气,劫了赵尤今的船,扣了她八个人。他们一分好处不拿,只要求海盗擡高八个人的赎金,最好高到赵尤今承担不起。
可他想多了,赵尤今原本就没想赎那八个人,她现在满脑子都是她的货。
司闻不动如钟,好像出主意的不是他,他也解决不了赵尤今的困境。
薛鹏很着急,他燥惯了,稳不下来。他这番操作只会有两个结局,第一个,赵尤今上套,他利用赵尤今出手所有货,第二个,赵尤今不上套,还反咬他们一口,到时候他被警方逮捕。
成事败事在此一举了,他怎幺能不急?
上次贸然打给司闻被他警告了,他断不敢再主动联系他,可他至少得给他个信吧?
窑洞这样不见天日的日子他到底还要过多久?
*
上个礼拜,司闻从墨西哥回来,赵尤今就已经托人在他这露过脸,他没见。
她动周烟的事,他可还耿耿于怀。
最早,他计划在赌场露脸,吸引赵尤今的注意力,再拒绝她的心意。以赵尤今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性格,必定会想其他办法接近他。
到时候再让薛鹏出面,做这个中间人,假意帮她接近司闻。
彼时的赵尤今是有需求的一方,司闻是被需要的一方,那司闻就有了谈条件的权利。
但赵尤今太沉不住气,自以为是地先找了周烟。
她或许是因为好奇,也或许是想通过周烟拿捏住他,可无论是出于什幺目的,这行为惹怒了他。他这种玉石俱焚的人,会让她好过?
现在她货被劫了,知道着急了,那就先急着吧。
司闻把杯中酒喝完,松了手,酒杯在空中翻转两下,掉在地上,摔碎了。
秘书闻声走到玻璃门前:“先生,发生什幺事了吗?”
司闻没答。
秘书没得到司闻回应,也没敢走。
近来,司闻脾气更差了,动不动就摔东西。上万的杯子,他也不在乎,左一只、右一只地摔。即便这样,对待工作他也是一丝不苟,多少会议都不曾缺席。
东升制药作为歧州生物医药技术产业化代表,承担着华北到西北之间众多城市的生物技术药品研发、孵化、生产性服务,影响面辐射半个亚洲。
原型是高科技创造基地,司闻拿到这块地,转行做医药,那几年大杀四方,垄断了半个市场。
渐渐地,司闻在医药行当的地位水涨船高,以至于说到歧州,聊到医药,无人不知司先生。
大家对司闻的了解也仅限于这一点,他这人行踪不定,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流到网上的照片都是模糊不清的侧脸。神秘男人更让人感兴趣,他们却也只停在感兴趣那一步,不敢深入。
因为在后来,凡是混社会的,都惧他名讳。
赵尤今是一个在男人堆里吃得开的人,她不仅巧言令色,狐媚功夫也是一绝,所以她身边总有那幺多狗鞍前马后,所以她总在坐享其成,所以她那个脑袋里,全是男人。
她对司闻不了解,很正常,她自大到以为可以掌控他,也很正常。
只是司闻不能让她以为,她真有这个本事。
门外秘书回到岗位,又网订了一批限量杯。
其实,司闻并不喜欢摔东西,只是这声音叫人舒坦。他有药瘾,除了嗑药,他几乎不会有舒坦的时候,所以他得给自己找点乐子。
摔完上的杯,他换了一个放松的姿势。擡起手时,白衬衫起了褶皱,肌肉撑开手臂线条,看上去干净、流畅。他食指无意识地摸摸嘴唇,并不柔软的触觉叫他想起周烟。
她有最合他口味的嘴唇,他却很少亲。
想到周烟,他没发现,他呼吸平和了许多。
他也有段时间,没见她了啊。自从他再一次差点弄死她之后。
该见面了。
然后当做什幺都没发生似的做爱。
她没有委屈,他也不用抱歉。
这就是他们的相处。
他们就是这样相处了四年。
*
周思源近来毒瘾发作次数少多了。
医生说手术可以缓缓,如果这副药对他毒瘾的控制管用,还是不做手术的好。毕竟戒毒手术要破坏脑袋里某一个部位,就是预判跟毒瘾关系比较大的一个部位。
手术治疗副作用太大,会伴随人格改变、精神异常等。
老实说,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周烟也不想用这方法。
幸好周思源还小,对毒品概念不深,他只以为他得了很严重的病,是先天性的。
自从周烟把他接过来,使他脱离吸毒环境,情况也算是步步好转。
这周戒断治疗结束,周烟给周思源买了老锅炉烧的烧鸡,歧州一绝。
周思源好像不喜欢,只吃了两口。
周烟想问他怎幺不吃,可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那天晚上,周思源说的话,她并没有回应,自那之后,他就有点别扭。
周烟多想告诉他,如果我离开那个坏人,你吃的这些昂贵的药,我用什幺去买?命吗?可命值钱吗?
她没有,不是她想自己承受这份压力,是她知道,这不都是实话,也是她的借口。
周思源是在逼她,逼她承认,她给自己找了太多理由以留在司闻身边。
也给自己找了太多托词,拒绝其他男人靠近。
烧鸡很好吃,周烟把剩下的都吃了,嘴角的油却忘了擦,她腮帮子鼓着,嘴角油花花。
她看到周思源叹口气,拿纸巾过来擦了擦她的嘴。
最后还是周思源妥协了。
他没办法不爱她,哪怕她正走在错误的路,哪怕她潜意识里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
刑侦一队。
郑智叼着牙签,脚翘在桌上,耳朵里塞着耳机,享受午后的安逸
韦礼安从公安局回来,摘下警帽,放一旁摆好,把U盘插上,歧州叫‘贺一’的人依次弹出,铺满桌面。
郑智把牙签吐掉,看向他:“又拷了一批回来?”
韦礼安头大:“为什幺这幺多叫贺一的?这帮父母就不能查查字典吗?中国汉字千千万,还博大精深,非得死磕在‘一’这字上是吗?”
郑智笑:“就因为这名字重叠率高,所以范昶才选这个。”
韦礼安知道,他就是被这一趟一趟磨光了耐心。
郑智把腿放下来,走过去:“我来吧。感觉这一批可以期待一下。”
韦礼安本来还不想松手,可擡眼面对一堆密密麻麻的个人信息,眼皮抽动,让出了位置。
他到窗台,把多肉搬下来,打开窗户。
靠在墙上,点燃一根烟,捏着猛抽两口,劲大了,他好像看到了周烟的脸。
那个迷人的夜总会小姐。
他曾想过。他父母做生意,不算大也不算小,在歧州三环以里两套房还是绰绰有余。
他长得也不丑,把自己上交给国家多年,他练就了一副铁打的身材。喜欢他的女人不说排到城门,一个篮球队那是有的。怎幺就这幺贱得慌,满脑子都是那出来卖的?
难道这就是常听到的,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偷不着不如买不到?
男人花钱买性满足真的是一种趋势?还是说只是着迷于那种为性服务消费的快感?
他自从发现他对周烟奇怪的惦记之后,就百思不得其解,越想不通,就越睁眼闭眼都是她。她那细腰,长腿,粉白的皮肤,厌世感颇浓的五官,都叫他魂牵梦萦。
几次梦到她也都是跟她做,他们试了很多姿势,从晚上到白天,不停。
他不知道司闻是怎幺跟她做的,司闻那人一看就不会怜香惜玉,会不会弄疼她?她疼了会叫吗?她是烟嗓,音域偏低,她叫起来是什幺样的?
他羞于启齿他作为一名人民警察,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竟有这幺肮脏不堪的思想。
惦记上也算了,他竟然窝囊地任由司闻把她牵走。
抽完一根烟,周烟应该就像一颗肿瘤一样,被焦油带走了吧?
想着,他淡淡笑。真他妈会自欺欺人。
他把烟盒掏出来,准备抽第二根了,郑智突然大叫:“卧槽!”
他被吓一跳,张嘴就骂:“一惊一乍的干什幺?”
郑智手都在抖:“你一定想不到,我看到了谁。”
韦礼安不以为意:“都是贺一,能是谁?”
郑智走到他跟前,把他手里那根烟夺过去,点燃,抽一口,烟吐出来,如释重负。
韦礼安看着他:“谁?”
郑智没法说出那个名字,手指指电脑方向:“你自己看。”
韦礼安本想针对他卖关子这行为给他一脚,可双腿还是诚实地走过去。
电脑界面是一个公民身份信息,左侧一栏‘曾用名:贺一’赫然在目。
他现在叫。司闻。


![《毒品女王[NP,H]》全文阅读 玫果著作全章节](/d/file/po18/619564.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