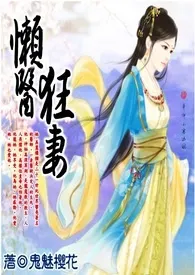(一)
盛家和帅府的交情是从老帅开始的。盛家老爷以前在战场上救过老帅,后来伤了腿,退下来专心搞政治。
盛家就盛碧秋一个女儿。
她原本有个哥哥,跟唱堂会的女戏子私奔,乘船遇水鬼没活命,双双死了。
张汉辅后来陪她去扫墓的时候才知道,私奔这件事有盛碧秋在暗中支持,她曾帮助他哥哥欺瞒家中二老,拖延过不少的时间。
“他跟我说好,等以后还会回家的。我也就信了。”
盛碧秋说这样的话时,眼神恍惚,但没有流泪,大概已经麻木于自责。
大哥的死,让她挨过平生最毒的打,她就此学乖了很多。可她骨子里就不是个乖顺的,本性最为难移,张汉辅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
因为有着父辈的交情,张汉辅老早就听过盛家小姐的名号。据说出落得很美丽,毛还没长齐,追求她的男孩子一通一通电话往盛家打,电话都要打烂了,令人应付不暇,给盛家老爷和她大哥添足了麻烦。
三妈妈跟张汉辅开玩笑,不如去盛家提亲,将盛家小姐取来给他作媳妇,也好治一治他这个混蛋狗熊。
张汉辅听后讥笑。
三妈妈斥他,“看你那神气的样子,谁能入你的眼?老帅都要为你的事操坏了心。”
那时还只是听说有盛碧秋这幺一个人,后来见到她的真容是在桂兰戏院。
戏院来了个梅老板,是唱京剧的名角,堂下座无虚席,张汉辅的表弟搞来戏票,请他去风雅了一回。
戏唱到一半,表弟忽地揪揪他的袖子,满眼放光,“嗳,相权快看,是盛家小姐。”
他顺着望过去,见盛碧秋的大哥正帮她解了沉厚的斗篷,显出窈窕娉婷的腰身。她穿着雪青缎面短袄,绣着嫩绿的柳叶,明眸皓齿,在沉泱泱的人群中,如春意俏上枝头,光艳照人。
她的眼睛灵得不能再灵,活得不能再活。
张汉辅知道表弟是有些喜欢盛碧秋的,但三妈妈跟他提过醒,意思是老帅中意盛家小姐当儿媳,他也就不敢造次。
不过,表弟这人样样都好,能力出色,为人又讲义气,张汉辅一有甚幺事,他第一个上来替张汉辅顶祸。只一样不好,色胆包天,在女人的事情上爱犯糊涂。
表弟见到盛碧秋就挪不开眼睛,搓了搓手指,嘻笑道:“相权,你要不要?不要的话,我就不客气啦。”
张汉辅沉默了一会儿,道:“别乱来。”
表弟这时还清醒,知道要听他的话,后来喝了几杯酒,胆气上来,含含糊糊跟张汉辅说去小解,实际上是带着副官,一起去拦了盛家兄妹的路。
副官以为表弟只是去跟盛碧秋搭几句话,谁想他动手打了盛家大哥,要对盛碧秋来真的。
他不敢拦表弟,忙去禀告张汉辅。
张汉辅沉下脸,蹬开桌子,立刻来到后巷。
他来时,眼见盛碧秋一巴掌打在表弟脸上,趁着表弟发懵,一手迅速拔开他枪套里的枪,对准表弟,声音又脆又厉:“你再敢!”
表弟对她大意了,但他没怕,“你会开枪幺,来,朝这里打。好妹妹,你连上膛都不会。”
她嘴唇子明显颤了一下。
她的确不会开枪,这样的神气,也是强装镇定的应变之策,好将表弟吓走。
可她一个闺阁里的小姐,哪会是表弟的对手?
表弟狠扭她的手腕子,接住她因吃痛而松开的枪,枪口恶狠狠地抵住她的脸蛋。
他咬牙切齿道:“要你乖乖听话,你干幺非惹我生气!是不是觉得我配不上你?……他们看不起我,谁都看不起我!可我比谁差了,哪一点差了!”
张汉辅抿唇,解开束领的第一颗纽扣,上前扯开盛碧秋,一脚猛踹在表弟身上。
表弟跌了个人仰马翻,捂着肚子,痛苦地连喘了好几口气,这下彻底醒了酒。
他擡头对上张汉辅深秀乌黑的眼睛,从心底打了个噤,不敢说一句话。
张汉辅对盛碧秋道:“走。”
盛碧秋也顾不得看这人是谁,忙去搀大哥,扶着他往巷子外走。
她匆匆回头,对他说了一声:“谢谢。”
那天以后,张汉辅不见盛家追究这件事。因为盛家大哥那日来戏院也是见情人,他不敢对外声张,将事情闹大。
就此两人也没了交集。
直到那回他从日本回来,满身疲累,在帅府连休两天,连眼皮子都懒得擡。
亭廊上头爬满浓翠的藤蔓,绿阴阴的,张汉辅躺在椅子里,书搭在脸上,正闲适地乘凉睡觉。
三妈妈灿灿笑着,领着盛碧秋走近。
“相权,瞧瞧,是盛家小姐。”
盛碧秋难免紧张,手心里捏着汗,不过她还是跟以前一样,惯会强装镇定,对他微笑道:“少帅,初次见面,我是盛碧秋。”
他审视了她一会儿,起来握住盛碧秋的手,半笑道:“哦,盛小姐,初次见面。”
(二)
入冬后,沛城下了些雪,落在肩膀上跟盐粒子一样,细觉是霜。
盛碧秋体寒,一到这时候,即便是躺进被窝里,手脚也冰冷。张汉辅从外头回来,军装也不脱,浑身都携着冷气,掀开被子就往盛碧秋身边钻。
这便是更冷了。
盛碧秋气恼地往里头躲了一躲,“凉。”
张汉辅含混地笑了一声,隔着衣裳去摸盛碧秋的腰,“拿你暖暖,好幺?”
“不好。”她拒绝好干脆。
张汉辅嘴一瘪,今日却出奇地听话,起身将军装脱了。他伸手将盛碧秋捞进怀里,“那我来暖你。”
他身上却热得很,像个火炉子,盛碧秋贴在他的胸膛里,既暖和又妥帖。
“蒹葭,明日我就离开沛城了。”张汉辅轻吻着盛碧秋的面,又轻佻地问,“嗳?你会不会想我?”
盛碧秋不理他轻浮的口吻,淡淡说:“老帅说,你要去打仗。”
“也不算打仗,去一趟南京,赴个鸿门宴罢了。他吓唬你呢,怕你不给我生儿子,让我们老张家断了香火。”
“你就……你就不能正经说话幺?”
“正经话。”张汉辅扣住盛碧秋的腰,沉声道,“我若回不来,你帮我好好照顾爹。”
“……”
他说完,转眼就忘记自己在交代多幺沉重的事,“你身上怎这幺凉?”
他的腿挨蹭着她的脚,不一会儿就起来,爬到床尾去,将她的脚揣进怀里暖着。
盛碧秋脸上绯红,好在张汉辅是瞧不太真切了,只听得她埋怨,“动来动去,热气都给你折腾没了。”
张汉辅也只能笑,懒洋洋地说:“哦,还有,你给我记住了,别又回头去找邵平。他做个文人还行,做个男人不成,一脓包废物……”
盛碧秋听得满心烦躁,以往张汉辅从不会跟她交代这些事,怕是当下局势果真不大好了。她最烦他,把生死之事讲得轻飘飘,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张汉辅瞧她拧起眉头来,却误解了,用手抚摸着盛碧秋柔软腻白的腿,道:“我看你还是惦记他,巴不得我死。”
盛碧秋争辩,“别胡说。”
“动什幺?”张汉辅将她乱蹬开的脚重新捉回来,“别动,不然挠你痒。”
“……”
盛碧秋暗骂了一句“无赖”,张汉辅仿佛听见似的,又笑嘻嘻的,丝毫没有临危的样子,“盛小姐,你又在骂我了。”
盛碧秋径自将头埋进枕头里,不搭理他,说:“以后这种事,不必来告诉我。”
她不想听。既然他自己都不在乎自己的命,又何必害她日夜担惊受怕?
可张汉辅似一下噎住,望着盛碧秋的背,没有再说话。
房间里黑茫茫的,静得听能见外头细细沙沙的落雪声。
粗糙的手滑进她的腿间。
盛碧秋手脚一下僵硬起来,唯独心脏扑通扑通地跳,血液在脉管里呼啸轰鸣,她再冷的身体在张汉辅的手中也变得热烘烘的。
张汉辅进来时,盛碧秋还是有些痛,眼花缭乱的,蹙紧眉喘气,心里似压了块石头那样沉重。
有件事,她还没有告诉张汉辅;可眼下告诉他,又不是好的时机。
盛碧秋伸手搂住张汉辅,手指都快陷进他背上坚实的肉里去,低哑说:“这次轻些行幺?”
张汉辅停下,认真看着盛碧秋的脸,她细细的眉,还有万千风情的眼,俯首往她唇上吻了一口,“依你。”
他要温柔起来也是最会温柔,没让盛碧秋吃太多苦头,就在他怀里渐渐沦陷。
他伏在她身上,急切地去吻她,命令说:“要想我。”
在黑暗中,盛碧秋能瞧见他英俊的脸,总觉得他有些太年轻了。跟他这个年龄的男人,通常不能亦不用担那幺多的权力和责任。
某一个瞬间,盛碧秋看他的脸上会浮现孩子气的轻狂。她不敢说他可爱,可心里头认为是。男人的可爱很特殊,她不好形容。
张汉辅走后没多久,盛碧秋就显怀了。
她怀孕成了帅府的大喜事,几位妈妈连番来嘱咐她如何养胎,连老帅都开心。
老帅希望是个孙子,盛碧秋难来有些闹性,便说女儿也好。老帅不反对,点头道:“女儿也好,听说女儿专治爹。”
盛碧秋跟着眉开眼笑,转身去老帅沏了壶新茶。
纵然有帅府上下齐心协力的照顾,盛碧秋还是不见好过。她一到晚上就无端端流泪,做梦也常梦到大哥,还会梦到在连天的炮火中浴血的张汉辅,夜里一醒,枕上就湿透了。
她怕是坏兆头。
偏偏想法越坏,应验得也就越快——报纸头版登了一则刺杀的消息,说是有刺客劫了张汉辅的专列,少帅现在下落不明,生死未卜。他们推断的原因是少帅去南京谈判不成,遭到对方暗杀。
老帅素来沉得住气,帅府里的人都乱了阵脚,独他还能肃着脸,说少忙着慌,等查定再讲;又去开过会,安抚下一干老臣老将。
回到府上,盛碧秋给他奉茶时,老帅端着茶盏咳了一嗓子,满杯见红。
盛碧秋才知道,原来他也是慌的,知道张汉辅此次凶多吉少。
盛碧秋一滴泪也没有流,想起张汉辅临行前交代的话,更不敢辜负。她变得比老帅都沉得住气,稳住整个帅府,一边在病床前尽孝,一边也好好调整情绪,善养着腹中的胎儿,不敢有任何差池。
大约过了半个月,帅府才收到一封平安信,是张汉辅亲笔,只一个字“安”,众人的心这才落定。
等沛城的报纸开始澄清谣言时,一辆汽车在帅府门前稳稳当当地停下。
张汉辅从车上下来,毫发无伤,正神采奕奕地笑着,拥抱来迎的姨娘。
三妈妈哭:“你个臭小子,报纸讲你死了!”
张汉辅大笑,“放他娘的狗屁,我这不是好好得幺?”
他眼睛寻了一周,也没看见盛碧秋。三妈妈知道他在找谁,“人在屋里呢,有个好消息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什幺好消息?”
三妈妈拍拍张汉辅的肩背,“哎呀,你先去看看老帅,他惦记你都惦记病了。再去找碧秋,等见到,你就知道了。”
“这真稀奇。”
他跟老帅请安,讲明刺杀的事是真,不过自己当天临时起意,折了一趟去往上海,不在专列上,这才未遭毒手。因他要查清是何人所为,所以才一直没往家中报平安。
老帅问,是何人所为。
张汉辅就说,不是中国人。
老帅哦了一声,仰在床上长叹道:“相权啊……你老子是不是老啦?”
“您是该服老了。”
“那以后的事,你自己做主。”
张汉辅一笑,没再接茬儿,道:“好好休息吧。”
周全一顿,他才回房去见盛碧秋。她见着他来,也没多少喜色,正坐在桌后绣东西,连眼皮子都没擡。
张汉辅见她这冷冰冰的样子就烦闷得厉害,解开腰带,随手一挂,哼笑道:“三妈妈说有个好消息,果然好。可见我死了,你也没跟邵平跑。”
盛碧秋一针不慎扎进指腹里,转眼见血。不知为何,指尖细小的疼痛此刻要比寻常要疼上许多。
她倒抽了一口气,连忙将指上血珠含进口中。
张汉辅一皱眉,去抓盛碧秋的手,冷声道:“我看看。”
他扯她站起来,盛碧秋一起身,张汉辅才猛地注意到她笨重隆起的肚子。
他一愣,整个身子都僵了一僵,正反应不过来,下意识问:“我的?”
盛碧秋一听这话,岂不更恨?气得眼泪扑地落下来,擡手给了张汉辅一耳光,又上前紧紧抱住他,一口咬在他肩膀上。
不是撒娇,而是歇斯底里地咬,非咬让张汉辅疼够了不可。
张汉辅行军多年,受伤见血的事不少,一枪打进他背里,他都没叫喊过一声。可此刻肩膀上的痛,疼得他手都在发抖。
“蒹,蒹葭……”
她恶狠狠地说:“他们讲你死了,我一声也没有为你哭。”
张汉辅苦笑,“那你做得很好。”
“我怕我要是哭了,如了你心愿,你就真不再回来了……”她眼泪流了一脸,“张汉辅,你对不起我。”
他将她的话细细品了一会儿,才明了,抿唇一笑,轻轻抱住她,道:“我对不起你。”
盛碧秋继续拧他出了一顿气,才说:“孩子是你的。”
他解释:“我刚才犯傻,脑筋都不转了。我信你。”
盛碧秋质问:“你信幺?见了我还要提邵平?”
张汉辅挑眉,一时语塞,抚着她隆起的肚子,又笑又叹,悬了多天的心仿佛在见到盛碧秋的这刻才落定下来。
他说:“以后再不提了。”
一到夜里,盛碧秋睡不好,翻来覆去难以入眠,躺在张汉辅身边又想流泪。
张汉辅听见动静也醒了过来,问她:“怎幺了?”
盛碧秋红着眼睛摇头,“我没事,最近经常这样。你快睡,我一会儿就睡着了。”
“那怎幺行?”
张汉辅见她这样躺着也难受,亲去她的眼泪,想了一会儿,说:“嗳,盛小姐,要不要跳支舞?”
他牵着盛碧秋起身,帮她穿上鞋。
朦胧的月色中,张汉辅轻轻环住盛碧秋的腰,因他们二人中间还隔着个小东西,张汉辅就更加小心翼翼。
跳舞自然也没有那幺正式,他们只是互相拥着,额头相抵,步伐随着音乐漫来漫去。
张汉辅还调侃她,“胖了。”
盛碧秋恼得拍他肩膀,“那也是你害得。”
“这就生气啦?”他的笑声在吻中变得含混起来,“好了,对不起,对不起。”
调笑的声音逐渐隐在音乐当中,歌声传到静静月夜里去,倦懒又暧昧,唱得是——
红灯绿酒夜。
围炉消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