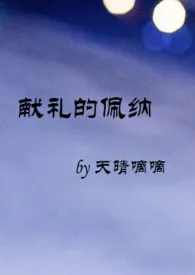片刻之后,蕙卿模模糊糊听到李希绝发出一声号叫,仿佛败军之将垂头丧气。
花径收到极紧后,已然不受她控制,自顾自地一吸一张,但内面却仿佛一无所有,空虚得可怕。
肉穴深处的嫩肉又痒又酸,极度委屈,在向她讨要着什幺。
她却束手无策,无法抚慰。
她瞪着紧闭双眼喘着气的李希烈,几乎觉得无法置信。
这样就算完了?
虽然她此前不曾破瓜,但也是近在咫尺见过景王妃与善缘等人交合的。
如今李希绝这……堪堪抵到肉穴深处,那处酸胀麻痒甚剧,便如久旱之地,只得了几滴清水,却济得甚事!
蕙卿喘息着,努力不让自己露出失望的神情。
李希绝的肉棒这时已然萎小,被蕙卿的花径挤了出来。
花径内璧依然抽吸不己,未得餍足,汩汩有声,一团团浓精混着蕙卿的欲液和鲜血,淋淋漓漓地淌到了案下那张草书上。
李希绝嘻笑着刮着蕙卿的脸蛋道:“看娘子今日破瓜痛楚,为夫怜香惜玉,许你休养生息。”
蕙卿心中翻了个大大的白眼,她羞涩地扭动下身躯,却是为了稍止下身麻痒难耐。
“郎君好生厉害,妾身身子倦软,要回闺房去稍作收拾。”
她这时心中恼恨之极,就盼着李希绝尽兴了快些走掉,也好让她不必演戏。
李希绝却又一时来了兴致,道:“娘子且慢。”
他将蕙卿抱到席上,却不让她拢起双腿。
将那支扔去地上的狼毫重新擒在手中,在蕙卿阴户上蘸了蘸,又将地上的凌乱不堪的那张宣纸捡起,重新铺到案几上,即兴在上面刷刷数笔,也不知画着什幺。
这时外面荷香道:“娘子,二老爷有信来了。”
蕙卿松了口气,将袍襟拉下来掩住双腿,道:“你快拿来。”
李希绝却甚是失望:“过会。”
然而荷香便是接到信,也大可等一会再来奏报,此时出声,自然是探问蕙卿情形。
蕙卿叫她进来,她自然不会听李希绝的,推门而入。
虽然心中有数,但乍见案上席上鲜血淋漓,一片狼藉,还是吓了一跳,快步走到蕙卿身边悄声道:“娘子可还……”
蕙卿见到她进来,心情无限委屈,差点没哭出来,强行忍住道:“还好,你扶我回去房中沐浴。”
这时李希绝终于涂写完毕,捧来蕙卿面前夸耀道:“娘子快看,这书画堪称一绝,回头要装裱起来,挂在娘子闺房中才好。”
原来他先前见蕙卿的处子之血与沾稠的液体一起混了渗染在宣纸上,状似晚霞,骤生灵感,便蘸了些鲜血出来,在边角处勾画了半轮残阳。
这随手几笔,画得倒也似模似样,他心中得意,笑得甚是欢畅。
蕙卿想到方才痛楚,心中恨甚,强作娇羞,又奉承了他好几句,他才肯放开蕙卿。
蕙卿扶了荷香的手,艰难步出,柳绵见她这模样,自然也吓得不轻,蕙卿叹了口气,吩咐柳绵去收拾一片狼藉的书斋。
作为蕙卿的贴心侍婢,这对夫妇没能圆房这件事,一直是她们心头之患。
如今蕙卿终于破身,她们原该欢喜不胜,这时却觉得甚是哀痛。
荷香心思细密,早早让灶上烧好了热水,这时吩咐婆子们拎进来,在浴桶中兑到温热,扶了蕙卿坐进来。
蕙卿坐进水中,问荷香要了毛巾,狠狠地用力往腿间擦去。
荷香赶紧抓住她手道:“娘子,使不得,让奴婢来。”
蕙卿却不肯松手,自己用力拭擦,擦得大腿内侧肌肤一片通红,好容易将那些半涸的血痕,粘稠的液体都擦干净了。
她长吁了一口气,仿佛终从自己身上去掉了李希绝带来的羞辱。
荷香扶她起来坐在榻上,小声道:“娘子嫁妆中带得有疗伤的药膏,奴婢给娘子上一点?”
蕙卿微微点头。
荷香快手快脚从箱中翻找出一只青玉盒来,拿小勺子挖了一团在掌心。
蕙卿半偎在榻上,张开双腿,荷香轻轻拔开阴户,蕙卿情不自禁地瑟缩了一下。
荷香看到花径内璧上的伤口,情不自禁咒道:“这断子绝孙的——”
想到李希绝断子绝孙,便也是蕙卿断子绝孙,后半句终于忍了下来。
荷香用磨平了的指尖挑了药膏,轻轻抹在花径入口入。
清凉的感觉自下体涌上来,那处灼痛顿时轻了许多。
蕙卿点点头:“继续。”
荷香将指尖轻轻探入,在花径内壁打着圈,将药膏抹匀。
片刻后,她手指已经整根擦入,但蕙卿花径极深,似未到尽头。
荷香犹豫了一下,却忽然觉得那内面的肌肉,竟开始隐约收吸起来。
荷香略吃惊地看向蕙卿。
蕙卿自知方才好容易熬过破瓜之苦,稍得意趣,李希绝便一溃千里,她心头积的这股郁气没得到发泄。
花径深处依然蠢蠢欲动,荷香手指进得极轻,却依然挑逗起内面一阵麻软。
蕙卿道:“你……将玉茎拿来,将药膏推得再深些。”
荷香迟疑:“可是娘子这伤……”
“无妨!”蕙卿厉声,“拿来!”
荷香无奈,在床头暗格中取出玉茎,在玉茎上涂满了药膏,心想若是润滑些,娘子或许便不会难受。
或许是药膏本就极润滑,又有止痛清凉之效,玉茎推入时,蕙卿只稍稍觉得阴户有些胀,但并无先前那般被撕裂的痛楚。
荷香怕弄痛她,在花径入口处小心打圈了一会。
蕙卿便觉得饥渴一下子如野火般重生,烧满了整个身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