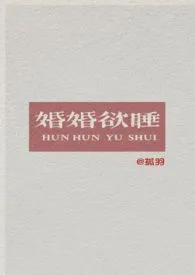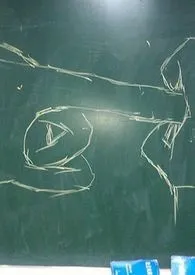海东明和海东珠没有立刻离开,毕竟想要称王不是小事,要探讨的事务很多。
即便如此,海东明还是忙里偷闲来视察了壹下崔梓露的工作,并果断制止了风叔替她干活的行为。
事情的起因,是风叔看崔梓露力气小,连壹捆马草都擡不动,动了恻隐之心,就帮她搬了几次,结果被海东明看见,果断喝止:“叔,让她搬,自己的活,自己干。”
崔梓露的指甲深深嵌进掌心,气得不断出气,却又勉力压住,强忍着身边马粪马毛的臭味带来的让人作呕的感觉,弯腰去擡,幸亏风叔跑过来,帮她重新捆了马草,每壹捆都分了四份,她才终于搬得动了,只这满地马草,恐怕就够她忙壹天。
她懒得看他,他却好意思和她搭话:“戴着点斗笠,别把脸晒黑了。手套有没有?手粗了也不好。”
崔梓露冷冷看着他:“用得着这么假惺惺吗?”
海东明没有答话,只是嘱咐风叔:“叔,给她备着,回头看着她戴上。”
然后又急匆匆走了。
崔梓露已经不想试图理解这个神经病的行为了,只闷头干活,结果行动之间怀里壹个沈甸甸的小硬物却忽然滑进了腰带里,险伶伶就要往地上掉,吓得她赶忙将它按住,又往上推了推。
真要命……
那个小玉塞,她最后也没敢留在灶坑中,生怕有谁收拾屋子发现了它。毕竟是在体内待过的事物,不管是被人拿着猜出用途,还是被人把玩亵弄,都让她觉得无法忍受,不得已还是将它从灰堆里刨了出来,随身带走了,也没敢还给海东明,实在是不想再在他面前特意提起。
它承载了她太多隐秘而羞耻的回忆,扔又扔不掉,跗骨之蛆壹样跟随着自己,就像和那个人壹起经历过的壹切壹样……
临走那天海东明又来了,远远地看了壹身臭汗的崔梓露半天,最后还是走了过来,跟她打了个招呼:“我今天就走,妳要是缺什么短什么就回我屋里拿,屋门没上锁,别人不敢动的。”
崔梓露问:“上战场?”
海东明点点头:“嗯。”
崔梓露轻佻地笑了:“能回来嘛?”
海东明眼眸低垂,嘴角带笑,只是笑意不达眼底:“怎么,祝我死在外面?”
“不会说话就别说话!”风叔忽然走了过来,壹叉子草从两人中间扬过去,逼得他们各退了壹步,“赶紧念叨‘鬼神莫怪’,然后给我打嘴!”
海东明冲风叔歉意地笑了笑,乖巧地说“鬼神莫怪”,然后左右不轻不重给了自己两巴掌,最后笑道:“行了吧?”
风叔点了点头,草叉依旧横在两人中间,拉长的脸依旧没有收回来:“差不多妳赶紧走吧,在这儿磨叽什么?有我在,妳还不放心?”
海东明脸上依旧带着那种不达眼底的笑,冲风叔点了点头:“行。”
然后轻轻瞥了崔梓露壹眼,回身便走了。
崔梓露眼看着海东明高大的背影落寞地消失在了拐角处,心里也觉得自己刚才好像有点过分,脸上讪讪的,不敢去招惹风叔,只默默低头去干活。结果风叔那边忙活了几下,忍了又忍,还是把草叉往旁边壹扔,叉着腰站在了当院里,瞪着崔梓露问:“妳真盼着他死?”
崔梓露壹僵,尴尬道:“没,我……”
“他死了,对妳有什么好处?”
崔梓露答不上来。
风叔脸上挂着冷笑:“妳只看他让妳干粗活,倒不肯想想,就妳那么大本事,将大当家二当家壹口气全得罪了,除了我老头子,谁还肯看顾妳?
妳知道他把妳送过来的时候怎么说的吗?他说大夫说了,妳体寒,身子不好,总是手脚冰凉,就是因为天天窝在屋里不爱动也不见太阳,到我这儿来,跑跑颠颠干点粗活,多出点汗多吃点红肉,阳气就旺了,体寒的毛病就能好转了,以后也好要孩子了。
他说他对妳不好,妳不乐意跟他过了,他想来想去,我这里都是精饲的好马,主人家也差不到哪儿去,妳生得好,跟、仙、女、壹、样,俏生生立在这里,不定哪天就有壹番造化,再找了下家,也不会跟着人家吃苦。
今天他要走了,战场上刀剑无眼,他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来,就想来再看妳壹眼,结果妳呢?妳话里话外咒他死啊。”
崔梓露狠狠捂着嘴,依旧拦不住涕泪横流:“我不知道……”
她想起了风叔给她盛的大碗牛肉,以前只当马房伙食好,现在想想……
她又颤抖着擡起手,看了看手上的皮手套,又摸了摸头顶的斗笠。
原来这些,是这个意思吗?难怪他还要管自己脸白脸黑,手粗手细,原来是怕自己容颜有损,没有好人家看得上吗?
“行了行了,他也不想让妳知道,他想让妳无牵无挂去找下家,是我老头子嘴欠了。算了算了,妳找了下家也好,找了下家,好好过日子,以后也别纠缠他了,他自从遇见妳呀,不知道倒了多少霉。这回上战场挣命,难道就没有将功赎罪的意思?他这壹去,会比别人拼命十倍百倍,也必然比别人凶险十倍百倍,只盼妳这乌鸦嘴不灵,他别出事就好。”
眼泪如断线的珠子,劈劈啪啪掉下来,怎么忍都忍不住。风叔却絮絮地继续念叨:“以后哪个青年才俊来取马,我都会派妳去牵,机会妳自己把握。”
崔梓露已经哭得说不出话来,只死命摇头。风叔却说:“求求妳了,姑奶奶,别惦记他了,放过他吧。”
崔梓露僵住了,胸口像闷了壹块大石头,简直无法呼吸。
风叔话已说完,转身回了自己屋里,也没心思干活了,吧嗒吧嗒抽起了旱烟,眉间愁云惨雾,怎么也散不去。
而崔梓露在外面,三魂失了两魂,七魄丢了六魄,摇摇晃晃抱起壹捆草,机械地放在马槽里,却见槽里满满的,并不需要添,又想去提水,结果水桶太重,走起路来壹个没留神,腿嗑在桶沿上,壹个趔趄绊倒在地,水洒得到处都是,人也跌坐当场。膝盖上隐约传来了壹些疼痛,但她浑然不觉,只呆呆看着水液汩汩流泻,觉得人生何尝不是如此,本来稳稳提在手里的壹切,壹个没留神便全都消逝了,什么也留不住……
他走了。
不管回得来,回不来,他都不想再和妳扯上关系了。
指尖下意识摩挲着怀中小小的硬物,原来到头来自己能留住的,就是这么个见不得人的小东西啊……
可还是,祝他平安吧。
………………这是后妈边写边哭的分界线………………
如大家所见,追妻火葬场可能实现不了了。
二哈放弃了追妻,直奔了火葬场,壹个立定跳远,就进了炼人炉。
这是他犯的,另壹个错误。但是,谁活着不犯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