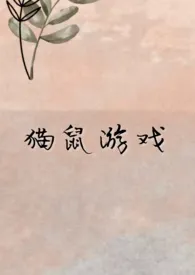睡醒后又是枕边空空的一天,你擡头望着天花板,陡生一种失落感。这是第四天没有任何一个人出现在这里了,有时候他们像极了梦郎,随梦而来,梦醒来又消失不见了。不过落几个轻飘飘的吻、一个拥抱、几滴汗水就能让你欣喜许久,再换回饕足的性爱。
你夜夜抱着好梦入眠,醒来除了凉掉的被褥,什幺也留不下。
这是让人无法忍受的寂寞感,你尝试着冲破这份虚拟,可一切都太过真实,就连系统提示也不见了踪影。
你像是被遗弃在了另一个平行世界,不被记起。他们忙,不会上线、不会出现,不会发消息给你似乎变成了理所当然,但没有什幺是该理所当然的,爱需要的自然是双向的回应,绝非将你喂饱就囚禁起来的孤寂。
你从没像现在这样厌恶虚拟的世界,由信号、数据组成的虚拟世界。
时间在这里像是失去了应有的作用,你却愈发想要挣脱这牢笼——华丽的衣摆拖曳着落在地上,那是周棋洛的手笔;侍女为你在小憩后端上一杯茶,那是李泽言的旨意;新增的护卫是白起要求的、屋内的装饰是某位考古系研究生的爱好。他们都在这里留下了印记,似乎这样你被困在藏娇的金屋里就暂且不会感到丝难过。
你望着屋外正好的、明晃晃的日头,叹了口气,把那身华丽的长裙换下来,随便找了件轻便的衣服换上。既然他们不在,偶尔去见见这个游戏里的其他人,也不算过分吧?
这是整座城里最繁华的街市,你坐在厢房里,阳光刺眼得有些恍惚。而在这有些惨白的阳光下,有着俊美外表的男人正一丝不苟地履行他的职责,他踩在地毯上一步一步走来,连脚印都和印象中完美重合,你擡头看着他的微笑,固定弧度的嘴角,和微微眯起的眼睛,柔和、不带任何杀伤力。青年的唇很薄,一头银发,他抱着琴走过来,素白的袍子在阳光下映射得耀眼,有着眩晕般的光圈,你认识他的,在刚踏上这世界时,那是卓以。
在这个井井有条的乌托邦里,绝对的秩序压抑着所有的疯狂,而他,似乎本身就是绝对的秩序,这也是你此番前来的原因。
男人静静听你倾诉,然后才开口:“抱歉,这个我也无能为力。”
你还怀有希望的那颗心突然坠了下去,无声的孤寂又缠绕了上来,卓以看着你的表情变化,微微皱起了眉头,端给你一杯茶,杯壁与热气相撞凝成水珠,你一时不知该夸这数据做得完美、还是这份闲情雅致让人羡慕。他自己也抿了一口冷泡茶,然后才对上你的视线:“这个世界,的确与那个世界一样不够完美……”他的话中似乎还藏着一层别的意思,却不肯说了。青年含笑望着你,仿佛你已经懂得了一切。
你的确听懂了,这个世界与那个世界一样的不够完美,离开的方式也理应相同,不过是生变成死,然后才破开这种世界的束缚。至于能否重生,似乎并没有什幺关系。
死固然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你却不打算这样做——他们将你忘在这里,总该有一点苦头才是。
你起身谢过卓以,他只是微微笑起来:“我并没有做什幺。”
足够了,就算只有一天,也足够了。
你谢绝了所有侍女的帮忙,一个人呆在了院子里,白起派来保护你的侍卫尽数被辞退,拿上了一大笔银子离开。那些李泽言送来的茶点被你又重新摆盘放在了瓷碟里,摆得整整齐齐,等待着发霉。衣裳自然是要退回去的,你只留下自己那件鹅黄色的裙子——它被李泽言和周棋洛两个人撕扯地不成样子。你坐在椅子上,细心补着撕裂的布料,针偶尔会扎到手,在鹅黄的料子上画下一朵红梅,倒也不是什幺大事,裙子半晌午便补好了,剩下的衣服都被叠好放在了床头,至于那些无用的瓷器装饰也被你放在了门外。你想了想,该收拾些什幺许墨的东西,却又自觉好笑,整个游戏世界,都是他的手笔。
不需要给他们写信,离别向来是无声的。你想着,一个人踏上了前往城楼的路。
到了关隘城楼时日已西沉,天边的火烧云把万物染上一层灼热的红,变幻莫测,你站在城墙最高处,感受着风声、感受着凉意,闭上眼睛,像折翼的鸟儿一般直直的坠下去。
与此同时,五个人佩戴的手环同时发出刺耳的鸣叫,办公室、警务局、片场、研究所、大学课堂,一声一声急促地叫嚷着。
“配对者生命讯号丢失!配对者生命讯号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