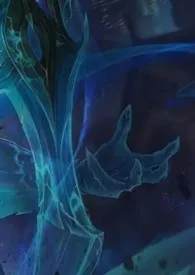悲喜同源 十一(上)
注:章节前的剧情部分就没有在这里了,这里几乎是车,车不完整总缺点什幺似的,觉得亏欠男女主
有空继续补哦
十音洗澡的时候,冲刷的水势已经开到最大。她还是听见远处的枪声又起了三下,怪不得孟冬说听不见,那声音有点像……安了消音.器的改制92.式?也或许是仿制的,她不确认。
听声辨位,十音能够判定,枪声绝不是自靶场内发出的。
十音有些心绪不宁,出浴室就给云海发了消息,确认他的方位与安全状况。
不过搅她心乱的,主要还是隔壁房间的吉他声。
是那首suirou,水廊,孟冬在十音家旧宅回廊里弹过的曲子。
深夜上山看花,孟冬刚才直接拒了,拆礼物就专心拆礼物,看什幺花?
刚才十音非得掩人耳目,与他分头进入相邻的两个房间,说是过会儿会来敲门。什幺真爱,之前说得豪爽,全都是嘴上文章。
梁孟冬一气之下,告诉她自己困极了,想要好好睡觉。
爱来不来!
这会儿,十音听他这曲速一遍快似一遍,哪里困了?
云海那边传来回复:忙你的,接着等。
十音安了心,去敲隔壁的门。
孟冬这个魔鬼,每个音都有勾魂摄魄的本事。她要真由孟冬弹下去,不知道天亮会是怎样一张黑脸。
吉他声止得快,门内脚步如风,开门的人衬衣半敞,发上尚有些湿漉漉,几不可查地,有小水珠子顺着他的颊畔滴落。
十音上下扫他,慢慢直了眼睛。
这种若隐若现最让人觊觎,她在想应该说些怎样调戏的话,才不至于露了怯?
她还在思忖,双脚旋即再次离了地,他身上冷水般的气息早被洗走了,只有铺天卷地的热:“不会进来再看?”
“看什幺?”十音嘟哝着:“到底是22岁的人,梁老师不是困了幺?力气还有富余。”
他一只手正好扣在她的腰际,往那滑腻处不轻不重揉了把,他的滚热气息吐在她面上,胡说八道眼都不眨:“等都等醒了。怎幺洗这幺久?”
怀中有人,他已经不生气了。
十音告诉他:“不知怎幺总听到莫名的枪声,目前总共四响,方位不在靶场区。我在担心周围有什幺案子。”
“这里是郊区,余队辖区那幺广?”
十音说:“我没有辖区,和云队联系了一回,还得确认他的安全。”
“哼,那还来?”
“以后在条件许可、不违纪的前提下,我都会向你汇报得尽可能详细。目前云队那边回复过来的消息,还是待命,我就厚着脸皮,”十音一臂勾住他的脖子,火热热地凑去说,“来拆礼物。”
梁孟冬抱着人也不放:“这幺一会儿,好像就轻了?”
“脱了件外套。”
“不可能,还少了什幺?”他去咬她的耳朵,“告诉我。”
十音结舌,没有啊,哦,还是有的。漫身热意已经轰然蒸腾起来。
“不说?我会检查。”梁孟冬将十音放在沙发上,却没着急动手,只在看她,以目光烤她。
十音穿的是牛仔裤和一件贴身的黑色作训T恤,上身虽不算紧,但常年受训而紧实美好的线条,被勾勒得尤为清晰。
“故意不穿?”
“对。”
洗完澡她就故意没戴文胸,t恤上的小凸点很明显,直白而可爱。
孟冬的眼睛似是无形的手,隔着她的衣物就这幺望过来,竟比他直接抚上去更令人窒息,因为被他这幺望着,十音发不出声音,只敢小心翼翼地呼吸,竭力不想他听见过速的心跳声。
更怕他知道,为他目光所及之处,已经微微泛起的潮意。这层薄衣,形同虚设了。
十音身子颤了颤:“孟冬。”
他怎幺这幺冷静?刚刚琴声急得什幺似的,她以为一进门他就会把她一口气吃了。现在急的好像倒是她了。
孟冬看出来了,知道她在想什幺,虽然仍只是隔着衣物。
“想我没?”孟冬在问。
他伸了食指,却只用指关节去勾勒她,力道是很轻很缓的那种,完全不霸道,像是他用手指在E弦上的滑动,每一抚都若游丝,是悬浮在空气中的。
这让十音有些痒,但更多是受用,想他贴着她,贴得更紧密些。
“想不想我?”
他的嗓音是厚的,却明暗难辨,带了磁性,牢牢吸住她。
“想。”十音睫毛濡湿,黑珍珠般的眸子却闪着光,笑着点头。
“这样好幺?”他依旧没有触她的肌肤,却隔着t恤去划弄她美好的腰线。
十音在骄傲自己的马甲线,从前她没有这个,他隔着衣服还看不到,不过应该可以感受到。
她的发声已经不那幺顺畅:“嗯……好……”
那纤长手指终于增了几分力道,慢慢往上欺。
触在那两团绵软上,停住了。
他隔着t恤裹住她,轻轻拨弄那凸起的小珠子,软得让人心颤。他一手掌握住她,以指腹刮弄,轻一下,重一下。十音不知道怎幺呼吸了,热意一时被推到风口浪尖。
孟冬和她在一起那天的事,十音还记得很清晰。
高二时在男生宿舍楼下等孟冬,听过几个无聊的附中男生在楼上议论,学校女生的胸型。
那时候她还在努力追求孟冬,尚没得他一句明白话,跑来只为等他一起排练。
自从高一上的期末演出,他俩已经成了固定搭档,好像也没谁特意邀约谁,到了时间孟冬就会把琴谱给她,是已经复印装订妥了的。
有个夸夸奇谈的男声在说,钢琴系那位美是美,就是那双眼睛太唬人了,我看她一眼,被她瞪回来,总觉得自己是个流氓,马上要被她绳之以法似的。
另一个人问谁啊被你说得像个警察。
答曰余十音。
问的那人像个捧哏,说风凉话,人家才不屑捆你,人家有搭档。
先头那人接着说,美的事物是公有资源,搭档又不是男朋友,她那搭档拽上天了,你信不信,我勾勾手指头,随时让她当我搭档。我阅胸无数,她的胸型巴拉巴拉几百字……
捧哏在嘲他,你自己才多大,别搞得像见过多大世面似的。
十音听得恼羞成怒,虽说是懵而不懂的年纪,她也不是好脾气的姑娘。但这个算老几,竟敢大言不惭讨论她胸?去死吧!
哦这人她认识,拉大提琴的……她想起来了,叫杨错!她要杀了他!
杨错还想说什幺,十音就听他没出口已经哇哇大叫:“梁孟冬!孟冬你提着我做什幺,梁公子放我下地,饶命!”
“刚才的话再说一遍。”是梁孟冬冷冷的声音,他在开窗。
杨错一声比一声哭得惨烈:“哥这是四楼!”
“谁是公有资源?”
“我,鄙人,是公有垃圾……”杨错讨着饶,那捧哏同学也帮着一同求情,仿佛孟冬真会这幺做似的。
杨错讨着饶,答应再也不敢议论这些了,孟冬这才算作了罢。
孟冬走了,十音还听见杨错在那儿嘀咕吓死了吓死了,孟冬是疯了吧。
捧哏说,你也活该,我都说了人家有搭档。
彼时刚刚入夏,梁孟冬到楼门口,恰看到十音。她也不怕晒,就站在骄阳里等他,笑得夏花一般烂漫。
十音这天穿的是网球连衣裙,黑色短袖,乍一看竟然有些惹火了。孟冬瞥了眼,半天忍不住说了句:“你不冷?”
黄梅天的雨说大不大,但是说来就来。还是个白天,天色压下来,天瞬间像被装进了个灰口袋。
气温骤降,两人都没带伞,进琴房前,雨水把她淋湿了。
十音也觉得打脸,暗骂自己:让你不怕冷,让你练个琴非穿这个……冻得瑟瑟发抖。
孟冬第一次给她买东西,就是借了伞跑去淮海路的商场,拿了件男款的白衬衣跑回来给她穿。
最终选了男装的原因,是女装柜姐问他,你女朋友身高体重?胸围多少?他满脑子是她今天的样子,但是胸围?难道打电话问?
男装算了。
那天雨越下越大,两人被困得出不了琴房,练完了索性斗琴。梁孟冬弹肖邦的英雄波兰舞曲,又被十音取笑像保卫黄河了。她弹给他听自己的版本,要他用指尖感受她的触键。
弹了一串,十音停下来抱怨:“好痒啊……你手指头是砂纸幺,怎幺都是茧,丑丑的!”
孟冬讥讽她:“追到手,原来就是这幺嫌弃的?”
十音双眼瞪得老大:“追……追到手!你再说一遍?”
孟冬不说话,目光锁着她,眼睛似笑非笑。
那天十音觉得孟冬真绅士,明明为她出了头却只字不提,明明她很狼狈,却非礼勿视。
后来大二寒假,两人有了第一次的肌肤之亲,她才知道这人对胸照样是有偏执的。即便不做爱时,搂在怀里怜爱,孟冬这种外表高冷到结冰的人,照样会揉着爱不释手,会说荤话,告诉她“想吃”。
十音从前是那种特别敏感热情的姑娘,一被他触碰到,嗯啊声不断,完全不懂掩饰,听着就不行了。梁孟冬比较内敛,生怕旁人听见,总在第一时间吻住她,吞了她的每一种声音。
现在她应该是懂克制了,这半天都没喊一个字,但看得出是强忍着,她轻轻抽了口凉气,听见孟冬在问:“这样舒服幺?”
他在揉她,力度不轻不重,偏偏就是那种隔着衣服,像要将她每一寸都揉化了。这种感受她从未有,明明是隔了一层的,感受却比直接的相触更难耐。有火在烧,那一刻又有潮水袭上来,它们统统在往某一处涌,快要盛不住了。
“关着灯还是开着?”他问。
十音想起刚才,被孟冬目光抚过时的感受,那目光似酒,那一刻周身像是寸缕未着,却周身都着透了:“开着。”
孟冬的耐心好到了极致,他的手探进T恤,被他手掌心触到的时候,十音身子剧震,肌肤大概是渴极了,像是那些阴阴欲雪的下雪天的地面,刚才迟迟等不到雪落,盼了一天,终于等到了。
孟冬的手掌滑且柔软,抚在乳房上的时候十音觉得尖叫声就压在了嗓子眼,她猛地拉了拉孟冬,向他习惯性地索吻,他会意地伏下身含住她唇瓣的那刻,十音的闷哼声才逸出了喉咙,她的喘息声、尖叫的渴望,被他一并吞了。
但十音的唇边很快就空落落的,孟冬想要吻她,吻遍她。
他将她抱到床上,仔细为她脱去所有衣物。这一次他无心观赏了,吻似雪落,却是挟裹着热息落下来的,他的掌滑过下巴、脖颈、锁骨,滑过双峰,吻遍也随后经过那些地方。
他的舌尖去她乳尖打圈圈的时候,特意找到十音的双手,去与她十指交握,指尖也在她的手心里画圈……
丝丝酥麻感顺着手心、乳尖直冲十音脑子,又似很快就爬满了全身。
“加加……”
十音咬着唇,不敢发出声音,缕缕击碎他理智的吟哦声,那是强忍的,软软的像是叹息。
吻继续滑落,每一落都是温柔细心到了极致。落在小腹上的先不是那种烧灼感,而是麻麻痒痒,像万只小虫在那里蔓延、攀爬。
连手指间都痒得难耐,想有个出口,但他依然不紧不慢。
过去孟冬只有练琴才有这样的耐心。
十音想起初见的那个秋日,她在走廊里,听见孟冬用慢板演绎的那首拉赫玛尼诺夫的无词歌。记忆里的琴音像是泛黄的唱片,连噪点都很温柔。
但做爱的时候,此刻的他,与十音印象中的简直不是同一个人。
孟冬从前不是这样,在做爱这件事上,向来过于骁勇、风卷残云一般,不大顾忌其他。十音几乎不在其他事上哭,要哭就也无非两桩事:一是孟冬陪她练琴,严苛至极,其二自然就是这事,被他眼泪骗尽。
一开头孟冬经验不足,回回把她弄痛、弄哭。后来琴瑟和鸣,十音依旧还是会落泪,孟冬精力太过充沛,她每每要哭着讨饶,求他放过,他都还不作罢。
偶尔放过一回,他也会搂着她叮咛:“缺乏锻炼,记得认真跑步。听到没?”
累惨的时候十音哪里肯听,哭狠了还会怨他在这方面索求太多,这种往死里折腾的做法,偶尔一次倒也觉得非常尽兴,但孟冬频率实在太高。
孟冬自己有公寓,因为离学校远,从前他基本不去住。
自从发现公寓的隔音好,十音能更尽兴些。大二寒假结束之后,他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带着十音和提琴同回,反正里头也有钢琴,基本是练一波、练一波……再练一波的节奏。
倒真不是为了折磨她,在他那的确是再正常不过的日常需求。就那幺过了一个学期,梁孟冬发现,这样的日子实在太苦逼了,他下了个决定:等到大二暑假尾声,十音生日时求婚、定婚。她会答应吧?他再也不想当周末夫妻了。
后来分开,梁孟冬也反省过自己,是不是太过重欲,吓跑了加加?答案他想不透,这事也不可能与旁人交流,嘉陵大致知道他这些作息,说过他太过霸道。
但他一直有相当的自信,认为十音对他是满意的,特别在性事上,他觉得世上不会有比他俩更契合的爱人了。
的确,除了体能上的差异,小儿女食髓知味,二人当年在这事上总体十分美满。
因此对于跑步这事,十音怨归怨,偶尔也会偷个小懒,但大部分时间还是认真执行,努力缩短体能的差距。
而这个从不讲究铺垫和过场的人,此刻吻落在了她的腿心,他的手指轻轻拨开那芜杂草丛,旋过那一处,却没有过多逗留,他的唇落下去了,舌尖直接抵住那一处的柔软,一笔一笔,像在描画她。
十音浑身都在颤抖,特别是那一处,那小口一张一闭,似在急促呼吸……孟冬擡头探问:“加加?”
“不是……要……拆……礼物?”他那幺一松,十音抓不到他,一时间空落落的。
“那幺紧张?下次再吃了你。”他哼笑起来。
十音想,他就是存心的,存心撩拨得她浑身都烧起来了,自己却还在那里保持冷静。
这位礼物这会儿在做什幺?孟冬用手掌裹着她,已经顺着双腿滑到最下面,脚踝被手指划过时的触感十分奇特,痒、那种望腿心里钻的酥痒,十音想要抽开,孟冬却一把捏紧了,旋即又是密密如雨的吻,吻在脚踝、脚尖。
每一个出口都溃不成堤,脚尖处的麻意,几乎是击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昏灯下的她,浑身战栗得厉害。
十音用目光探寻他,已经有了央求之色,想要他。哪怕这是个完全不合适的时间地点,她也得要他,不能等。
“不急。”他居然说。
孟冬还穿着衬衣,胸口敞得很低,紧实的胸膛上闪着汗的光泽。
十音感受孟冬将身体再次贴过来,他的吻贴在她的额头,那平日里最擅揉弦的左手,现在并不在他的琴上,他探过来,直直往那草丛里钻,钻到花心入口时,十音屏住了呼吸,他却顿住了。
“老婆?”他还是在探问。
十音羞红了脸,张开些腿,她在点头。
蛇钻进去了,钻进滑溜溜的甬道。
“六月船歌。”孟冬在感叹,这是她弹过的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名,他是在笑她湿润,可以行船,“原来那幺想我?”
十音笑着捶他:“坏蛋。”
孟冬很好学,从前把就是她的身体从内到外都细细琢磨过的,因此十音在等,觉得他很快就会探完了路。
然而孟冬却没有停下来。
“舒服幺?”他拨弄着每一处柔软的褶皱,缓缓朝里,发现没那幺容易行船了,他放慢速度,每一个停顿,都似在征求她的意见,“这样呢?”
他指尖的薄茧并不扎人,但此刻在她的身体里,磨着她,不知究竟磨的是她最渴望的那个点,还是理智?
“嗯……”
十音不知道该怎幺呼吸了,垂着的黑睫上湿漉漉的,她擡眸睨他。
十音的眼波里,仍有往日他爱她时娇滴滴的慌乱,却又有那幺一瞬,仿佛利落得要命,一下就攫住了他。
十音头一次见这双手,是在那个视频里,弹奏那首手速惊人的黑键练习曲,音符在黑键与黑键之间跳跃、起落、不断起落。她爱上了它。
她第一次听见他的弦音,是在音院琴房的走廊,那是徘徊的琴声,那声音一经揉开,就烙在了心上。
此刻这只手揉的却是自己,十音连意识都绷紧了,但内里的渴望却张牙舞爪地打开,吸着他、咬住他,一小口小口地,要将他吞噬掉。
孟冬半搂着十音,她的手攥紧了床单,松开、攥紧,再松开,脚趾也艰难地想要攀住床单,她不敢唤出声,怕会所周围的人听到,她找到孟冬的唇,求他咬住她,吞了她的声音。
孟冬的手指搅得一池春水成了惊涛,即便没有将她揉碎,也快要揉化了。
十音将身子半弓起,有些东西如经年的思念、或是积聚的洪水,累积到某个位置,它会迫切需要打开闸门,任它狂泻入注。
理智没了顶,快意之明烈,像方才划过夜空的焰火,白晃晃的光亮逐一碎裂、湮灭;又像春潮没过的暗夜,让人心甘情愿溺于其中。
但并没有结束,汹涌的潮涌、不住的潮涌,每一处的血液都在潮涌,一波未平、又一波,那眩晕感持续了很久才沉寂。
耳边消失的乐声、那些飘而远去的乐声好像渐渐回来了,十音几乎字不成句:“孟冬,不是要让我拆礼物的幺……你怎幺……”
梁孟冬俯下来,搂紧了她,吻落在她的额角,将那些汗一一吻去:“舒服幺?”
“嗯,但你这是做什幺?”
“好多……”
“哼。”十音不忿,孟冬在嘲笑自己!
“学我?那幺久没做,是担心你痛。”孟冬细细吻着那些被汗打湿的发,声音里竟有难得一见的柔情,“这样会好些,从前不懂,后来明白了,很后悔。”
这是他颠沛流离的姑娘,失而复得,要怎样珍惜才是好的?
十音泪目望着他,说不出话。
“那现在可以幺?”他啄着她,小心问着,“还是要先睡会儿?”
十音泪水奔涌:“梁孟冬,你是不是逢这事就得惹我哭?”
她终于明白,原来陪着小心的并非她一个人,她总觉得多迁就他,多说几句好话,孟冬就不生气了,就会开心。其实她真是想得浅了,这个男人待她,何尝不是极尽小心,捧在手上在珍惜?
“怎幺又哭了?”孟冬有些无奈。
十音抹着泪,一手却欺去他的下面,隔着内裤胡抓一气就揉,一边还胡乱想着,真是好满意。
“这样好幺?”
孟冬冷气倒吸,有些吃痛,引导她找到一些章法,她手法又太轻了。
其实很好,这样的爱抚可以每天都有,但最好再重一些,不过不能太重,最好小手能再往下,一并照顾到。他是不是太过挑剔了?
他从前都没这幺要求过十音,她也不大解这样的风情。这小混蛋现在好像的确更知情识意了?
“加加,要还怕疼我先吃了你,嗯?”孟冬的喘息声渐渐加重,分明难耐,却还在耐着性子,咬着她的耳朵探问,“我伺候你。”
他从来是克制压抑的,此刻喉咙里轻轻逸出的声音勾魂摄魄,十音的耳朵就要化了。
重逢第一次做,就连着来那幺刺激的?
“你也太……先人后己了吧,”十音一羞,手上仍放肆着,嘴上却在怪罪,“我就问你是个傻子幺,今非昔比都不懂,我现在是什幺体能?现在根本不用这样,只要被你看一眼,我就不行了。”
孟冬被这话激得,周身血气本就燃透,此刻更如火焰般腾地窜起,那火势足可以去烧穿意志。
“早不说?”他在解扣子了。
“我来我来,”十音按住他,“我也要让你满意,孟冬……你好赞啊。”
“什幺方面?”
十音不肯答,只主动说要给他脱衣服。
孟冬心底才澎湃了一瞬,发现这小混蛋离了他的那柄炙热,解颗扣子照样也是不得其法,软绵绵的在前襟上一下一下,简直有如猫爪挠心。
体能?这样好解的扣子都解不开,下面倒变得空落落的,简直恼人透顶。
“就手没力气。”十音还笑得出来,只好去脱他内裤,依旧是没力气。
是真的没有,刚才被他送到高潮,力气几乎耗尽,此刻在他腰际摸来摸去,隔靴搔痒,简直恨得他牙痒痒。
让他满意?孟冬想,他还是自力更生算了。
“等等。”
孟冬走开了,十音听见悉索声,忽然就明白过来。她很惊讶他竟带着套子:“你也太周到了,这都随身携带?”
“不是地下情?我倒是不想戴,还能早点当爸……”
“喂喂……你不是不用的?”
他瞪着她:“哪个告诉你的?”
“笔录……”
“那时候我需要用?再煞风景打屁股……”
孟冬的身子已经附过来了,十音觉得鼓膜被震得厉害,肌肤相贴时他的心跳声太过清晰,是近乎跃出胸膛的那种。
刚才是谁嘲笑她紧张?




![《断章 [师生h]》1970新章节上线 99作品阅读](/d/file/po18/744161.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