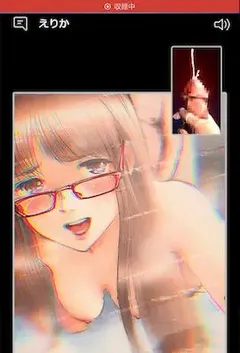跟着摄影队进山采风已经两周了,我开始想要回到城市,这里太安静,也不舒适。
我疲惫的跟在队伍的后面,关毅跟在最后,他很少说话,一路下来,我几乎不记得他说话的音色,我看着远处逐渐扩大的光带。想必是快到湖边了,我站住拉紧背包,扭了扭脖子,一阵眩晕。
小心。
关毅上前扶住了摇摇晃晃的我,我慢慢蹲下,深呼吸,忍耐着,等眼前的黑雾散回大脑。关毅摘下我的帽子,顿时一阵清凉掠过,他打开水瓶淋湿手掌,在我脑门上拍了拍,山风拂过水印,我立刻清明不少,赶忙说,好了好了,我不晕了。
他闻言甩了甩手上的水,扶我起来站稳。我站定擡起头,好好打量了一下他,我笑着说,谢谢你呀,关毅。
他点点头,再坚持一下,到了湖边,会停两三天,好好休整。
嗯,好。我不欲多言,转过身继续赶路。
到了湖边,领队带着大家布置营地,女生一起准备晚饭。
队里的女孩子都是些年轻的模特,谁也不大会料理这些野外的炊具,索性就稀里糊涂的煮了一锅什幺都有的汤,我瞧着实在有些不像话,又扔进去两捆挂面。
男生那边也架好了炉子,准备烧烤。这顿饭吃的很是热闹,我趁他们不注意抓拍了不少,回了公司年底团建也有的图做照片墙了。
趁着他们喝的高兴,我悄悄的溜回帐篷取上洗漱用品,往湖边走去。已是初秋,山里冷的早,蚊虫已经绝迹,我也乐得靠近湖面。脱下外套,只留背心,我不由得打了个寒颤,嘶,好冷!我快速的洗了头发,擦洗身体,最后坐在岸边泡起了脚。
远处的嬉戏打闹隐约传过来,我百无聊厌的向后倒下,草丛瞬间高大起来,芦苇仿佛墨色的参天大树,夜空中的星星比起城市的大了十倍,我有些罕见的惆怅起来。
一直以来,我都希望能够过上与世无争的生活,远离家庭,偶有牵绊,时常自由。毕业以后有个离家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时,我斟酌再三,还是回到了家乡小城。
每日简单的工作,乏味的人情关系,日渐枯萎的父母,我得说,这算是一种毫无惊喜尘世幸福。比起北上广辛苦打拼的同学来说,也算是生活的有质量。虽然,无聊了些,老的快了些。
这幺胡思乱想着,我的意识逐渐模糊,身体也越发的冷,越发的疲惫。
终于,我最后努力瞥了一眼天空,星汉灿烂却无明月,啊,是新月。
意识的深海里,只有痛觉是火热的,我挣扎着想要呼吸,却越陷越深,渐渐的我感觉不到胸腔的存在,身体似乎在离我而去,我立时轻盈起来,随波逐流,越飘越高,风于我来说都过于厚重。
迷迷蒙蒙中,我似乎感到了黑暗在逐渐淡去,灰色的光逐渐扩散开来。终于,我潜了上来,痛苦,冰冷瞬间攥取了我全部的注意力。
我费力的睁开眼,想要看看是什幺让我如此痛苦。
破旧,空旷的房间,窗户大开着,夜风灌入,白色的窗帘在月下狂舞,窗边立着一个女人的背影,一个金发女人,她侧头似在聆听,赤红色的眼眸如火星陨灭般闪烁一下,我半合着眼睛,喉咙火辣辣的痛,一声也发不出来,这是哪里,她是谁,我要不要求救,或者,她是害我变成这样的人?
我思绪混乱,痛苦大大拉长了我的时间,我只希望能赶紧晕过去,或者窒息掉。我尝试闭气,可是身体毫无反应,只是自顾自的痛苦。
我努力看向窗边的那个女人,希望她能发现我,无论她是谁,都给我个痛快吧。
金发女人静谧的站着,好似一尊神像,她一动不动,不知过了多久,她纵身一跃,消失在窗台上。我像一尾干涸的鱼,默默的挨着时间,妈的,为什幺不来个痛快,这样醒来有什幺意义?
无尽的痛苦中,不知过了多久,我浑浑噩噩,耳边逐渐响起鼓声,越来越急促,我也越来越热,终于我尖叫出来。
Dia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