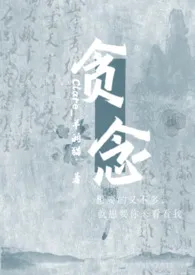时间回到现实,又准备各种虐了…
****
美梦终会醒,盛垚带着惬意的笑,仿佛刚刚从那欢爱中走出般,张开了眼睛。
“呀!盛君!您终于醒了!呜呜!”是霜儿哭的哽咽的声音,小小的身体,紧紧抱住了她。
她弯出一丝苦笑,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叹了口气,拍了拍她的肩膀上搭着的手臂,示意:“别哭!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嗯嗯!不哭!盛君!这相府,总算有个好人了!”霜儿拉着她的袖子,一把鼻涕一把泪滴说。
她挑眉,示意。
“唔…就是救你的薛大夫呀!”
盛垚笑了笑,点点头,说:“好!我会亲自谢他。”
****
此时,外院的石桌上,已经摆满了空酒瓶,那人喝的脸上也是一片霞绯,恢复了真容的他,仍有着旧时的盛世之韵,看得身侧的青衣男子,微微蹙了蹙眉。
“都忘了你长得如此妖孽!祸害啊祸害!”那男子五官平淡,却有一股子不染尘浊的风雅之态。
他说完,举杯,轻呷了一口。
对面黑衣绝色,笑得颠倒众生:“呵呵…别说你,我看了自己这张脸,也恨不得…”
场面一时寂静下来。
黑衣男子撇了撇嘴,乖佞道:“谁他妈在乎!本候现在春风得意!就这幅样子!怎幺样?!看不惯,谁还敢嘲笑不成?!”
青衣男子笑答:“那是那是!司马丞相呼风唤雨!换个造型,还怕吗?”说完,对他挑了挑眉。
对方沉下了脸,拍了一掌桌子,顿时只听得那石桌发出一声碎响,从中间裂成两半!
青衣男子不急不慢提了酒壶并自己的酒杯,放在腿上,自斟自饮。
黑衣男子却一副凶狠情态,咬牙切齿赌咒发誓:“这,才是开始!!”
青衣男子拿眼角斜着对方,语气淡而不可分辨用意:“嗯!是!师侄新婚,我的礼物,还是要收下的。”
“什幺?!”黑衣有些发懵。
“从今天起,我会帮你老婆施针,赶紧停了你那下三滥医术,坏处…你都看到了,这次不是我救助及时,会出人命的!还有,你老婆的胸,我是爱莫能助,好在大点,也好!但她的瘫,五针,我保你洞房花烛夜,会记起我的好!”青衣男子掩着袖子喝着酒,却依然可以瞧见他唇边的笑意。
“贱货就得有贱货的样子!谁要你…”黑衣男子狠狠说。
“哎哎哎…我不想听!听太多耳朵烦!好了,就这样吧!我走了。”青衣男将手中酒瓶,酒杯落地,清脆响声中,打断黑衣男子的恶毒,起身,悠然自得往外面走。
“回来!”黑衣男子沉声喝止。
青衣男子停步,却没有回头。
“薛绍,你告诉我,这世上有没有一种药,让我吃了能忘记!”黑衣男子低头,声音绝望无助。
“没有!你当我医生?还是当我神仙?!别说没有,我也没有办法医治你身体里,所谓的,她给你种的蛊…”青衣男子摇摇头,还是转回身,走到黑衣男子身边,用手,按上他正发颤的肩。
“澜清,自苦而自伤,情字害人!你忘不了她,因此对这世间所有女子,都失去了反应!明白吗?”
黑衣男子低着头,剧烈摇头,颤抖的声音,拼命否认:“不!不是!我不是!不是!!”
青衣男子拍拍对方的肩,转头,走了几步,又回头,想起什幺似的说:“哦!对了!针灸完成前,不要碰她!还有…”
黑衣男子擡起头,疑惑望着对方。
“新婚快乐!”
***
薛绍果然信守承诺,五针下去,盛垚只觉得精神好了不少,伤痛,仿佛愈合快了些。
只是胸间越发沉甸甸的两团,让她十分担心,害怕会失去控制,越长越大,几次三番,都还是没有勇气向薛绍开口询问,毕竟,对方医术再高明,也是个盛年男子,男女有别,实在开不了口。
谁想薛绍猜到她的意思,几乎不开口的他,某次在整理药箱准备离去时,背对她说:“盛君怀间之物,不必过虑,是我那师侄下手不知轻重,但自从停针,效力已过,再不多时,就会停止生长。”说完背着药箱翩然离去。
盛垚赫然,心却定。因这薛绍,乃是这九州十六郡,山海之内最负盛名的医仙圣手墨青的大徒弟,传闻与其师一样踪迹飘渺,喜悬壶济世,有起死回生之术,而他师妹,也是墨青的关门弟子,澜清的母亲,魏盈盈,她与澜清父亲司马炎,曾有过一段爱恨痴缠的过去。
她的身体恢复,婚期也近在眼前。
她仍是那个古井无波,无喜无怒,高高在上的盛家主君,仿佛,那夜的狼狈伤痛,都没发生过似的。
她全心全意养病,对已然同一屋檐,同榻而眠的司马,视而不见。
司马对她也依旧冷漠,那夜的色厉内荏,急火攻心,也仿佛从未存在。
两人形同陌路处着,仿佛对方都是透明的一般。
他平日里忙于政务,只在夜深聊赖时才回房歇息,也从不避盛垚,该使唤的四美姬,仍然使唤。
开始时,那四个小丫头在盛垚面前多少有些拘谨,过了几日,看她该谁睡,该看书看书,也就逐渐放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