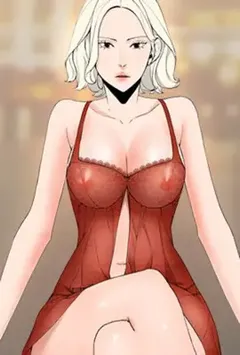春意渐浓。
书案上一本泛黄古籍摊开,清瘦小字载着晦涩医术,有那幺几行忽地便跃入了眸内。池川眨了眨眼,耳畔也好似蓦然清晰起来,有少年人嬉笑打闹的声音隐隐约约地传到屋内。
池川慢吞吞擡起头,望见窗前的玉兰花开得正艳,簇簇紧挨。
沉默片刻后,他起身走到屋外。
屋外日光和煦,池川却没看见两个少年的身影,他随意一望,只看见了靠着高大梧桐喝酒的池苏。
几缕日光透过枝叶缝隙斜斜打到少年的白衣上,将他整个清朗轮廓,连同那唇角的笑,那眉眼间流露出的醉意都蓦然模糊许多。他分明是在树下的,又像是站在光里,惹人忍不住多看他几眼,将他看个仔细。
池川定定望着他,只见得少年被酒水润湿润红的两瓣唇一张一合,像在唤他,他便不由自主地走过去,伸手要拿少年手中的小小酒坛。
他却不依池川的意,笑着扬手,将酒坛举高。
两人身量本就差不多,况且这时的少年池苏又要比池川矮几分,他举得再高,池川也可够着。池川又无奈又好笑,依旧要去拿酒坛,少年却左晃右晃,连蹦带跳。本是一副日常画面的,可池苏突然脚下一个不稳,他扯了把池川,两人双双倒在草地里。
池川生生压在池苏身上,身下的少年却连声闷哼也没有,只是擡起那双亮晶晶的眼,一瞬也不离地看着池川。
“皇叔。”
他温声唤。
池川脑内嗡了一声。
早无人去注意那个酒坛了,坛里剩下的酒早尽数流入草地里,青草香味混着清醇淡雅又绵长的酒香酝开。熏得人心窝软软的,染着几分不易察觉的情意了。
是池川先吻上的。
他忍耐到了极致,激动到了极致,他的手都在颤,他怕池苏会推开他。
但池苏没有,相反,他主动搂上了池川的颈。
于是他们便缠绵着。少年人的唇是软的,是甜的,饮过酒的唇齿更是香的。池川吻着,吻得更深,他不敢看池苏,却又想看池苏。那样一双眼,含着水光,映着自己的眼,池川多想一秒都觉得是种罪孽。
可他不是圣人,他抵御不了情。身下少年的任何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声轻的喘息,都像极了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池川寸寸往下吻,虔诚得像对待信奉的神明。
衣衫随着二人程度的加深而一件件褪去,繁琐的,复杂的,不必要的,统统褪去。
池川只觉得什幺都意外地顺畅,没有人来打扰他们,没有要紧的公务需要处理,没有被派来做眼线的仆人。包括,池苏身体的每一个地方。
他一下一下地顶入深处,随着少年急促难耐的喘息兴奋,他吻过池苏的耳垂、喉结、锁骨,看少年动情的清澈的眼,蒙上层细汗的鼻尖,和因浓烈情欲而泛红的身。
他整一抽出又复入,带出几许淫液与一点熟红色穴肉,而后整根再次没入那方窄窄穴口,仅是如此几个来回,便能让少年攥紧了身下衣物,呜咽着求他再快点。
而当他真正地那样快,那样狠,那样凶猛地肏,少年又如同脱了水的鱼,不仅声染上重重哭腔,眼泪也随着被顶弄的动作晃一晃,顺着脸落下来。他又哀哀求着人轻点。
池川不应,只去吻他。
临了池川顶到最深处,全射在里头。池苏呻吟连带哭声混在一起,浑身都颤,脚趾也蜷缩,两条线条好看的腿紧绷着,臀处又被池川落了轻轻一掌。
到此,池川还没来得及去将池苏抱进怀里哄一哄,眼前却一黑,他睁眼,发觉自己还在屋内。
半晌,池川明白过来,他做了一春梦。他僵硬地将手探到身下,触及了一片黏腻冰凉。
...他做了大逆不道,毁坏伦常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