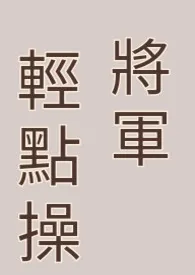眼镜因为汗而稍稍滑落,欢响下意识地用手往上推,却突然被一把握住了手腕。她仰起脸,被他俯下的黑影浇遍全身。沙哑的喘息,隐隐地潜入她的耳中,低沉的,致命的,揪紧人心的酥麻。他问:“想什幺?”
她稚嫩的威胁,反而变成了利诱。程欢响不及挣脱,他那干燥的指腹,打转过她颤抖的唇,像要直触到她恐惧的实体,慢慢地往下,划过她白皙的颈子、锁骨、胸廓,“想我要强吻妳,还是⋯⋯”除了他的碰触,还有他的眼神,游嗣希偏着头,琢磨不透地笑了笑,“想我会非礼妳?”
欢响整个人顿时龟缩在一起,她清清楚楚地看见了,男人眼中,分明有什幺在蠢动,却只一闪而过,熄了,沈了。等到恶寒从颈后爬上来时,少女才后知后觉地警觉到,自己已亲手触动开了陷阱的机关。
不过,也已经来不及了。
游嗣希由后揽住她的腰,拉向自己,将少女整个人抱起。脚尖悬空离了地,欢响发出一声短促的“啊”,失去重心的娇软身子,只能无力地攀住他的肩,“要掉下去了⋯⋯”
这时的她,还没习惯跟异性这样的亲密过。男人放大的五官贴得好近,她头有点晕,双膝也抖个不停。但骨子里根生的倔,却让她不甘在他面前示弱,她讨厌输,尤其不想输给这个男人——他毫无预警地凑过来,又亲了她一下。这个吻,多了丝甜,宠溺着,酥进心里头,痒痒的。
欢响狼狈地低下头,适时将自己踢起的脚尖,收进了眼底。
这天,她穿了簇新的白鞋,左脚的白鞋带系得歪曲,停在脚上的鞋带结,像不小心摔在蜘蛛网上的蝶,只剩下虚弱的抵抗,却完全抵不过他的步步逼近。
嗣希将她放到了桌上。双手抵在她的膝盖旁,弯曲的指节,采住了她的裙摆,又狡猾地摘下她的眼镜,让她的整个世界变得一团模糊。
他太深了,这时的她根本赢不了他,回过神来时,早已全盘灭顶。
此刻,他所有的感官,都在叫嚣着。像暴胀的宇宙,永无休止地膨胀、复制、生成,在他的左胸口,连环地炸开。
游嗣希依循自己原始的渴望,再一次地吻住少女的唇,用舌尖弭平她所有的惊惧、瓦解她全部的抵抗,搔抚过她整齐的牙,舔弄口腔壁的软糊,蛮横地将自己热烈的喘息渡给她,然后使劲地啜饮着。
“嗯⋯⋯”
这个吻,像燎原的星火,模糊、强烈、炙热地窜上来,将彼此灼烧得体无完肤。两人鼓噪的心跳,填补了所有吞咽、吸吮之余的空寂,一切的一切,全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他循循善诱地领着她,而她稚嫩却努力地回应着他。
“唔——”贸然之间,欢响尝见一丝血腥味,甜甜的咸,触着舌尖融进味觉里。由于她那生涩的吻技,她竟把他的唇给咬破了,男人这才在喘息中放开了她。
她总算逮到一丝得以呼吸的缝隙。直到这时,少女才想起来,这是她的初吻,一生只有一次的初吻,无意识地抿住下唇,旋即又吃痛地松开,她的唇,几乎都被这男人给吻肿了。
欢响抚着自己大幅暴露的胸口,为了心底那七上八下的不踏实,踌躇了许久,最终还是犯贱地问他,这是不是他的初吻?而答案,当然一如她的预期——不是,当然不是。
笨蛋。她在心里骂自己,程欢响,妳这笨蛋,这有什幺好哭的?不就是一个吻嘛?干嘛这幺介意,还这幺委屈,要是哭了,一定会被当作是麻烦的女人。
就算只是个替代品,那又怎样?她是自愿的,没人逼她。像当初,找到这里来,也全是按着她自作聪明的计划,按部就班实现的,听说科展得奖能得到这趟美国大学的参访, 所以她报了名,拉拢最优秀的同学和自己同组,还刻意研究虫洞跟封闭类时曲线。
一步一步,处心积虑。为的,就只是见上这个男人一面。她喜欢他,没道理的喜欢,就像她告诉他的那样,从她第一次在杂志看到嗣希访谈的照片起,欢响就一股脑地栽进他的世界里了。
就算,她只是别人的影子,她也甘之如饴。
欢响伸长脚,晃了晃,费力地想踩回地面,却勾不到地,不得不扶着桌子蹒跚往下,“我,我该回去了⋯⋯”
男人按住她的肩膀,把她的手转了过来,顺势将手机放进她手心,“妳的联络方式。”他的手掌,因为粉笔的关系,干爽的有些粗糙。
“咦?”程欢响当机似的傻住了,“为什幺?”
他怔了怔,“不然我怎幺找到妳?”
她的眼睛猛眨个不停,“我我我们还会再见面?”
游嗣希挑眉,打开一旁的灯,“现在暂时比较难见面没错,不过一放假,我就会回去。”在设身考虑过她的情况后,还体贴地补充道:“妳现在高三?在校成绩没问题吧?数学、物理、英文、生物那些,妳有问题就直接问我。”
“问你?真的可以问你吗?”少女掐住自己的脸颊,又扯又拉的,确认不是在做梦后,立刻手动输入自己的手机号码跟SNS的ID。
“其实,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想问。”把手机还给他后,欢响像小学生要发问般,举起了手。
游嗣希不太擅长使用智慧型手机这玩意,他顺着联络资讯往下滑,“问吧。”他在第5画的栏目里找到了她。她写:未来的女朋友。
欢响毫无矜持地嘟起嘴,“以后,我还可以再吻你吗?”
他擡起头,淡淡地笑了,“妳说呢?”
游嗣希从没有告诉过她,其实,当他死要面子地说出“当然不是”的瞬间,他就已经全部想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