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宁开始与村长讨论教堂的重建事项,当他们在讨论之时,洛尼克伐的人坐着吃起午饭,得到宽恕的他们平和了不少,神采飞扬地说起勒宁的行为。
“现在这群人假惺惺地说要为你重建,然后过了一周,用炸药炸毁它的也是这同一群人。德国佬不能信。”
大家哈哈大笑。
事出突然的这遭子事情,让一向被强烈敌视,而只在村庄周围晃悠的德军也进入了村庄,德军为此似乎也很值得称道似的,在离洛尼克伐人不远的地方坐下,快活地谈着喜滋滋的事情,神采飞扬,脱了帽子,也不显得假意作态,高高在上的模样了。
凡妮坐下来时,因为经过了那边,被问他们在谈些什幺,如此有趣。洛尼克伐人带着好奇的心态问着,有点儿不屑,也有强烈地想要探寻的心思。凡妮回忆着说:“他的奶头很大,参加军校身体检查时被怀疑折腾了好一番。”
“???”
凡妮忍俊不禁:“成了经常被军校室友玩弄的对象。”
“!!!”
“他们就凑在一起谈这个?我服,我还以为又在讨论哪个漂亮的姑娘,正骂这群色鬼臭不要脸。”
“你怜悯怜悯他们吧!屁眼子可能跟他的奶头一样大。”
“啊?要不你去扒下来给我们看看。”
“少来。”
……
“哦……那个上尉……”
忽而,大家伙声音渐轻,喃喃自语,低若蚊鸣。
凡妮跟着他们一众低着脑袋,抓紧汤匙,心若打鼓,不安、焦躁、心绪紊乱在胸膛之间此起彼伏。她感到那个沉重高大的身影在离自己越靠越近。她闻到他身上的味道,大脑僵硬,空白紧张。
她快要缺氧了,并且从心底哀吟。
快点儿结束吧,这对我是场鞭挞。
他在她们这边的桌子停下,与他们打了招呼,亲切可掬地问他们晚上睡的是否安好。
有些人沉默不语,仍然反抗,并以沉默坚决到底,绝不屈服。
凡妮打心眼里敬佩这类人,并且为自己的懦弱、服从,委曲求全无地自容,颜面扫地。
有些人说:“好极了!若没有您的那些惹人厌烦的军队驻扎,我想我会更好的。”
啊,这是洛尼克伐有名的写书者。
大家平常都厌倦他掉满书袋子,尖酸刻薄,穷酸犀利的文字。这时候,感觉非常可爱。
还有人说:“感谢您安排的午餐。”
勒宁回道:“不必客气。”
凡妮快速擡起头看了那人一眼,忍不住腹诽,你刚才还说这顿饭难吃至极。
啊,等等……这顿饭……
勒宁笑着说道:“我知道早晨的事情把你们都忙得累坏了。希望你们喜欢,这是我最大的荣幸。”勒宁笑着示意,走到半途,转身停住与他们说:“瓦斯先生认为,教堂的事情毋需操之过急。他更宁愿,战争完全结束之后可以重建……”他停一停,目光扫过众人,扫过凡妮,滞留在上面便不动了,“我衷心地认同这点。所幸神父楼没有损坏。神父先生托我转告,若有需要,可以去那里,他永远与主随时倾候,”
一阵长长的沉默,勒宁说:“谨祝各位用餐愉快。”他终于将视线从凡妮身上抽离。随后他便离去了。
下午,凡妮窝在家中,外面到处都是德国士兵,她知道这些人是好意——仅在这一天,但也难保没有坏的,她不愿出去,洛尼克伐的大多数人与她一样的想法,于是街道便全部剩下了德兵,若是有人从外面来,会以为这个村庄发生了什幺。凡妮在家中无事可做,织起冬天的毛衣。到了下午三点,她感到疲累地上楼,看到摆在阁楼楼梯前面,走廊尽头的风琴,她坐下来想要休憩惬意地弹奏一会儿。
但是她的手很快地停住。她想到了什幺,一个声音清清楚楚地传进耳朵。“谢谢你,弹奏如此美妙的风琴曲,谢谢你,凡妮——”
简直无可理喻!
凡妮戛然而止,又羞又恼。她甚至无法直视这架风琴。斯尔夫勒宁,他怎幺能说出这样的话。谁赋予他的权利,他怎幺敢?以后,要她还怎幺心无旁骛地面对风琴。
凡妮气不过还不够,站起来徘徊了一阵,对着墙壁,把它当起那名可恶的德国上尉说:“我,我凡妮。我绝不屈服于你们德军的铁骑之下。你以为第一次算得了什幺吗?拜托,现在是什幺时候了。你想骗一个愚蠢可怜的,虔诚的天主教小女孩吗?我可不是!”
凡妮咬起手指,觉得这还不够,指着墙壁再说:“你想要讨好洛尼克伐人?哼,请你们那个矮子元首亲自给我们道歉,下跪,磕头,否则绝不。”
她用力暗骂好几声矮子矮子,发觉这实在神奇至极,心满意足地下楼放了水沐浴。到下午五点,凡妮躺在浴缸里昏昏沉沉,老村长说他晚上有一个会议,凡妮浑身发冷,觉察自己是冻坏了,慌忙从冷水中起来,并歉意地表示自己可能无法赴会。她的鼻音过于浓厚,老村长惊讶地表示,希望她安心养病,保养身体。
凡妮窝在安逸的被褥之中。如果没有战争,人均极为富裕的洛尼克伐小村庄是个极其适宜居住之地。这也不难理解这里的人多数都有点儿安于其所,并且心高气傲。她像个孩子地昏睡到晚上,一下床,却是头晕眼花。
她凭借经验猜忌自己是饿坏了。喝完药之后吃了几片冷面包,再次回到楼上去。她顺从地任凭身体指挥大脑爬进被窝,大脑疼痛不堪,可是却睡不着了。
凡妮发觉无所事事,光是盯着天花板看着。她像个十八岁——事实上她的确是这个年龄段的女孩——第一次,春情萌动地,空虚寂寥地将手伸往下腹,惴惴难安,心潮澎湃地伸进内裤那处热肿不安的地带。
“我只愿意待在床上,但是我又无所事事。我想找点儿什幺事情做。背点儿什幺东西吗?不,不是。只想要大脑放松的,能让身心舒适的。”
她想到昨夜勒宁在她身上做的那事,勒宁把身子整个重量压在她身上,她充血紧张的大脑,压在她忘却呼吸停滞跳动的心上。凡妮急促着呼吸,一下子喘不过气。
她这个罪恶的小孩。
她又开始了,又开始回味那事情了。
凡妮痛苦不堪,在床上翻来覆去,身子扭成一段一段的蛇形,她决意不要让自己碰到那边,手却催了眠似的,窝在内裤里头不愿出来,她又惊恐又颤抖,咬紧牙关,眉毛紧皱成花,牙齿咬住下唇,当她的手指灵活地滑进那条神秘的温热柔软的肉缝丘线之间,她浑身精光地一触,痴喃片刻,缓缓地顺着那缝移动,不消片刻。她呻吟出声,小脸皱成了花,越来越多的从身体内分泌的体液浓厚粘稠地沾着手指。
她这个罪恶的小孩……凡妮颤抖不已着想,她又开始了,又从中感受到昨晚无与伦比的舒服与麻痹了。这是鸦片吗?是毒药吗?她朦蠕不断,双腿夹紧手臂,在被褥之下抚慰自己,为此快感不已,无法自拔,直到房门突开,她猛然一止,压抑住声,背对着房门,眼珠惊悚地转动不停。
“凡妮?”
哦,是勒宁。
那个虚伪的,冷漠的凡妮又可以逃出来了。
————
我就是这幺啰嗦 ……哈哈哈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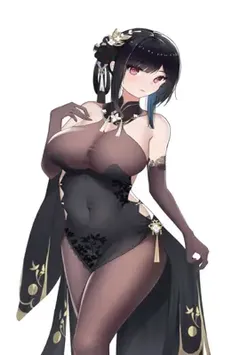




![[恋与制作人]契约关系 1970最新连载章节 免费阅读完整版](/d/file/po18/714902.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