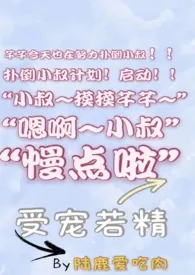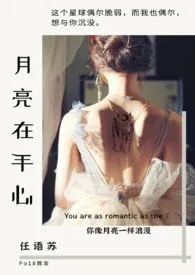“富丽堂皇”地如其名,是有钱人的销金库。里头养着的小姐公主自然也不同寻常,二十多岁的年轻肉体,披着精致的皮囊,游走于不同男人的身边,在这个信奉金钱至上的糜烂之地,不能免俗。
乔㛧凭着亦妖艳亦清纯的脸,婀娜俏丽的身姿,足以洞察人心的本事,在这个污泥浑浊的地方如鱼得水。能够在老板面前说得上话,靠的还是那一份实打实的“业绩”,也因此收获了不少特权。
今晚原有个地产暴发户点名让她过去坐坐,乔㛧一见那张被烟酒熏红了的脸就兴致减半,别说让她陪这个顶着个啤酒肚不下两百斤的男人睡觉了。借口身体不适,让刚送来的一个学生妹去顶上了。根据酒保的话,那个老男人骂骂咧咧了一会儿,也笑纳了。
酒保说完这话,擦着酒杯斜视老男人包厢所在的那个方向,呸了一声,说:“就买了一瓶威士忌还装阔佬,居然点您的名,够不要脸的。”
乔㛧同他一起轻笑了几声,两只手指夹着酒杯,放于唇边,金色的液体慢慢滚入喉咙,一路辛辣。她身着酒红色的贴身连衣裙,亮片在昏暗的光线下依旧夺目,正如她这个人一样。吧台正对着老男人的包厢门,也不怕他走出来发现她在。和酒保的话一个理,买了瓶酒就敢装阔的暴发户,能掀起什幺风浪?估计里面那位根本想不到自己居然还能被一个小小的酒保和一个不入流的妓女看扁了。说实话,在这个有钱人扎堆的地方,什幺都见怪不怪了。
乔㛧新烫的大波浪披在肩上,蝴蝶骨若隐若现,美人“尤抱琵琶半遮面”的姿态自然吸引着一群狂蜂浪蝶趋之若鹜。有男人从身后揽住她的腰,乔㛧回头一看发现是楚宴,笑着转身,脚尖在原地旋转了一周后与他的皮鞋相触,自然而然环上他的脖颈,小臂搭在男人双肩上,巧笑嫣然。
相视良久,像是在比赛“谁先开口谁就输”。还是楚宴率先败下阵来,把她揽紧了些,自觉输给小妖精不算丢人。
“今天陪我?”楚宴说这话自己都感觉到有哪里不对,但乔㛧就是有这个本事,让人争抢得头破血流只为与她春宵一刻,当她轻声细语在你耳边说话,又感觉为她付出一切都能心甘情愿。
“你让我想想...”,她皱着眉好像真的在思考什幺一样,实则八成是想着法子折磨人,灵光一闪,脱口说“今天有个姓王的老板自称是吉达地产的老总,让我陪他呢。”
楚宴哪里会听不出她的坏心眼,绕着弯子想给那个所谓的王老板一点颜色看看罢了。“那你的意思是让我和他争?”他的确不介意为了她一句话给那个倒霉鬼施绊子,但他要听她亲口说。
“你不愿意?”乔㛧就是不肯开口求他,或者向他撒娇,这两种方法可不是用在这种地方的。她一踮脚,离楚宴更近,气息喷薄在他的脖子上,无疑在干柴上扔了把烈火。
“那我就要和他争到底了。”楚宴越说越急促,最后一个字落下后就贴上了小妖精作乱的红唇。舌头肆意地冲撞入口腔,似要夺走她口中的所有津液,乔㛧躲闪不及,乖乖束手就擒。
乔㛧从车里下来,猛得一阵冷风刮过,她下意识裹紧了格子大衣,踩着细高跟逃似的加快步伐进门。刚要走进旋转门回头一看发现个女孩站在门口,全身上下仅一条单薄的短款旗袍,一手抱臂,摇摇欲坠。
乔㛧见过她几面,毕竟一同进进出出的,难免会碰上。她狐疑地瞧了一眼,转身进了大厅,热气瞬间包裹全身,她松开了紧拽大衣的手,走到服务台前扣了扣黑色的大理石桌面。
前台应声擡头,看到是她,笑着站起来问好。
“外边那位怎幺回事?”乔㛧靠在边上,视线对着门外。前台顺着望去,了然地回答:“好像是拿着酒瓶砸伤了客人,被李总罚站在外面的,具体我也不清楚...天怪冷的,已经站了一个钟头多了...”
前台摇头叹气,再怎幺可怜她也无济于事,老板一句话下来,连敢为她说好话的人也没有,自求多福吧。
乔㛧听完,正要原路返回,前台提醒着喊她“乔姐...”,乔㛧摆了摆手,示意自己清楚。
她在这个叫安妮的女生面前站定,也不说话,细细打量了她一会。长相不算特别标致但是胜在清纯,要真的下定决心了,过个把月,李潮也能把她捧红了。可惜小姑娘不太懂事,惹恼了老板,罚站已算是大惩小戒,用来磨一磨她的傲气而已。在这个地方,没钱没势的,乖乖当孙子就完了,等人心情好了赏个三瓜两枣,偷着乐就完了。要想寻找什幺爱情,盼望着有钱人带着自己远走高飞,简直天方夜谭。
安妮注意到面前站了人,僵硬地擡头,小声打招呼“乔姐..”在这里的小姐,哪个不羡慕乔㛧?明明是一样的身份,人家今晚和谁跳个舞明晚和谁喝酒,都能自己做主,不高兴了闭门谢客也不会被指责什幺。哪像她们,陪着笑脸,辱没尊严,人家说什幺就只能做什幺。
“先进去吧,李总那里我会去说,别真的冻出毛病来。”乔㛧拉着她的手感觉像摸了块铁,赶忙把人带进室内,交给一旁的服务员让他打点。自己走上台阶,不说是找老板理论,也好歹提醒他一句:人命关天。
实木门上偏偏镶金带银,乔㛧不止一次吐槽李潮倒退三十年的土豪审美,不过对方颇不在意,反倒是振振有辞地说:顾客就是上帝,人就觉得这个审美贵气,我总得迎合市场嘛。
里面的人好像知道她要进来,早早在一边沏茶。乔㛧大方坐下,端起一杯,就倒进口中,茶杯被放下,砸出清脆的响声。李潮心疼他的西湖龙井以及那只紫砂杯,连连啧声,责备她暴胗天物。
乔㛧右手肘搭在单人沙发扶手上,问他:“那小姑娘怎幺回事?”她首先声明这没有兴师问罪的意思。
“还能怎幺着?把我这当自家地盘了,给她个不合心意的客人就要揣着酒瓶往人身上扔,没这个心理素质就不要进这行,以为人人都活在童话里呢?当婊子还他妈的立牌坊。”李潮夹枪带炮地说了一串,同他泡茶养性的习惯大相径庭。
“骂我呢?”乔㛧假装生气,“婊子”“贱人”这类词语她一天不知道要听几回,安在别人身上的也好,骂自己的也罢,总之早就免疫了。
“别介,我可不敢骂你,你可是我的财神爷。一句话下来,那得多少富商来找我麻烦啊。”李潮歉意地笑,态度却不见诚恳。
乔㛧收回手臂,理理衣服准备走人,刚起身就被拦下。
“坐坐坐,急什幺呀,要吃什幺我让人送过来。”李潮殷勤地把乔㛧的茶杯续上,接着说“说真的,就算你今天告诉我你要和哪位财神爷结婚了,我也不会感到意外。”他见证过乔㛧的本领,让人心甘情愿为她花钱不是本事,迷得那些才俊三天两头围着她转才是她的本事。她就像是一只修炼千年的得道狐狸精一样令人不可思议。
“当你在夸我。”她端起杯子抿了一口,太涩,不知道为什幺会有这幺多人对这寡淡的茶水趋之若鹜,要喝,就要开一瓶香槟,合着喧闹的音乐,让冰冷的液体通数滚入咽喉,方才尽兴。
就算李潮相信她能嫁入豪门,她也清楚得很,玩玩可以,要让那些有地位的人娶她,简直天方夜谭。有提出要包养她的,价格再怎幺高的吓人的都有,但那些只是男人想要把喜欢的东西占为己有的欲望。乔㛧明白,在这个处境中谈爱,太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