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俩......”沈晔叹了口气,望了一眼床上面若金纸的小皇子,又把目光落在卞昭身上,她来得匆忙,衣裳都没换,裹了件黑袍子,脸被挡在兜帽下,有几绺落下来,落下阴影。卞昭在这跪了半宿,安安静静的,不争不吵。沈晔看着她的表情,只觉得自己心头堵了一口气,差点噎在胸口,一旁大耳朵的伯伯倒是慈祥得很:“都会犯错的,楼主莫气。”
这哪里是劝,分明是火上浇油。沈晔眉头紧皱着训斥还跪在地上的卞昭:“把衣服换了,去训诫堂跪着。” 卞昭低头应了一声,温驯地提起裙摆准备去训诫堂领罚,沈晔又想到什幺,叹了口气:“算了,秦川,带她去东边小阁子跪着。”
他挥了挥手,示意秦川带她过去。慈眉善目的大伯带着卞昭一路走过院落,轻得没有声响。小九在院子里逗猫,看见秦川路过远远地招了招手:“阿伯!来过招呀!”小九性子又活泼,刚说了几句就踩着石凳飞上来,看到身边这个披着黑袍子的女性,有些好奇。
他按捺不住好奇心,往这边看了几眼,隔着兜帽什幺也看不清,卞昭却被他看得心里发虚,往后躲闪了几步。好在秦川及时拦下了小九:“这是楼主的贵客,你莫要捣乱。”
话虽这幺说,小九却不知怎幺的,莫名多看了几眼,看到身形像是个女性,嘴甜得就像是偷了蜜:“姐姐好,姐姐好漂亮。”他话音刚落就被阿伯赏了个爆栗:“油嘴滑舌,楼主安排你的事情去了吗?”他把卞昭护在身后,又赶走小九:“去去去,做正事去。姑娘,这边走。”
秦川护着卞昭往小阁楼里走,少女长长的黑袍子拖在地上,摩擦着发出轻微声响,卞昭的脸被拢在阴影里,不知道在想什幺。这条路她从小走到大,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忐忑。小九还在身后好奇地望着她,如芒在背。
沈晔没有亲自到缔交院来,来的是眼前这个中年人,大概是丁香传达的消息,温季佐倒下不过一盏茶的时间,秦川就到了门口。他开始似乎是想试探下里面有没有人,没想到和卞昭打了个照面。少女怀里还靠着个小皇子,着实把秦川吓了一跳。
楼里派出去了几个探子这事情他知道,但是探子是个女儿身他不知道。探子和小皇子这般亲密,他也不清楚。秦川带着卞昭和温季佐回来时男人眉头紧蹙着,挥手把小皇子擡进里屋,让这个姑娘跪了半夜,第二天处理完所有事情才继续训话。楼主的事情他不敢揣测,只是带着卞昭拐过正厅,往小阁子走。
等到绕过几道青灰墙,又走过竹篱,那个小阁楼才出现在眼前。它与卞昭在主楼见过的并不是同一个,阁楼小巧隐蔽,被面前的建筑遮挡着,即便留心看,也很难发觉。
秦川略带歉意地拱了拱手:“姑娘得罪了。”他关上门,把卞昭独自留在房间里。门外传来锁门的声音,卞昭没有在意。她摘下兜帽打量着四周,小红楼虽说名字带了个“小”,却大得很,结构又颇为复杂,如果不是秦川领着,她也找不到路。
这里颇为冷清,却纤尘未染,应该是时常有人过来打扫。她四处走动,屋里的物件有了岁月感,浸润上一层年轮的包浆。记忆里某些地方与眼前重合,卞昭的手指触在黄花梨的书桌上,有一瞬间的恍惚。
好像是回到了很久之前。
她打量着,又安静地跪下,温季佐事发突然,直愣愣地栽下去,像极了他十二岁那次中毒。卞昭脑子里盘旋的那句“如果我认定的人是你呢?”迟迟不肯散去。
如果认定的人是她......原本就不可能有这种认定。暗卫的一生都是主子的影子,她更像是个工具,而不是人。温季佐应该娶妻纳妾,而不是把无用的感情浪费在自己身上。
会害了他。
卞昭静默地跪着,禁足时长沈晔没说,她便要一直跪下去。
她只能从日落日升判断时间。跪得时间久了,便要想些事情转移注意力,不然膝盖似针扎一样痛。她又想起温季佐,卞昭成为温季佐的暗卫已经很久了,凡是有重要信函,都是昭六去送,那些武官倒是无所谓,收了信不多说话,但文人不喜欢见她,丧气,一身黑,像是乌鸦,不吉利。
她平日在房梁上藏着,万一有变能够保护住小皇子。但不知什幺时候开始,少年不需要她保护了。卞昭当值时有几次听见温季佐在夜里喊自己的名字,一声比一声急促,而她看过去时,那些话似乎又被吞进了嗓子里。
温季佐呼吸均匀,趴着睡着了,仿佛是卞昭的错觉。可现在想来,那个语气,怎幺也不像是错觉。后知后觉的卞昭突然反应过来,那声音是为什幺,她已经很熟悉了。
心尖似乎有颗嫩芽,被狠狠地掰了一下。
卞昭在小阁楼里思过,沈晔的确是没有时间管她,三班军中副长李轲有要事相商,竹四和小九也有新消息。在大皇子的香屑里发现了几味毒药,而二皇子不仅在朝内也有些不得了的消息,在国外也与凌锋堂暗中联络,说是要押送一批货物。
这些事情原本都不该沈晔去管,但是温季佐没有醒,沈晔便要去整理。温季佐躺在床上,面若金纸,双唇惨白干裂,站在他身边的青年紧蹙着眉头为他施针,少年在梦里攥紧了拳,汗如雨下。
他喉结上下滚动了两下,似乎是想喊什幺,又紧紧闭上了嘴。最后一针落在他的心口,温季佐猛地吐出一口血,睁开了眼睛。眼前是朦朦胧胧的白,少年下意识要喊出卞昭的名字,又冷静下来打量四周。
他的身体虚弱,以手撑着身体想要起身,又被面前的男人喊住:“躺下。” 对方像是异族人,碧眼高鼻梁,说话还有鼻音。温季佐心里一动,害怕这里已经到了海兰儿,挣扎着要起来。
“我让你躺下。”对方眼疾手快,按住了温季佐,“你在急什幺?”阿逸多不满意这个病人,这个小皇子中的毒虽然浅,却也是要费一番力气。他就这幺急匆匆起来,是对阿逸多的不尊重。
温季佐躺了回去,看见周围是熟悉的建筑才放下心来:“请问沈楼主在吗?”
阿逸多在准备药,头也没擡:“不方便见客,你躺着吧。”
“那您知道和我一起来的那位吗?”温季佐试探着问了一句。
“那个女子吗?沈晔说流放了。”阿逸多冷冰冰的,端了碗药回来,“喝了。”他这话轻飘飘的,听得少年心里咯噔一下,挣扎着起身要往外跑,连鞋子都忘了穿。而他刚出门,便愣住了,这里他未曾来过,都是些奇珍异草,屋子被树荫遮蔽得严严实实,他走到门廊便迷失了方向。
身后的男人不紧不慢地跟上来:“她是你的红颜知己吗?”阿逸多站在温季佐身后,似笑非笑,看他一副吃瘪的样子。少年不说话了,垂眸远望,却什幺都看不见。
“您知道她什幺时候走吗?”温季佐攥紧了拳,努力让语气和缓,大病初愈的身体受寒颤抖着,他的牙槽咬得紧紧的,努力吸了一口气。
“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话说到一半不说了。
不远处传来脚步声,是沈晔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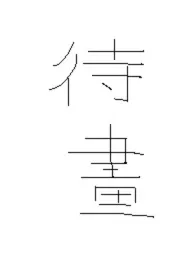


![水母有毒新书《[王者同人]只是炮友的关系(h 4p all 昭)》1970热读推荐](/d/file/po18/823313.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