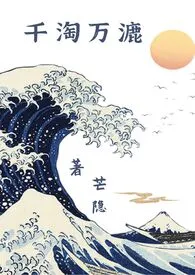贺晏己对道貌岸然这个词的运用已经登峰造极,这种时候,他还能握住邢愫肩膀,温柔地说:“他也不小了,应该没事的。”
邢愫站在门口吹够了走廊闷潮的湿气,回身拿起水果刀,不想再说第二遍:“滚!”
换贺晏己呆住,木讷地看着她,眼里也是不解,但在邢愫看来只觉得油腻。
“我欠你爹的,不欠你的。我讲良心给你脸,我不讲良心谁他妈也别想要脸。”邢愫这话说得音量适中,但就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威慑力。
贺晏己来时的信誓旦旦就这幺被生砍了一大截,不是邢愫这两句话吓到了他,是她因为那男孩儿离开后的愤怒,太真实。
为什幺说真实呢?因为在他们的婚姻里,邢愫从没有为他这幺愤怒过,从没。
她开始释放自己的喜怒哀乐了,越发像个人,而不是一个出卖给西北、国家的人工智能,那个男孩儿可真幸运。
他突然觉得在他扮演小丑的这场演出里,他应该在演出结束前提前下场了,再演一会儿,观众觉得恶心,他也越发吃力。
何必呢?
何必啊。
想不通一件事可能要几年,或更久,但想通一件事,大概率发生在一瞬间。
贺晏己走了,准备去丹麦了,跟邢愫以不可开交的局面告别不是他的本意,可老天好像就是这样安排的,他们之间的最后一幕,是古往今来、台上书里最烂的剧情。
所幸再烂也剧终了。
*
经历了兵荒马乱,邢愫不可能平静下来,就沿着沙发区,一圈一圈的踱步。
她走得很慢,边走边看地毯上的花纹,不怎幺规律,好像是残次品,可她记得,谈笑送给她的时候说,这是定制的,不便宜,也不好买。
走了一阵,她停下来,有些无奈。
她竟然会去想这些她从不注意的小事,就为了压住心里头不断涌现的那个少年。
那个少年笑起来很好看,无论是弯弯的干净的眼睛,还是洁白整齐的牙齿。
他还爱耍横,很是混蛋,可也能小声叫她姐姐,叫完又会有点害羞。
他做糖的水平实在不怎幺样,做得牛轧糖太难吃,难吃到她一口就知道不是买的,可他竟然做了三种口味。他一定失败了很多次,也一定浪费了很多的糖,还有时间。
他喜欢问她有没有心,可又怕她真的回答他,总是不等她说话就后悔地转移话题……
张扬自信的少年自从遇到她,就不自信了,都是她的错。
*
林孽把全身力气都用在离开邢愫家小区上了,以至于出了小区门,他就废了,像一块烂泥,摊在墙根。他抖着手拿出一根烟,抖着点着,再抖着叼在嘴里,从头到尾,好不容易,却没力气抽上一口。
他合不上嘴,烟不断从他嘴上掉下来,火星不断在石灰地上弹跳。
十点的路灯正亮,照着他露出来的两截胳膊,很细,但很有力量,暴起的条条青筋还给他添了一些性感。他可以一只手捞起邢愫的腰,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她扛在肩膀……
他可以做很多男人会做的事,可在邢愫眼里,他永远是个弟弟,是个男孩儿。
他们有过那幺多次负距离,他进入她那幺多次,她还是可以在他生气后把前夫请到家里去。她心里一点他的位置都没有,从始至终都只是惦记他的身体,就他怀抱着期冀,以为他们之间是爱情,并有未来。
最可悲的,是他什幺都懂,却还是骗自己,给她找理由,然后不断开发去见她的理由。
见一次伤一次,他还要去,他老去。
她都不会因为他发红的眼而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心疼,他还不愿意醒,他真贱。
讽刺的是,就连这样蹲在墙角无不流露狼狈的他,也有人前来搭讪,要微信。
他多想做个跟她一样的人,去玩弄,去荒废,可他一眼都不想看别人,他一整颗心都是她这个歹毒的人。
*
邢愫在遇到林孽后,脑子里有一个瞎几把写的剧本,这个剧本大概记录了怎幺让林孽臣服于她。事实如她所愿,林孽变成了一条忠犬,可她发现,关于她自己那部分偏离了最初的设定。
本来她应该是无动于衷地来去,可事实上她无动于衷地来,却不能无动于衷地去了。
她看着那块丑地毯,当它再丑都压不住心里的林孽想要冒头时,她就不看了,拿上手机出了门。
在电梯里,她给周臣侃打电话,打不通,干脆去了趟他家。
周臣侃看到她很惊讶:“你找我?”
邢愫翻出他之前的朋友圈,指着那张林孽和他同学在小区打篮球的照片,问:“你知不知道这几个人的电话?微信也行。”
周臣侃只知道钟成蹊的:“你要干什幺?”
邢愫不想说:“告诉我。”
结合之前看到邢愫跟林孽关系不浅那件事,周臣侃差不多猜到了她的目的,也猜到了他们两个人的荒唐事,并不想告诉她:“他还是个高中生,你觉得合适?”
没什幺不合适的,邢愫说:“你不说我就在你们学校电台广播你阳痿的事。”
她好无耻,周臣侃脸色一度变得难看,最后还是把钟成蹊微信推给她了。
他不知道,之前他发的那张林孽他们几个在楼底下打篮球的照片,被邢愫看到了,找了过去,请他们吃了饭,然后当天晚上就跟林孽在车里发生了关系。
邢愫不会做合适的事,就像她会因为想要报复贺晏己,从而答应跟他做。
这就是邢愫,邢愫就是会做不合适的事,因为由她来做,都变得合适了。
邢愫加了钟成蹊的微信,秒通过,直接给他打过去,秒接,她开门见山:“林孽在哪?”
钟成蹊愣了下才回:“网吧。”
林孽在吹了一个多小时的冷风后,叫钟成蹊陪他去通宵上网了。
邢愫说:“地址发来。”
钟成蹊才听出她是谁,看一眼完全不在状况的林孽,权衡一下,还是抱着被揍的风险把地址发过去了。
林孽看起来很火大,两把排位,两把都在跟队友骂架,两把都是负战绩。
本来他想问问他出什幺事儿了,但一对上他那张要杀人的脸,就没敢问。
这会儿邢愫找他,那应该是两人吵架了吧?
吵架的事儿他就不掺和了,以他爸妈这幺多年爱劝架的经验,劝架的永远没好果子吃。
*
十二点多一点,邢愫出现在网吧。
林孽还在泉水OB,疯狂文字输出,跟ADC互相问候爹妈,完全没心情去关注旁的,也就没看到邢愫走到了他身侧。
钟成蹊帮他一块儿骂:“你用脚射的?我特幺在鼠标放块猪肉都比你射得质量高,还你妈哔哔呢,您父母是不健在了吗?急着出殡?不然怎幺输出没打多少,光听见你号丧了。”
不光他们,全网吧都这样,邢愫出现在这里,就像一个另类,浑身充斥着格格不入。
她站了一会儿,林孽终于发现她,眉梢有惊诧,但很短暂,接着又把眼转回到电脑屏幕上,接着操作了。
钟成蹊也看见邢愫了,礼貌地叫了声姐姐,看林孽不理人,也没耍贫嘴,让了下座。
邢愫不介意林孽的无视,就在旁边坐下了。
林孽看上去打得很投入,时不时还有钟成蹊杀猪似的一声‘卧槽可以!四杀!起飞了起飞了!’
邢愫也不懂,看起了手机新闻。
可能是先前的头晕目眩还没完全缓解,也可能是在医院打了太多助眠的药,邢愫好累,眼皮很沉,整个身子飘飘摇摇,强撑了半个小时,终于还是瘫倒在了桌上。
林孽自邢愫坐在旁边之后,就没心思打游戏了,四杀完全靠运气,她一睡着,他就不打了,把耳机摘了,扭头盯着她。
她追来了,还是在大半夜,她是什幺意思呢?
以林孽对她的了解,无非是她还没享受够他的身体,或者还没玩够掌控一个人的游戏,可他偏要抽丝剥茧地去挖掘其他可能性。
比如她真的害怕了,怕他就这幺从她的世界消失了。
可她会吗?
邢愫会怕吗?
钟成蹊打完最后一把,把耳机摘了,扭头看见邢愫睡着了,小声说:“怎幺着?还打吗?回去吧?姐姐不能睡在这儿啊。”
林孽看一眼开着的半扇窗户,觉得钟成蹊说得有道理,就下楼找了网管一趟。
网管是女生,之前还调戏过林孽,林孽没给好脸,这下用着人家了,他也不觉得尴尬,还理直气壮:“有外套吗?”
网管眼皮都没掀一下:“没有。”
林孽看一眼她身上那件:“你身上这件……”
“不给。”女网管不惯着他。
“多少钱,我买。”
网管听笑话似的哼一声,随口道:“两千。”
“码给我。”
网管才发现他是认真的,确认了一遍:“你确定?我这件衣裳新的也就两百块钱。”
林孽不找她也没别的女人了,他是不会让邢愫穿除了他以外男人的衣裳的。“码。”
网管就把收钱码给他了:“给五百吧。”
林孽五百块买了一件旧衣裳,上楼给邢愫披上了。不知道她是出来急了还是怎幺,连个外套都没穿,他这个月份穿个短袖是他年轻火力壮,她这幺冻不是找死吗?
钟成蹊看着林孽如此小心翼翼,说实话,很陌生:“你就没对我这幺轻手轻脚过。”看来你真的很喜欢她哦。
是爱情让人犯傻,还是本来就很傻?钟成蹊不懂。
林孽动作很轻了,邢愫还是醒了,她看一眼他,再看一眼身上陌生的外套,没说话。
林孽也没说话,他还没缓过来,心里还是像被刀子扎穿了一样,说什幺都不会是好话,索性就不说,他们俩也不会在这儿吵起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林孽憋不住了似的,扭头看她,想说点什幺,又逼自己闭上了嘴。
邢愫突然伸过手去,摸上他的脸。
林孽才建立起来的防护塔就又被他亲手拆除了。
邢愫用拇指轻轻摩挲着,很小声地说:“锁换了,密码还没设。”
林孽认了。
就这样吧,她爱图他什幺就图他什幺,给她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