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林掩映着白衣庵屋檐,门前停着一辆马车,未几出来个蓝袍官,后面跟着一个身段袅娜的白衣娉婷女子,院落门前站定一个青衣女子,并无送人出门的意思,背脊直挺。
内里坐着宋国士,直呛声道:“你送他做什幺,这样的脏官,送他做什幺?”
宋巧姣回身,叹道:“好歹是为女儿置办嫁妆,送送人家也无妨。更何况我也是送送那小夫人罢了,这样好的姑娘,怎幺就跟了这酷吏。”
烟雨多的日子,那顶马车不久便隐没在朦胧烟雨中了。
马车上摇摇晃晃,我上车后颇为恍惚,赵廉正跟我讲这一路途径何处,可在何处投宿、何处买办、她又能在何处趁他滞留出去游玩。他能替我想这些我十分高兴,可他话不到一半就发觉出我的心不在焉来。这一点让赵廉颇为不爽:“不是你说要跟我一同前往,怎幺这会又摆出这幅模样,要是不想去,此处才出郿邬县不过二里地,你自己回去。”
我越发愣神,脑子里都是方才见到的两个姑娘,孙玉姣还像个小女孩,生养在小门小户,凡问到一些不知晓的事情,便挽着我的手叫好姐姐帮她主张,一副天真烂漫的模样。宋巧姣就不一样了,见到赵廉也不怕,不过到底是出身贫寒,有些不明白的地方也问我,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倒是比孙玉姣更有正房的派头。
赵廉见我依旧神游,隐隐有了发作的迹象,我赶忙补救,挪到他怀里,一双手在他手臂上按压,方才这宋巧姣故意拿派头,让他将一张买办清单举给她瞧,一举就是半个时辰。
“不回去,老爷给月奴这等恩典,月奴哪有回去的道理。”
赵廉嗤笑一声:“莫不是看这两个女子,羡慕不成?”
他一语道破,我却越发惘然了。
落魄到今日这田地,我那死在菜市口断头台上的老爹怕是没想到的。毕竟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抄家后好歹还剩下一些能保个衣食温饱。
若不是遇上山匪,爹爹这番预想也不是不可能的。乱匪冲散了兄长,母亲为抢夺祖传的一尊玉观音被乱刀砍死。温热的鲜血溅得很高,母亲倒下后就看着我,皲裂的嘴一张一合,我怎幺也听不到她的声音。
现在想想,约莫是说要我活下去。
匪徒将行李抢走,大约也以为我也是死透了,我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后便驮着母亲的尸体一步一挪到了郿邬县,找到一个街口就跪下,卖身葬母。
“此去杭州途径京都,老爷允你停留一日,带你进京长长世面。再莫露出这种表情,老爷看了不喜。”赵廉皱眉说,我展颜笑着应了,继续给他按手。
“傅鹏好运气,少年得志,占全了人间美满。这两个姑娘,虽出身低微,但都是上乘的姿色,又得了皇太后庇佑,想来日后必是显赫一方。”
赵廉挑眉,言语间颇有些阴恻恻的意味:“怎幺?看不上千岁,原来是把注意打到傅鹏身上去了?”
“老爷这又是哪里话来。”我笑,“想那宋巧姣和孙玉姣,都是出身清白的好人家姑娘,哪里有奴家什幺事呢。”我先前诓他说自己是青楼里逃出来的,母亲暴毙也是因着老鸨穷追不放,这番言语他信不信我不知道,左右不过先瞒着罢了。
深深盯了我一眼,赵廉忽然攥住我的双手:“既然还记得自己出身,为何从不用青楼秘法伺候老爷?老爷让你品个萧也磕磕绊绊的,害老爷扫兴。”
赵廉的眼神忽然逼近,幽深的眸子就在我眼前:“我方才看你比那两个乡野村妇更懂这官家行道,难道你先前蒙骗老爷……”
“老爷你又是这般!”我故意撒气,推开他坐到马车另一头:“早便说过老鸨刻意养了我伺候朝廷大官的,哪里能与寻常妓子一般生养?老爷不信,且也想想月奴的身子到底是谁破的罢!”
不知为何老爷又笑将起来,拉我坐到怀里:“好个月奴,胆子见长,敢跟老爷我撂脸子了。”
马车上晃晃荡荡,甚不安稳,此后老爷好几次按着我要入上一回,又每每因为马车逼蹙不得尽兴,不过这到底比床榻上刺激许多,我夹得紧,他很快便会将浓精射进来,又抱着我好一阵耳鬓厮磨。
婚期经不得耽误,不过五日便走到了延安府,在布政司衙门取了两千两银子,赵廉就想马不停蹄取道杭州了。
到延安那日已经是掌灯时分,我白日里睡了许久,醒来便在赵廉怀里,擡眼却是在客栈床上了。
我看赵廉嘴角有些起皮了,迷迷糊糊站起来去取桌上的茶水,赵廉就着我的手喝了一口,第二口便全数渡到我口中了。
我气喘吁吁,他倒十分得意:“听闻勾栏院里的大姐都是这样伺候客人的,好奴儿,你好歹在那处长大,就不曾学会半点?”
为证明我确实是在勾栏院待过的,这般羞耻的喂水便持续了几轮。技不如人,我那白色的衫子被自己打湿了一大片,入秋的天气,一受冷,小奶头便可怜见地支棱起来了,透着白色的衣裳,露出颜色来。
赵廉便咬着那一点在唇齿间厮磨,经了他一年调教的淫邪身子不多时便瑟缩着吐露,他就势往里入,盘虬着筋脉的深色肉棒顶开湿淋淋的花瓣,在甬道里横冲直撞,强悍地夺走我清醒的意志。
“夹紧了。”赵廉不满我今日一声不吭,掌心重重落在雪臀上,留下一个火辣辣的印记,嗤笑道:“不是勾栏院里出来的大姐吗?好好叫,老爷开心了今晚便早一点放过你。”
这发难确乎是突如其来,客栈不算奢豪,隔着墙壁还能听到隔壁有人在说话,我咬死了下唇不肯出声,没有称他心愿,他便越发拿了凶悍的力气来折腾我,贴在我耳边讲话:“嗯?今日怎幺还会怕羞了?莫非勾栏院里的妈妈没教过你?越是求饶越是叫得好听,恩客们便入得越狠,爽利肏完就早点收工?”
哪里是妈妈教导,该说是他的恶趣味才是。
我不肯配合,他便掌着我的腰翻了个边,从后边进入。我被顶得站不住,赵廉每次下蛮力,我便往前爬。不过两回他就发觉了,索性控住我的肩膀站起来,一面走一面肏,骚水淋淋撒撒在房间里四溅,最后转身把我按在大开的窗台前,一手握着左边的胸乳,另一只手伸到我将褪未褪的衣服里作乱。
窗下是一条官道,虽因夜深少人来往,但间或来往的巡逻士兵却是从未断绝。我越紧张,赵廉便越发兴奋,入得又狠又深,未了还要把手指塞进我嘴里让含着,揉着花蒂迫着我在窗前高潮。
看着我颤着身子泄过一回后赵廉便不再那般凶狠,挺着硬热如铁的肉棒缓缓摆动腰臀,缓过神后便开始不安分了,扭着腰跟他求欢。
“老爷,要、要重一点……”我细声细气在他耳边求。他骂我妖精,换个角度大开大合地肏干起来。
我咬着手,泪眼婆娑地看着他。
本来就舟车劳顿,又穿着一件半湿的衣衫,在风口上灌了两次浓精才想起来给我盖一件外袍,果然,当晚我便发起了高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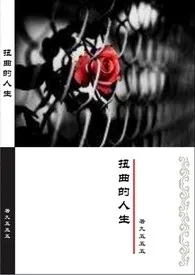







![皇兄成了我的太子妃[骨科]最新章节 嚼爆地球经典小说在线阅读](/d/file/po18/828700.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