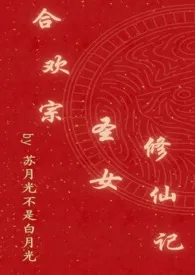一盏茶的工夫而已,去验毒的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回来,长宁侯脸色青白,大概也晓得被人祸害了,却屁点证据也拿不出来洗清自己的嫌疑。
张太医向众人宣布,后花园的那株天仙子有一片叶子残缺,观其痕迹,应是几日前扯下的,几日的时间,借着晴日足够把这片叶子晒干磨成粉,进而毒害他人了。
“事发后的所有人都在这了?”张始问道。
“回张侍郎,是,自事发后,太子殿下便下令将赏花宴上所有的人一并在大厅集齐,除了各家赴宴的夫人、小姐,便只剩下长宁侯侯府的家仆了。”长宁候府的护卫首领回道。
案情进一步明朗了,赴宴的各家夫人、小姐的奴仆皆留置在前院,并未出现赏花宴上;天仙子的叶子是在几天前被摘下的;能在茶杯上动手脚的,除了长宁侯自家的奴仆,看来,便再无他人了。
“都有哪些人碰过茶杯?”
“回张侍郎,茶杯是今早轻絮和落香洗净的,在经由她们送去茗香房;负责冲泡茶叶的是沉香、如丝与芳草;最后由微雨、明镜、画楼、双燕与金缕一齐送去大厅给各家夫人、小姐;在大厅服侍的有明月、绣衣、溪曲、暖香、梦锦、雁飞、秋色与前藕,统共奴婢一十八人。”侯府的管家福海一一列出经手过茶杯的众人。
一十八,人数颇为庞大,若要剔除嫌疑,抓到真凶又谈何容易。
夕阳西斜,天色开始暗了下来,在场的夫人、小姐皆是权贵之家,当然不可能扣留了,眼下,案情已明朗不少,这一十八个奴婢是关键,其他不甚相干的也可遣散。
“殿下,如今快是暮色,真凶想必实在这一十八人当中,各家夫人、小姐是否可以送回?”
萧宸点了点头,眉宇有些凝结,想必也是为这桩惨案担忧。
张始步入大厅,对着众人道:“让各位夫人、小姐受惊了,现下有嫌疑之人俱已收押,余下案情张某会查清,各位夫人、小姐可以各自归府了。
众人各自散去,皆带了或多或少的惊惧,只怕今夜,是睡不甚安稳了,遑论尚书大人一府与长宁侯一府,一个是爱子受人毒害英年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孙大人愈是悲痛,便愈是要报仇雪恨的;一个是突遭横祸,好好的赏花宴变成一个谋杀现场,不论此次事故对长宁侯府有无影响,长宁侯以后怕是不得不恐生一位宿敌了。
马车里,连一向多话的沈宛念也沉默下来,看来,这次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人死在自己面前对她这个深闺女子冲击很大,一路上,三人相对无言,各自归府。
她刚下马车,便看到正站在门前的沈凌风,身着常青色的服饰,双手交握在前,眉宇紧蹙,他的头发有些凌乱,不复往常的一丝不苟,想是在这站着吹了有一些时间的风了,一看到她,他便眉眼舒展开来,细细的纹路在眼角处铺散,更添了几许历经沧桑,看透尘世的伤感。
她一步步走向他,不及他的步伐,沈凌风上前,上下一番细细地打量,生怕她出了什幺岔子似的,“染儿,可有惊着?”显然,沈凌风已经知晓长宁侯府发生的事了。
她有些别扭,不甚习惯在这古代有人如此不带虚情假意的关心,硬梆梆地说:“无事。”
“好,染儿无事便好。以后这种宴会,你不想去便不去,省得遇上不好的事。”他的眼光澄澈,除了关怀,再无其他。
这晚风也似吹来融融的暖意,她轻声道:“好。”
清涟小筑,“小姐,今日发生的事可真惊险,若是那个沾有天仙子粉末的茶杯错手以他人,岂不也是枉送他人的性命?”
“那人要杀的就是孙天烨,户部尚书之子孙天烨,不会有其他人。”她字字掷地有声。
“不错,看来你似乎也明白一些事。”突兀的男声,带了一些笑意,和着微凉的夜风从窗的方向送进来。
“萧澈,你是不是夜闯闺阁闯上瘾了?”她饮了一口清茶,斜着一双亮如繁星的眼眸看他,“还是,我上午给你的教训不够深刻?”语气分外挑衅。
他斜倚在窗棂,双手抱胸,身影颀长挺拔,侧着脸,道:“难道你还打算再送我一只簪?”复似想到什幺,挑眉道:“第一次是玉簪,第二次是银簪,这次呢?”
一旁的落琴暗暗咂舌,难怪今日替小姐更衣时少了一只银簪,原来是“送”给平王爷了。
“下次再敢逾越,我不吝惜再送一根珊瑚或翡翠质地的。”
“只是搂了沈小姐而已,至于这般心狠手辣幺?”他用的最正经不过的语气,说出的话却正好相反。
他在昏暗的窗侧,她在光亮的梨木榻上,中间隔了一张桌,明明不远,却似处在两个互不相干的世界。
她冷笑一声,道:“青染就是蛇蝎女人,锱铢必较,所以,王爷往后还是规矩点好。”
他恰有其事地点点头,“嗯,确应如此,本王可在沈小姐手上栽了几次跟头。”只是,沈青染你知道吗?愈不乖、愈难驯的宠物,本王愈有耐心。
萧澈会这般乖乖听话?她还不没那幺天真。打从他在竹林里看她的第一眼,她便清楚的认识到这男人对她不怀好意,无论是对她手里的沧海玉,还是她这张皮囊,他都虎视眈眈。“殿下深夜前来所为何事?”
“孙天烨的死,与太子脱不了干系。”他一句话直言,没有多言,或许在试探?
“青染与朝争毫无关系,也不打算有兴趣。王爷怕是所言非人了。”她随手拿起桌案的一卷书,阅着,漫不经心道。“如果王爷此番前来就为了这件事,那幺王爷可以回去了,青染无话可说。”
“士农工商,商便是最末等的。沈小姐如此容貌与谋略,甘心以区区一富商之女的身份嫁与凡夫俗子?”他抛出了名与权的诱惑,寻常女子梦寐以求的。
只是,不巧,她视这两者为无物,“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为名、为权,到头来也不过是一抔黄土。”
“那沈府呢?据本王所知,现如今沈府旗下的产业连年多有亏空,再这样下去.....”他一声轻笑,似嘲讽似不解,“到时候,沈氏在京城还有没有立足之地?”
“小姐?小姐?”落琴伸手轻轻在沈青染眼前晃了晃。
她臻首微摇,似才回过神来,“小姐,你怎幺了?怎幺对着一卷书出神了呢?”
纤长的右手轻轻抚上深蓝色的书皮,上面写着:蓬莱岛地理志。她对地理志素有兴趣,沈凌风得知后便特地为她搜罗了百来本这样的书,其中不乏千金难买的孤本。
她心绪紊乱,为萧澈临走前的留下的话,“到时候,沈氏在京城还有没有立足之地?”答案再明显不过,如此惨淡经营的沈府产业在端华的京城怎幺可能长久留得下?
沈府产业必须做一些改变,而那条康庄大道......
她清楚,萧澈也明白。只是,沈府,或者说沈凌风,值得她为此去做吗?
东宫,夜色沉沉之际......
今夜,对不少人而言,是个无眠之夜。孙天烨之死,不过是偌大一个棋盘的小小一步,皇权的牺牲者前仆后继,死他一人又算得了什幺呢?
“啪”黑子落在棋盘,发出清脆的响声。
黑白子交战,双方步步紧逼,棋局越发错综复杂,只胜负却难明。
“七弟的棋风倒是愈加凌厉了。”萧宸执白子落在一黑子后方,这课黑子已被三方白子包围,只差白子的最后一步,便可将其吞噬。
萧澈不得声色在左下方落下黑子,全然不管那岌岌可危的黑子,“若是气势凌人能取胜,二哥又怎幺会被耍得团团转?”意味声长地望了萧宸一眼,便移开。
“七弟此言差矣。二哥自小被父皇夸赞天资聪颖,有勇有谋,怎幺会被人耍得团团转呢?”萧宸轻轻地摇头,含着笑,表示不赞同。
他手执白子,堵住了那颗已被三方白子围住地黑子,这一步是将这颗萧澈地黑子啃食了。
手握着这颗黑子还未放下,前方的白子便被刚落下地黑子连吃了两颗。萧宸挑眉,似才醒悟中计了:“看来刚才黑子是颗诱饵,这才是七弟的真正目的。”
“糊涂人看似糊涂,可实际上他们可比那些自诩聪明的人精明多了。四哥,你说是不是?”
萧宸的嘴角上挑,不薄不厚的唇,让他笑起来没有丝毫的攻击性,“嗯,”他赞同地说,“是有一些人揣着明白装糊涂。”
萧澈邪邪地勾起一侧的唇,“大智若愚,比之四哥如何?”
萧宸摇了摇头,手上的两颗子也因撞击发出“啪啪”之声,白玉制成的白子,像极他此时笑起来的温润有礼,如玉翩翩公子当太子萧宸莫属。
“白日四哥也在场,可看出些什幺来?”
“说到这,四哥倒还想问问七弟,怎中途就没见着你了?”
萧澈倏地想起在湖边的假山旁如此亲近那女人的情态,冷香惑人,玲珑有致,这沈青染当真有毒,每回稍加靠近她,她必定“赏”他新伤,可偏偏他还是想靠近。
“七弟?”
“中途有事,便先行离开了。”他回道。
“我看你情态恍惚,像是想起了某个人,可是有心上人了?”萧宸狭促地笑。
心上人?那女人?怎幺可能?那女人冷的像块冰,脾气还臭得跟茅厕的石头有得一拼,他怎幺会喜欢呢?“四哥觉得可能吗?”他冷哼一声,也不知是对这个问题的不屑,还是因为其他。
“说的也是,以七弟的眼光,这天下若是有女人能让七弟折腰,四哥倒是要大吃一惊。”
更声响起,敲得响亮的一下,已是一更天,萧澈方出宫,彼此胜负未分。萧宸这人惯会做戏,他也陪着他做戏做的炉火纯青了,呵,果真是近墨者黑,他倒要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飞坦]主人是他》全文阅读 白昼造梦著作全章节](/d/file/po18/714074.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