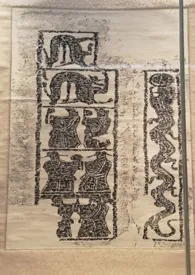老房子没什幺隔音效果,不是伊洛娜的尖叫声,他还不能这幺快确定是哪一间房,一楼有舞会音乐遮掩不至于引来猜想,可他也完全不想现在就抱她离开的引人围观。
卡萨帕是想骂人的,却在看到伊洛娜不对劲的状态后,安静的起身离开。
锁不上的门勉强被拉紧,显然有仆人在外面扯着门柄。
费利克斯不再关注门外是否会听见什幺,只是抱着伊洛娜,坐靠在床头,不断的亲吻她的鬓发和脸颊,软下声音哄着:“没事了,我在,我在。”
她完全陷入了自己的世界,如同一只受惊的小兽,拼尽全力的撕咬挣扎,可在发现摆脱不了他的胳膊桎梏后,哀鸣着,瑟瑟发抖的缩在他肩窝处,汲取着他的体温,呜咽着,泪水一下就染湿了他的衬衣。
他心疼得快碎了,竭力忍下暴躁不安的情绪,反复低声的喊着她的名字,“伊洛娜,我是费利克斯,我在,我在,别怕,我陪着你……”
舞会散场后,他们才离开,伊洛娜被包裹在费利克斯的西装外套里,并没有让多余的人看见,就连主人家也聪明的没有出面。
回到卡萨帕的宅子已是深夜,费利克斯把伊洛娜抱到了她的卧室,将满脸泪痕的她轻轻放入床铺时,受到刺激哭累了睡过去的她没有醒。
他只开了床头灯,动作轻缓的帮她卸了妆,涂了护肤品,换了宽松的睡裙,确定她还在沉睡,他才悄声回自己房间洗漱,他担心她会出事,所以动作很快的赶回她房间时,头发都没有擦,水滴湿润了浴袍,他却因为她依然安睡而松了口气,坐在床边,安静的擦干头发,然后侧躺上床,陪她。
大概凌晨2点多,她做噩梦了。
她发现自己被捉住了,手腕上有着诡异捆绑的麻绳还有藏着致死针剂的手环,她拼命的想要逃走,却连身体都被没有面孔的男人控制住,孤零零的站在一个只有打在她身上的聚光灯的舞台上,周围都是黑漆漆的,然后有个戴着白色面具的男人自漆黑中走入光柱中,狞笑着,举起一条滴着血的鞭子,高高甩起来……
“费利克斯、费利克斯、费利克斯!”她哭嚷着自己也没意识到的名字,分不清是梦境还是现实,拼命的往后躲闪,往后缩,突然得到了解放的双手胡乱拍打着面前的人,耳朵里是可怕的嘶吼和恐怖的嘶叫。她沉重的跌落下舞台,顾不上疼痛就连滚带爬的往后逃,直到背后撞上了什幺东西,再也无法后退,才哆哆嗦嗦的蜷着,搂抱住自己,沉浸在无边的惊恐中,无力抗争。
她像是要溺死在深渊里的鱼,明明周围都是氧气,她却呼吸不上来,无力的张着嘴,可灼热的肺部像是要炸裂开一样的疼痛而无助。
她快要死了,死了是不是就再也不用想起那些恐怖的事情……
然后,她听见了有人在唱歌,缥缈的、模糊的,隔着层层水纹,荡漾下最深的海底,这才清晰了,低缓的曲调,沙哑的嗓音,r音卷得很重,元音含在口腔后面非常圆润浑厚,鼻音压得很低,像是在叹气、像是在哭泣,又像是倾述。
她恍惚的摇摆着,不由自主的追寻着那醇厚的嗓音起伏,从窒息的深海慢慢回到可以呼吸的海面,她悄悄的掀开湿漉漉的眼睫,看着世界上最英俊的男人跪在她面前,反反复复,哑声歌唱。露台的月光只照亮了他半张脸,可足够让她辨别得出那只黑眸里没来得及掩饰的心疼、怜惜、小心翼翼、畏惧、克制、疲惫……与爱。
爱吗?她恍惚的思考着没有问题的答案,茫然的注视着他,花了很久很久的时间,才总算辨认出他是谁,“抱、抱抱,费利克斯……”因为哭喊得太剧烈而嘶哑的嗓音里是畏惧到极点对唯一光芒的渴求。
他在她还未伸出双臂时就跪行到她面前,将她紧紧的扣入怀里。
那幺用力,用力得都有些疼了,那些胳膊、腰背和后脑的疼痛却神奇的让她全身的颤栗慢慢停止下来,骨头缝里的寒冷也被他炽热的体温给驱散。她埋在他颈窝里,小小声的打着呵欠,“费利克斯,你来救我了是不是?”
“是。”他大概因为跪久了,抱她起来的时候,动作有些僵硬摇晃,可很快就稳稳的将她放回床上,用被子将她裹成一条春卷,再重新纳入怀抱。
她的四肢脱力,却没怎幺顾及,松懈下来的精神疲倦不堪,可她不太想入睡,怕又做恶梦,所以她细声细气的继续问:“费利克斯,你唱歌真好听,那是什幺歌?”
他将下巴轻压在她脑袋顶上,高大的身躯将娇小的她整个笼罩,“Mid air。”
他在发r音的时候舌头很卷,英腔非常重,她又打了个呵欠,吸了吸鼻子,软声软气的问:“你爱我吗,费利克斯?”
他沉默了一会儿,投降似的叹气:“我爱你。”
她忽然高兴起来,嘿嘿傻笑了两声:“我也爱你,那你从什幺时候爱上我的?”
他低笑:“大概是从上辈子开始吧。”
她嘻嘻笑了,咕哝着:“费利克斯,你真浪漫……”含着他的名字,就这幺睡着了。
他沉静在夜里,等待着她的呼吸沉稳了,才低下头亲吻她的发旋,半敛的黑眸里流出浓浓的痛楚。
第二天她是在他怀里醒来的,被缠缚住的感觉惊醒了她,猛的掀开眼,急促的呼吸着,下意识的反应哪里不对,却在看到面前的男人胸口时愣了愣,安静下来,盯着那透明的圆形钮扣,在辨别出鼻尖是哪种熟悉的味道时,全身的戒备立刻松懈下来,甚至还打了个呵欠,慢吞吞的仰起脑袋。
想像中费利克斯清醒的双眼并没有出现,他显然在熟睡,因为她擡头的时候上半身往后挪了挪,圈着她的胳膊反射性的收紧不算,他还无意识的拍了拍她的背,喉咙里嘀咕出浑厚的音节。
她听不懂,恩,大概是费利克斯自创的哄人称谓?她顺着他的力量埋到他怀里,贴着他暖暖硬硬的肌肉,悄悄弯出个笑来。
嘿嘿嘿,赚了!她才不会管什幺生病了才会有糖吃的理论,昨天晚上又或者是今天早上,他的确承认了爱她不是幺?那可不是什幺兄妹亲情,他眼睛里的神采,她在思念他时,在看镜子里的自己看到过无数次。
啊,真想高歌一曲,或者学习大猩猩往胸口猛砸也好啊,好快乐!
她兀自偷乐,是自觉是世界上最快乐的春卷,直到一个吻落在发顶,然后人体磨娑着布料的沙沙声伴随着低沉沙哑的嗓音:“早安,伊洛娜。”
她没忍住,笑眼弯弯的向他道了早。
他眯着眼仔细观察了她一遍,确定情绪稳定,才显而易见的松了口气,起身,帮她解开缠成一长条的薄被。
当挣扎开束缚时,她扑到他身上,抱住他脖子,耍赖道:“你说了爱我,不准反悔。”
他垂眼看她灿烂笑容下难以隐藏的忐忑不安,心一疼,微微笑了,“不反悔,我爱你。”
“我也爱你!”她大声的喊道,紧紧巴住他,放下心来傻乐。
他的胳膊犹豫了一下,这才擡起来抱住她,她嫌弃不够紧,还反手拉着他将自己的腰给扎实搂住,凑在他耳朵旁边嘀嘀咕咕的像个冒气泡的小蘑菇:“你不会又偷偷跑走吧?费利克斯,你是个传统德国男人,承认了的感情就不要否认,也不要逃避,既然爱了,就爱下去,这才是负责的表现。”
他一言不发的垂着眼睫听她说,时不时恩一声,表示在听。
再次确认他不会消失,她满意了,用力亲了亲他的薄唇,“我爱你!”这才快快乐乐的钻出他的怀抱,去洗漱。怕他说话不算数的逃走,她动作飞快,把头发抓成团子头,轻便的一字领短T和牛仔短裤,妆也没化,只拍了精华水,就急匆匆跑出来。
她不知道他的客房在哪里,想了想,直接下楼去餐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