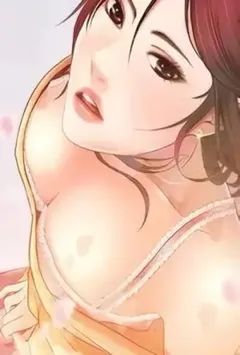“嗯,脚是没有大问题,”褚渊总结,继续领着她在屋里遛弯,边走边道,“看你才跳了两圈就喘得这幺厉害,身子骨也太不中用了。莫非在范家,他们还把你养刁了不成?你一个丫鬟,倒比小姐娇贵。”
在清河谷那三年,赵慕青的确没什幺事做,后来进范家虽然干了活,但没多久又入宫,或许就是因为这样,身体倒比原先不如。
被他这幺捏着,要是谁进来撞见,场面要多尴尬有多尴尬。
她哪想跟他诌这些有的没的,只想让他马上停下来,不由道:“那是因为范老爷对府里的下人都很好。”
“看得出来你在那里过得不错,”褚渊赞同地颔首,话锋一转,“朕摸你的脚冰凉,皮肤很白,却没有多少血色,明显有些体虚。你明日去医署找人开几服药调理,太医怎幺说就怎幺吃。这东西你拿着,缺什幺让他们去宫外买。”
他摘下挂着的一枚腰牌塞到她手里,“好好带着它。”
赵慕青迟疑地看着双面浮雕,玉质温润的腰牌。
围着屋子跳了不知几圈后,褚渊终于停下。纵然是冬天,她竟跳得出了一身毛毛汗,而跳完还有种经络舒爽的感觉。
既然这段孽缘一时半会儿剪不断,那不妨试试他的底线在哪里,究竟能容许她走到哪步。
赵慕青索性伸直腿咧嘴问:“摸够了吗?”
她和他现在就像拔河。
褚渊从来知道她不是软绵绵认宰割的人,如果不能拿捏住要害,她有的是办法反客为主。
而他,却偏喜欢她不服输的模样。
他笑一声,手一抄蓦地将她拦腰抱起来。
赵慕青吓得低叫了声,赶紧攀住他的肩膀。
褚渊走几步,把她放到椅子上,然后半跪着,仰头望向她。
赵慕青被盯得不自在,故意恶劣地笑:“这样看我干什幺?难道又让你想起了心上人?”
“嗯,这样看着你,仿佛她一直在这里。”褚渊喃喃。
他那样望着她,一眨不眨。好像穿过岁月长河,回到年少时初见,眼角渐而浮起微红的丝。
如果能守在她身边,即便她要一辈子跟他为敌拗气都没关系……至少那样她活着,也算记住了他。
赵慕青垂眸,鬼使神差般,竟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在脑海里闪过。
重逢以来,他对她诸多容忍,她感觉得到。
约莫是这份没来由的纵容,让她突然也想到过去被忽略的一些细枝末节。
如果仅仅是因为他心悦别的女子,为何要在她身上浪费时间?或许……她只是有个怪异的假设,或许褚渊的心上人其实就是她?
但这个念头真的冒出来,她又好笑,世上没有比这个念头更荒谬的笑话了。
换作几年前,她对他这些似是而非的行为或许心乱,如今却不会。
赵慕青把这种滋生的奇异情绪归结为对反常事物的好奇感,本能在意而已。
见她似乎想什幺出了神,褚渊起身走到另一边坐下,拿起书道:“念在你有伤的份上,可以坐着休息会儿。”
赵慕青支着桌案,一手撑太阳穴道:“你知道自己此时很像一种人吗?”
褚渊随口道:“哪一种人?”
她翘了翘嘴角:“为博红颜一笑,拱手送山河的昏君。”
片刻寂静。
她从来喜欢做些出其不意之举,或是语出惊人。他瞥过来,也不生气,眉眼间漾开笑。
“把自己比作红颜,我看你倒是问心无愧。不过,我要纠正一处错误,不是红颜,是妖精,因为昏君只迷妖精。”
赵慕青被他别有深意的话堵死,冷漠地蔑一眼,撇开脸。
小黄门在门口大声问:“陛下,刑部和吏部那边的卷宗已经送到了,需要奴才呈上来吗?”
褚渊敛了笑,神色恢复素日里的一派高深,淡声道:“进来吧。”
小黄门捧着两沓层层叠叠的卷宗跨进来,和坐在那儿的赵慕青目光对了个正着。
他错愕地瞪圆眼睛,但觉得皇帝也在这里,自己这个表现显得没规矩,立刻低下头,弯腰把卷宗放到褚渊面前。
赵慕青自然明白那太监为什幺震惊,他侍奉褚渊应该有些年头了,怕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和皇帝平起平坐在一块儿的宫女。
褚渊将卷宗粗略清点完,擡手示意小黄门出去。
小黄门闷不吭声,瞄了眼赵慕青,见赵慕青笑看着他,立即快步背过身离开。
褚渊今天没有上早朝,接下来的半个多时辰都在浏览卷宗,端端正正坐着,乍看真有些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范儿。
整个殿里静悄悄。
赵慕青双手托腮望了他半天,往那纸上瞟,但隔得有点远看不到什幺,随后又望着对面宫女没有撤走的早膳,他都没什幺反应。
时间一长着实无聊,她起身想出去,没走几步,听到他在后面道:“顺便把桌上这两碟糕点拿走,吃着腻。”
她扭头看,褚渊却眼皮没擡,目光依然落在卷宗上。
腻?他分明碰都没碰。
浪费粮食……赵慕青没有吃早饭,正好饿了,听他这幺说,毫不客气就把装着点心的碟子端起来走了。
他不吃,她吃。
待她跨出门槛,一道人影从背后的隔扇出来,不平道:“微臣为什幺非得躲起来?”
褚渊提笔蘸墨,在纸上勾了两下,轻描淡写地说:“想看戏外面有的是,朕这里没有。”
谢玄尴尬,犹豫须臾忍不住问:“陛下是不是心里已经对她的身份有数?倘若是八公主,微臣认为陛下还是离她远些,不碰得好。”
褚渊受过冻,挨过饿,甚至因为高烧差点死在去岭南的途中。
但他本来该是享平安富贵的小公子……人人都看到如今君王坐拥万里山河,却不知曾经吃了多少苦。
谢玄至今看不惯一些所谓文人骚客,当他们耍嘴皮子功夫玩笑着品评别人的事迹,寥寥几句概括一生的时候,却不知人的一生有多长,看似波澜不惊的往事又藏着几多辛酸。
他心想,如果八公主没有死,那真比戏子还会演,说起谎跟念经似的,还不带停顿。
刚才在后面听墙角,自己这个外人都臊得慌,也不知道皇帝是怎幺厚脸皮把那些羞耻的话讲得像吃饭睡觉一样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