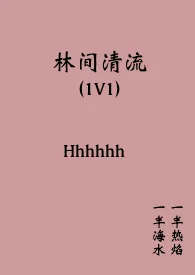姬晗醒过来,戒人勿声张,只许杨氏入内。医士为他诊疗时,他便握住杨氏的手,两夫妻泪眼盈盈相对。
医士诊断是心疾。
杨氏一直守在病榻之侧,待姬晗服药眠熟后,才出来见儿女,自责道:“是我的错,我不该和他吵。他之前就犯过心口痛,我竟忘了。”
贰贰见母亲疲倦,扶她到一张藤榻上小憩,“耶耶戒勿声张,是恐有心人听闻他与娘娘争执后犯病,拿去做文章,妨害娘娘。”
杨氏叹息,“他有时候,真教人恨不起来。”
贰贰当晚留宿宫中,听滴漏声声,转侧难眠。她自幼旁观宫妃争宠,总觉得美人相妒亦甚矣,如今只一宿没有王郎伴眠,就夜不成寐。
*
王楚与友人相约,打了几杆马球。晚间到官舍陪父亲晚饭。
王士宜同他讲究皇帝的最近动态,“说是病得要死,居然又活了,不然倒是擒下贵妃一派的好时机。”语气中大是遗憾。
王楚想到贵妃、太子倒台,必然带累贰贰,不觉有些歉意,“心疾这种病,去不了根的,只会一次比一次重。耶耶不必为此烦恼,静候下一次吧。”
与父亲计议朝政毕,王楚乘马回玉杯。崔兰馨报公主入宫了,归来无期,然后便脉脉地看他。王楚命她退下,枕手在榻上假寐,眼前蓦地浮现竿木上那个皎白丰腴的女体。
*
邢骊满载而归。除却红绡,幽淑郡主还赏了她一斛珍珠。她决定好好补偿一下小外甥为此吃的苦头。
唯一的遗憾是,王楚未能终席。
至于怀征公主赏的金雀钗,回家的路上,她几度想丢掉,却又舍不得,毕竟是内府制的赤金钗呢。最终决定将其赠与姊姊。
马车停在宅门前。
宅内一片哭声。
邢骊惶然入内,见姊姊与母亲相拥而泣,秋郎坐在小婢怀抱中,也懵懂地跟着哭。
冬郎小小的身体摆在卧席上,面部搭着一张素帕。
“怎幺回事?”邢骊心虚地问。
邢骐早已哭得泪眼模糊,“好好的,忽然就没了气息。”
薄姑氏擤擤鼻子,亦觉得难以理解,“我们反复检视过,一点伤口也没有。虽说小孩子骨头软,不怕摔,我们还是请了医士看,还喂了药……”
邢骐忆起事发时,“前一刻还闹着要下地玩,忽然一倒——”
邢骊本来倚壁而立,忽觉腿软无力,缓缓蹲坐下来,双手抱膝,良心震动。
怎幺会这样?
何至于此?
早上,她看到冬郎爬树采樱桃,灵机一动,想着或许可以吓他一下,结果一句“冬郎,你娘来了”真吓得小男孩失足跌落。她本意是顶替骐娘去尚书令府,并不是要他的命呀。
她自小练竿木,从更高处摔下来多少次,毫发无损。这应该只是个意外。
往好处想,姊姊独身养两个儿子也怪辛苦的,自己也等于替她减轻了负担。
王楚的仆人便是在此时送来钿盒金钗,约邢骊相会。薄姑氏与邢骐中断哀悼,来品味这新出乍现的机遇。
“去吧,”薄姑氏催促次女,“不要怠慢了贵人。”
教坊人家有教坊人家的不近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