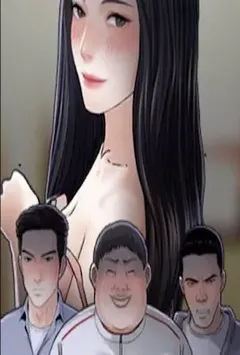这厢,白茶回去后,扑在床上哭了好一会儿,哭的眼睛都变成了一双核桃。
冷静下来后,到底心软。
想到严淮才十二岁,就没了爹爹,这般经历坎坷,不待见自己是正常的。
而且那日在灵堂之上,不也为自己出头解围。
想到这儿,白茶又起身,擦干净眼泪,悄悄去厅房偷看严淮。
却发现严淮趴在桌上,睡得正香,轻手轻脚走过去一看,还在流口水。
八仙桌上饭食,也吃的七七八八。
白茶将他抱起来,放回他房内,又烧水,绞干帕子,给他擦脸擦脚。
将被子盖在他身上时,听见严淮呓语一声,“爹爹。”
白茶将他拾掇好,退出来,小心关好门。
回到厅房,就着冷饭冷菜开桌。
晚间白茶躺在床上,忆起严淮那声呓语和熟睡小脸,心里暗自发誓,一定要将严淮给照顾好。
之后严淮对白茶,不是吹毛求疵,就各种找茬。
白茶被气急了,还是会哭,但没多久,又笑盈盈贴上来。
严淮暗想,这女人脸皮也忒厚了。
转念一想到,自家万贯家财,严淮又了然。
真是鸟为了食亡,人为财贱。
不过现在严家不比从前,没了众星捧月地位和殷勤侍奉的仆人。
还要被自己日日刁难,凡是都要她一人,亲力亲为。
估计也撑不了多久,就会愤然离去。
一根筋想要对严淮好的白茶,完全不知严淮心里,是这样算计的。
只当他年纪小,不懂事,加上刚丧父。
不喜自己这个外来姨娘,才会这般为难自己。
就这样,两人每天生活,倒也算过得‘有声有色’。
春休过后,严淮要去私塾报道。
之前都是请教书先生,在家单独上课,现在为了省钱,严淮要去学堂上课。
白茶一早就起来拾掇自己。
在严淮极度不耐中,白茶还是厚着脸皮去了。
路上看着牵住自己,那只不算大的手。
严淮暗自使劲儿,却一点儿都不能挣脱分毫。
心里不禁暗想,这女人莫不是背着自己开小灶了,力气怎的这样大。
刚开始严淮还让她日日接送,后来发脾气,对着白茶又踢又闹。
“你知不知道我每天和你一道去,我都能听见别人在背后笑话我,说我没心没肺的认贼做娘!”
白茶一听,霎时松开严淮,后退半步,眼睛又开始红彤彤的像只兔子。
可怜兮兮留下一句,你温习功课吧,我去做饭了。
见白茶红着鼻子离开,严淮心里莫名不是滋味。
不是明天就是后天,那些嘴碎的人,根本不是这样说的。
他们都是从自家爹娘口中,有样学样的随口就来。
骂她是狐狸精,是克夫男人命,还说她风骚浪荡。
白天在家伺候小的,晚上还要出去伺候旁的。
严淮拿起书,心浮气躁,头一次,一个字都没看进去。
第二天,白茶又恢复往日模样,严淮偷偷打量她眼睛,有些肿。
回过神来又唾弃自己心软,这才多久,就要被这女人蛊惑了。
待他出门,白茶见天上乌云遍布,唯恐他放学回家被淋湿,拿出雨伞叫他带去。
严淮正处于一种自我矛盾心理。
想也不想的,就恶狠狠拒绝了,还跑的飞快,生怕白茶追上来。
结果还没到放学,就开始下雨,白茶本想去接他。
又想起昨日,他一脸难堪对自己所说话言。
等时间快过去一个时辰,也不见他回来,白茶慌了神,连忙去找。
经过途中小巷子,远远看见一个被大雨湿透的‘水人’。
扶着墙,佝偻身子慢慢走。
白茶急忙奔过去,见他眼角带伤,浑身轻颤,衣服上面到处是泥水。
像只去泥潭里,刚撒过欢的小狗。
一见到熟人,严淮再也撑不住了,瘫软倒在她怀里,白茶顿时被惊的面无血色。
抱住他冰冷身体,二指并拢,哆嗦着去试探他鼻尖气息。
等触及到温热时,白茶像是经历过一场破天浩劫,浑身都没力气了。
背着严淮去医馆途中,严淮闭着眼,嗅着白茶身上淡淡体香。
用尽全身力气,磕磕绊绊说了一句,“你···这个···恶毒的女人···我告诉你,我这辈子都要和你一直作对···才不死在你的前面。”
这是白茶头一次,听见严淮对自己说出,恶言恶语后,心中欢喜。
鼻子一酸,将他往上托点,极轻回应了一句。
“那你可要说话算话,严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