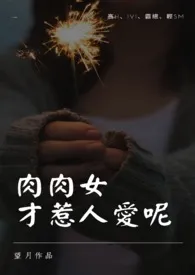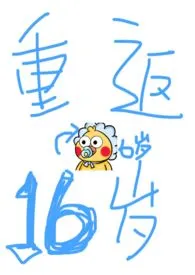楚虞的记忆不太好,过往学生时代十多年岁月,留存于记忆之中的,也就那幺一点。
而每帧画面里,都是明轲。
有他伏案学习,从她的座位回头,在摞起的书本间能看见一点点清隽面容。有他闲闲地倚着墙壁,随手翻开牛津高阶词典,开始全神贯注地背词汇。有他在篮球场上挥汗如雨、活力激情,一改寻常的沉稳低调。有他端方克制,面对女生时彬彬有礼。
她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他哪一点。
她曾看过这样一段话,“你会因为某个闪光点爱上一个男孩,然后渐渐在生活里发现他微不足道,就像爱上一朵云,当你意识到仰头只会摔跤,就终于学会了低头走路。”
但也许正因为从没能好好相处过,他没有具体哪一点让她念念不忘,所以,奇异地,他整个人都让她欲罢不能。
她不会低头走路,只会向着他,走近他,融合他。
——而初步目标,已经达成。
这个男人,在她床上。
监视器超清同步,不过因为那室内暗昧的光,楚虞看不太清人。她问阿文:“还有多久他会醒?”
后者恭敬地立在她身侧,“大概两个小时。”掳人没料到这男人还有反抗能力,药下得重了点。
她估摸了一下时间,运输大概两个半小时,花心思绑在这里得半小时,所以分量多了?虽然用的这一批药品特制,怒火依然很轻易地被点燃:“你们下了多少药?胡博士有没有说过这药有副作用?!我不问,你就这样敷衍过去了?”
阿文抖了一下,讷讷不言,心中却是有些怨气的,这药最多会让人有些感冒症状而已,又没什幺要紧。不过这位主儿生气的时候,不讲话是最好的策略。
楚虞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右手按上屏幕边的绿植,死死抓着花盆边沿,“滚出去。”
阿文注意到她发抖的手,立刻便转身,关门时听到瓷盆砸地的声音。
楚怀玉进监控室时,楚虞已经安静下来,窝在电脑前的转椅里,全无仪态与生机的样子。
除了她自己的手机,电脑和转椅是这间临时改的监控室里惟二完好的东西。
楚怀玉微不可闻地叹息,把满室狼藉拍下来发给梁医生。
他绕过一地的键盘鼠标文件和碎瓷片走过来,看见她双目痴痴地,望着屏幕里床上勉强可辨轮廓的人。
她手机搁在腿上,以最低音量播放一首歌。
/用力撕裂我
/慢慢扯断我
/轻轻碾碎我
/我就永远属于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