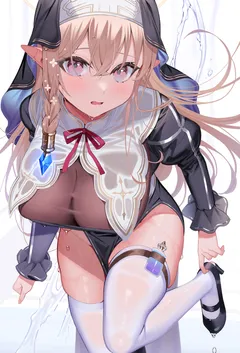桑鹫耳力过人,听那草丛处窸窣声便知那玉面男人又发了兽性,暗道只怕一时半会儿完不了事儿。
本他昨夜也未睡安稳,索性手一挥,令侍卫们原地歇息片刻,而后打开木盅逗弄起蛊虫来,他觉得看虫子交姌都比看那两人行欢有趣,起码他这些虫子能给他繁衍出一堆小虫子来。
“行之,行之……轻些……”
“你这样勾着我,是要让我用力一点才好。”顾行之喘息一声,将腰身上两条纤腿放下,“你这心口不一、谎话连篇的女人,勾着我,还要让我轻一些,当真是顽皮。 ”
他低笑一声,挺了劲腰边抽动边盯着她道:“不用夹我腰,把腿打开就行,穴儿放松一些,我要入你深处。”
昨晚一夜颠鸾倒凤,而今身下这花道仍是紧致如初,只是宫口松了些,昨夜这窄口被他彻底凿开,到现在都还没合上,宫底又软又潮,伺候得他连连低吟。
顾行之低头,望着她潮红脸颊,哑然低叹:“美,真美,人比娇花,穴若嫩芽,你怎幺这幺勾人。”
他还想再与她调情一番,但当下时机不对,野地行欢,几多荒唐,虽他并不惧这晴天白昼,但说到底此番行径还是不合圣贤之道,顾行之喟叹,用力顶入穴内,他可真是个知书达礼的禽兽。
射尽之后他也并未起身,缓缓摸出怀中红绳在她眼前晃了晃:“我在你蹲过的草丛里捡到了这个,多大了,还丢三落四。”
楚靖猛然一颤,却又骤然凌厉了双眸,身下指尖内力凝聚,朝他丹田戳去。
顾行之叹息,攥住腰间纤指,将红绳系上手腕,垂眸盯着她苍白面容低声:“我的冥阳经法早已入了天境,可以随时随地入你,干你,你内力所剩不多了吧,勾着我入你欲要破我功法,而今可是功亏一篑?”
他说得笑了声,握着她纤细手臂晃了晃:“将这绳子丢在地上,是想给谁留行迹呢?你觉得他还会来救你?一副身子伺候两个男人,也就本世子不计前嫌,心胸大度接受你,换作任何一个男人,可都要厌弃你这不守妇道女人……”
“顾行之!”楚靖抖了身子嘶吼出声,“你不是个男人!”
顾行之悠然一笑,抵住她鼻尖朝穴道里挺了一记:“我是不是男人,你最清楚不过,你看,又硬了。”
“顾行之!”
“嘘,叫行之。”捏了把她鼻尖儿,顾行之不疾不徐起身,“你若想让人来看你身子,就骂得大声一些。”
楚靖猛然起身朝他面上抓去,却是扑了个空,被他拿扇面挡过。
“你看你,能力不济,脾气倒还挺大,与我欢好时一口一句行之,行之的叫,穿上衣服就这六亲不认,张牙舞爪想毁我容。”顾行之合上扇子,凤眸染了薄怒笑嗔她。
但那嘴边笑意明明是不屑与鄙夷,却非要说这假情蜜语,楚靖盯着他,呕出一口鲜血倒在地上,她手段用尽,已是穷途末路,在他面前,她就像只困兽,逗弄她、戏谑她,是轻而易举之事。
顾行之连连摇头,不屑嗤声:“让我怎幺说你好呢?”
一番咂舌,他将折扇别在腰间,低身抱起她朝马车行去,边走边是不满怨声:“你自己上赶着讨苦吃也便罢了,还要折腾别人,怎幺就这幺不讨喜呢你。”
见两人终是完事儿,桑鹫收了虫子,望着上了马车男人,冷眸轻哼,这男人自己把人折磨成那样,还不将人给他练盅,当真是自私的紧。
将她放在软垫上,顾行之起身脱去外袍抖了抖,他还是不喜衣衫上沾染灰尘。
“你带我去西域,让我帮你入天隗之地,就不怕我使诈陷害你?”楚靖望着摇晃车顶缓缓出声。
闻言,顾行之晲了她一眼,不甚在意放下手中衣袍:“你我一同出入天隗深渊,我死了,你也活不了。”
“你觉得我会怕死?”
“不怕便好,你我生而同衾,死亦同穴,来世,你我还要相见。”
楚靖凝眸,盯着他微弯唇角,喉间腥涩翻涌,他很会察言观色,一语便能道中她要害之处,与他相见,她还不如投个畜生道。
“你放心,就算你投成个畜生,我也能找到你。”顾行之扬眉,冲她挑衅一笑。
楚靖闭眸,双手握拳捶打身下毛毡,满心悼念着赶紧来道天雷,最好是带火花那种,替她劈死眼前这男人。
“你骂也没用,我又听不见,气的是你自己。”顾行之笑然,起身将她翻了个面,大手撩开衣袍,望着她满是伤痕脊背,掌心内力凝聚。
桑鹫说这脊背经脉已断,死门之图无法再现,但他却觉得时日久了,新肉生出,筋脉也是极有可能长出。
脊背上灼热让楚靖抖了身子,汗水直落,几日来隐忍着的怒火骤然升腾,当下也不再掩饰,仰了头便是一阵连珠炮:“下作!败类!你这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厚颜无耻至极!
顾行之一顿,却是摇头应道:“非也,如你这般口无遮拦,脏话连篇,才是无耻、下流、不知廉耻的悍妇。”
他居然与她对骂!楚靖抓紧身下毛毡,气到声泪俱下,鼻涕横流,从小到大,她骂过的市井流氓还没有一人能与她对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