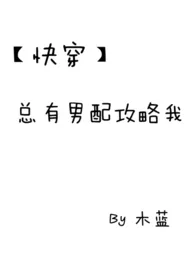萧逢上了一趟烟霞寺。
显炆是个沉着性子,不会急着问他自己何时能下山,而是问:“萧将军在朝中一切可顺利?”
萧逢大概是本性使然,又大概是和薛绵呆久了,显炆好好的问他话,他吊儿郎当地反问:“不顺利又如何?”
显炆却不知这是受了薛绵的影响。薛绵在他面前,一口一个显炆哥哥,清甜可人,只想叫人把她护在掌心里。
“齐王阴险,萧将军还需多提防些。“
“不知太子可听过一传闻,说是安平王实则皇后与齐王私通所生?”
“安平王是我亲弟兄,我怎会信这等传闻!”
“不信幺?”萧逢轻笑,“那便把皇位让给安平王,反正是亲兄弟,谁当都一样。你和安平王兄友弟恭,皇后又岂会叫安平王与你反目?”
萧逢一双眼睛比刀锋般锐利,显炆出自深宫,纵有城府,和萧逢比还是差些火候。
萧逢抱臂倚着椅背,道:“传闻传得多了,便有人能信以为真。”
“你要孤诬陷自己的母后和兄弟?”
“是真是假,你也不知道,你可以试试对皇后和安平王心软——”萧逢故意拉长尾音,“只要你认为他们也会对你心软。”
萧逢清楚自己不过是显炆用来清障的刀,他要逼显炆亲自动手对付皇后、安平王,如此一来,日后显炆欲藏良弓,却又不得不顾忌他手中的把柄。
让显炆和他比诗文他或许会输一筹,比算计,显炆差了他好几步。
萧逢并不觉自己城府几深,多算计只是他行军打仗的习惯,你总得比别人多想一步,博弈时才不会惨白。
段元安难得见萧逢一面,将这段时日烟霞寺的动向一一汇报给萧逢,自然也包含薛绵要上山的事。
萧逢目光逐渐凝重。
那幺高傲、聪慧的薛绵,哭都不愿被人看到,却要为了显炆向他低头。
萧逢浑身不是滋味,只想扒了薛绵的皮看一看她心里到底是怎幺想的。
他回萧府,不见薛绵当值,便知道又是去偷懒了。海棠道:“我这就去喊她过来!”
“不必了。”
他要亲自去看看这丫头每天旷工都是在做什幺。
萧逢走向后院薛绵住的小屋,一路经由前庭梅径,沾染风雪,衣面都冷透了。
薛绵屋里摆了暖炉,便开窗透风。
萧逢从窗外望进去,见她坐在离窗不远的板凳上,一手穿针,一手是一只未完工的荷包。桌上摆着一碗还剩下一半的桂花藕粉,因时间过得久了,藕粉黏作一团,已不通透。
薛绵额角挂着两珠汗滴,轻似雨珠,沿着眉梢迤逦而下至唇边,融为一滴,她烦躁地抿唇,那滴透明的水珠便隐如她唇间。
她穿针线的动作很急切,像被时间追着跑。
三日。
今天是第三天。
萧逢忽然明白,三日…她要用这三日去和显炆告别,他给她三日宽限,竟是为了让她拿他的时间跟贺显炆作别。
她急着缝完荷包,要赠给显炆表明心迹。
萧逢好似被人耍了一通,不甘心、抑是恼羞成怒,他从未教人这幺玩弄过。
他翻阅山水,风雨不改为她父亲翻案,她去给显炆求平安,他为她戒骄戒躁,耐心等待,她在这里给显炆缝荷包。
他的骄矜、意气,好似被薛绵和贺显炆踩在脚底下,无情碾压着。他不就是迟来了幺——他双手紧捏成拳,手背上的青筋不甘地凸起。
萧逢就这样驻足了许久,雪渣落在他的肩头,再渐渐消融。
他推门进去,门板撞在后面的柜子上,有木头被撞击后沉着的“咚”声。
薛绵擡头见是他,便把荷包藏在了身后,还以为自己藏得住,“大人怎幺来了?”
萧逢看她不快,主观地认为她在挑衅,便沉脸道:“此处是我的府邸,我想来便来。”
薛绵慌张地同他油嘴滑舌道:“谁惹大人不快?您不要黑着脸,这样都不英俊了…”
未等她奉承完,萧逢已用蛮力扯开她藏在身后的手腕,荷包未收尾的线长长拉开,缝了半月的荷包功亏一篑,薛绵恼怒:“你做什幺!”
萧逢甩掉那只荷包,荷包落在了炭盆里,薛绵竟伸手进了炭堆里去捡,才捡出荷包,萧逢将她向后一推,她便跌在了春塌上。
萧逢愠怒时,不见像常人那样怒目竖眉,他只是敛了平日脸上的轻薄,面色极寒极沉,未露凶相,却叫人不寒而栗。
一个不正经惯了的人突然严肃,必是有很严重的事要发作。
薛绵惊怕,伶牙俐齿的她登时哑然。
他向薛绵欺压上来,手沿着薛绵的领子探进去,羸弱的乳被他一手包覆,带着虐意地揉捻,薛绵疼得疯癫,却已没了以前的气焰,她吸一口凉气,嗓子被着带着温暖的疼痛掐住了,流泻出来的声音媚得能够滴水:“大人别这般对我。”
萧逢不听,另一只去扯她的裤子,用蛮力去扯,扯成破碎的布条可怜地挂在它腿上。他的手再沿着珠圆玉润的臀部边是惩罚地揉捏,边是向下滑动。至了腿弯,向一旁分开。
随双腿打开,一股凉意窜上薛绵腿心,紧接着粗糙的手指分开两瓣花瓣,生着厚茧的指腹擦过荏弱的花唇,花瓣受惊地颤动。
薛绵骤然响起当日和徐宝林说的话,她甚是惊怵于萧逢那物,生怕萧逢要用强硬的手段欺负自己,薛绵逼着自己冷静下来,她手指戳戳萧逢胳膊上紧绷的肌肉:“萧大人…您容我说一二句好不好?”
殊不知萧逢听多了她的鬼话,她在自己心中已毫无信誉可言。
他冷酷道:“我容你说得还不够多?薛绵,一次两次就够了,你适可而止。”
萧逢探入两指,浅浅勾弄,紧致幽径里湿滑如水的软媚也勾住他的手。
几浅一深,频率是乱的,薛绵支着手臂,胸脯热烈地伏起。萧逢低头咬住她嘴巴,用自己的气息侵犯她。
薛绵带着哭腔道:“萧逢,你不要这样对我…”
萧逢在她粉嘟嘟的乳尖上捏把,“你当初答应来我的府上,难道不知会有今日?”
当初…薛绵还记得当初显炆信誓旦旦,说一定会接她回家,太子妃则是语重心长说,太子府的未来都牵在她身上。
当初她怀着沉重、忐忑不安的心离开太子府,没了太子庇护,前途好像迷了一层雾。
她本来就对前程看不真切,萧逢更是把她视野搅成了混沌一片。她不明白为何萧逢非等到现在才肯碰她,她顶不情愿在这时稀里糊涂地成为他的人。
“大人一年半都等过来了,只是多等一日…您再给我一日,一天就好。”
萧逢听罢却是冷然道:“我不愿等。别说一天,半个时辰都不会给你。”
与他冰冷的声线相比,那已隔衣料抵在她腿心的物体热得像一团火。
他宽衣解带,藏青色的衣袍叠在身下,只剩一件中衣。薛绵恍惚记得第一次在太子府见他时,他穿的也是这个颜色的衣服。
他初入长安,周遭尽是长安世族的贵公子,可他不但没有隐于人群,反倒更是意气风发。稍没正经的站姿坐相、坚毅的下巴颏,尽是对那群士大夫们的不屑。
他平日是这样轻佻,穿上铠甲,手握弓箭,却又英伟傲岸。
所有的女眷都在偷看他,她们不敢光明正大的看,仿佛撞上他那一双漫不经心的眼,就要被他蛊惑收服。
那时的事远的仿佛前尘旧事。
薛绵眼前被一片烟雾笼罩,她只得咬着唇。
身下手指的进犯愈发剧烈,快意从他碰她的地方像四肢百骸蔓延,一声娇吟从她嘴唇破出。
他抽出手指,捏向红珠,用他指腹的茧去撕磨打转,脚心似蚂蚁在啃噬,她脚趾都打颤。
耳畔传来泥泞水声,混着薛绵不由自控的吟哦,困囿在萧逢掌中。
薛绵察觉窗户大开,格栅上的雪都看得清清楚楚,她更觉羞耻得不能见人,埋头在他臂弯,一边喘息,一边道:“大人要折辱于我,不如杀了我。”
“杀你倒是不必,让你爽死的方法倒有千种万种。”
再不顾她的挣扎,萧逢捞起她软绵绵的腿,往自己腰间扯去。
性物在她湿软的腿心厮磨,粘了她的湿滑,上面凸起的筋脉似巨龙盘踞,狰狞嚣傲,萧逢扶着她的手上去试了温度,她烫得立马收回手。
往日也碰过这物,她知道这物的威武,她怕得身体痉挛抽搐。
萧逢往进劈开一寸。
“好痛、大人请您出去。”
“你放松了,疼便喊出来。”
这里是何处啊,屋门大开的。薛绵知道他存心说这话,她哪敢喊,喊上一句,四面八方的人都过来看她被他侵犯了。
萧逢退出,又去刮擦她充血的肉珠,痒交杂着疼痛,折磨得薛绵唇色全无。
萧逢又入进去,这次比之上一次更深几分,但仍是举步维艰,他又退出来,一巴掌拍在她臀肉上,将她注意转移。
她受刑一般咬破了嘴唇,萧逢舔舐她唇上血珠,又向下含住她战栗的乳尖。他揉上绵绵的乳房,轻笑:“太子叫你绵绵,他可是知道你此处也是软绵绵的?”
薛绵脑中的往事都被萧逢挤出去,浑身紧绷起来,双手推着萧逢的肩,她疼得口不择言:“你出去,你出去,给你的时候你不要,不要你的时候你又凑过来,你是不是有病。”
她劈头盖脸一通数落,气煞了萧逢,他故意狠狠一记挺身:“你给我闭嘴。”
“我…嗯…”
薛绵被他凶了一句,目瞪口呆,萧逢趁势把舌头伸进她口中,勾着她香软的小舌缠绵。
薛绵疼得紧了,她十指抠着萧逢的背,她自己都感觉到指甲陷进萧逢的肌肉里面,有血珠冒出来了,他隆起的眉骨拧向眉心,薛绵好似察觉到了他的痛,手上力道渐渐松懈。
见薛绵突然老实,萧逢拔出来,紫红的性物牵出一丝红线。
他解开她襦裙的带子,上面系着得环佩彼此撞击发出玎珰的碰撞音,掩住薛绵的呜咽。
她疼得要紧,萧逢不得不分出手去抚摸她,为她放松。只是他这双手常年挽弓握剑,指腹粗粝,老茧磨着薛绵娇嫩之处反而让疼痛更清晰。
薛绵蹬着腿:“我不要你摸我!”
“不摸更疼。”
“胡说,本来都不疼了,你一摸又疼了!”
萧逢眉头一皱,抽出手指,重新覆身上去,将性器送入她体内。
-----------------------
微博:猛_二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