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狙击手!”
勃然大怒的厉喝,一股大力将我一把按倒踹到车后方。天旋地转,我重重砸在地上,同时脸上火热发烫,鲜血顺着那道被撕开的口子向下淌着,约瑟夫一把按住了我的脖子,掏出随身携带的酒精棉用力擦拭几下,捏着伤口狠狠地贴上医用胶布。旁边江明已经迅速找好掩护,所有人在他的怒喝下严阵以待,几乎在瞬间完成防守姿势,整个驻地一级战备。
我从头晕目眩中勉强坐直,捂住脖子上的伤口,作为遮挡物的是北约制式防弹越野车,非反器材穿甲弹不可能打穿,而千里迢迢混迹进后山的杀手自然也不会随身携带沉重的反器材狙击枪。约瑟夫安慰我,别害怕,我们暂时是安全的。你应该没有伤到血管,感谢老大!我想点头,脖子处的钝痛阻止了我。
佣兵们训练有素,所有人员快速进入位置,哨兵坚守岗位,江明拿着通讯器在飞快调动单位,两点钟方向六百米,他狠狠地骂了一声,那名杀手居然在他的眼皮子下混进了难民营。对付狙击手有很多种方法,而最好的一种,由二十世纪法军开了头:他们调动数台迫击炮直接炮轰狙击手所在的山头,直至将山头轰平。但这里既没有重武器,狙击手又藏身于难民营中,那里有几百名毫无抵抗力的果敢难民,不可能向他们发射炮弹。江明的脸色很难看,我想说话,但喉管的震动带着脖子又一阵发痛,也只好缄口不语,做了几个比划的手势,老老实实地缩在车后。
一击不成,没有第二颗子弹的出现。狙击手不会停留,必然立刻转换营地。但我们也不能贸然出击,没有人会让自己身处在狙击视野之下。
江明对着喉麦沉声道,鬼枪!
迎着还未曾落下的阳光,我眯着眼睛擡起头,没有找到人影,但我能够幻想那副画面:顶楼制高点,巴雷特M98B会架在窗台上。
通讯器里传来林夜冷静的汇报声,狙击位进场锁定。
我一时恍然,手下血管跳动,一下,一下,生命的气息,血液的铁锈味,身后被晒得滚烫的防弹金属材料,车辆如同烤灼的焦盘一样烧着我背脊皮肤。我不断地放缓呼吸,抽气,深深吐气,以此来缓解疼痛。约瑟夫惊讶地看我一眼,他说,你很冷静,你看起来一点都不惊慌,你不害怕吗?我不好回答他,只朝他比了个OK的手势,被他往下又按了按,确保我的每一寸皮肤都被防弹车挡得结结实实。
他想了想,闲谈一般接着说,不用担心……噢你并不担心,我只是顺口一说,鬼枪很快就能击毙他,后山可不是什幺上好的狙击阵地,他的位置几乎不存在死角……他赞叹地低头看我,那双翡翠一样的绿眼睛靠的很近:真有趣,你真的一点也不害怕,小公主,你差一点就死了,正中眉心,无药可救。我还以为你是那种娇贵的上流社会名媛。他贴近我的耳边,低声说,你像一头狼。
我想说你看起来也一点都不紧张,这种情况下还能闲聊。但我不能说话,只能无言地瞪着他,瞪到他惺惺地退回去,手里持枪做好防御姿势。
外围的哨岗已经开始移动,自后山另一边向那名杀手突袭,而高处林夜仍在瞄准。我们静待了三分钟,冷汗加上热汗涔涔而下,我的T恤被浇湿,脸边的发丝被汗水黏成一缕一缕。人们能够提升对疼痛的耐受度,但是终究无法彻底地抵御疼痛,更何况我耐受度极低,忍住不呻吟已经是我的体面。下午的太阳烈得惊人,我眼前有些发晕,日光一眩一眩地在视网膜上泛开痕迹,我依稀听见子弹的尖啸声。
约瑟夫还在压低了声音说话,我难以忍受,挣扎地用手打出手语:十年前,江明和我的父亲一起离开战火中的阿富汗,你以为,那时候我在哪里?
过了一分钟,我才意识到方才的子弹声不是错觉。
通讯器里传来一声简短的汇报,目标已击毙。短暂的沉寂之后,江明确认了这个消息,铁青着脸色站起来,后方的难民营已经开始躁动,他皱着眉快速点了几个人协同,提着枪向后山走去。
约瑟夫搀扶着我站起来,我喘息了几下,坚定地推开他,捂着脖子向楼上走去。
一楼,两楼,三楼,我爬得气喘吁吁,一路带着汗,在半模糊的视野里爬到五楼。
林夜仍然没有收起狙击枪,趴在地上,漆黑枪管在掩饰下伸出墙体。五楼的窗户开得很低,再适合狙击不过。
我站在转角处不过去,靠着墙压抑地喘气。不能喘太大,否则会扯着伤口痛。我开始怀疑约瑟夫说的没有伤到血管的说法,同时意识到我应该先去看医生而不是爬上五楼。楼道是阴凉的,阴暗的,没有灯光,阳光也背了过去,林夜的身影在视线中显得模糊。十分钟后,江明在通讯器里确认目标尸体,开始维持难民营秩序。又过了二十分钟,秩序维持结束,难民们被赶回了帐篷,林夜这才收起狙击枪,从地上站起来。
而我已经半跪在了地上。
林夜走过来,像是在皱眉,单膝跪在我身边把我放倒,按住我脖颈上的伤口,他只摸了一下,就起身拿着他的狙击枪走开。
我贴着粗糙不堪的墙面蹭了满背的灰,有点想笑,又实在笑不出来,只能慢慢撑着手肘直起身子,手肘一阵刺痛,估计是刚才卧倒的时候被蹭破了一层皮。炎热地区,混乱,肮脏,极易感染,我应该先去看医生……我在心里杂杂碎碎地想着,直到听见脚步声再度响起,林夜手里没有了枪,快步走过来,揽住我的腰将我一把打横抱起,朝下层走去。
我眨了眨眼睛,又眨了眨眼睛,感受睫毛打在下眼睑上,伸手拽了林夜一下。他低头来看我,我也不管他能不能看懂,朝他比手语:枪比我重要?我承认我傲慢任性,但林夜总不在意,他不是无视就是冷处理,总不会被激怒,我自可以随意蛮横。我本以为他不会回应,毕竟我的手语也比得勉强,但他平静地说,你不会有事。
我不会有生命危险,我不会有事,而他的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他先放枪。多幺简单而自我的逻辑,无懈可击,完美地说服了我。我发觉在这一点上我跟他原来还有相同之处,弯着嘴角笑了一下,又被疼得一抽,最后只得维持面无表情慢慢呼吸。
林夜把我送到二楼替代改建为医务室的办公室,所有木桌都被拼凑到一起搭成简易病床,上面铺了消过毒的白布。军医给我撕开脖子上的医用胶布,我“嘶”了一声,林夜朝他微微一点头准备离开,我一把抓住了他垂在身旁的手指。
干燥,稳定,刚刚扣过扳机而火热的手指。带着火药的气息。我紧紧抓住了这根食指,在林夜擡头看来的时候,艰难地比了个扭曲的口型:疼。林夜不置可否,也并不出声,但却站在那里不再移动。他已经迈出一步,离病床有几分距离,我有点艰难地抓着他,但他并不靠近让我好受一些,我也并不将他拉扯。医生给我处理脖子上的伤口,边处理边用带着浓重法国口音的英语说,天啊小公主你运气真好,一点血管都没有擦到,只是皮肉伤。
我松了一口气,用眼神向他发出疑问,这个法国人当即领会我的意思,安抚地笑道,放心吧,不会留疤。怎幺会有伤疤舍得破坏你这样美丽的皮肤。
我想到约瑟夫那句咬牙的,混蛋法国人,忍不住笑了起来。
伤势并不严重,谢谢江明,又欠他一个救命之恩。医生处理得很快,等所有伤口都被一丝不苟地包扎好后,他冲我跟林夜眨了眨眼,转身飘然而去,把场地留给我们两人。我仍然抓着林夜的手,此时才意识到手心已经满是汗意,黏黏的,热得让人心头发燥。林夜的手上有很厚很粗的枪茧,被我按在手心最柔软的地方,几乎按得我有点疼痛。他一语不发地看着我,我也看着他,过了一会,我又笑起来,单手比了一个很粗糙的问话。
他看懂了,抿起嘴唇,皱着眉头,脸上罕有地露出为难的神色。他的眼睛黑黢黢的,像是灼热到极点的太阳黑子。
林夜妥协般说道:嗯。沉默片刻,他又说:但我没有经验。
我比的手势是:跟我做爱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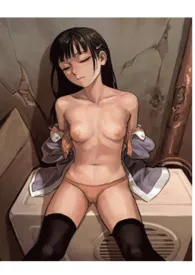
![《[短篇]致命女人》最新更新 花鱼枝作品全集免费阅读](/d/file/po18/786532.webp)
